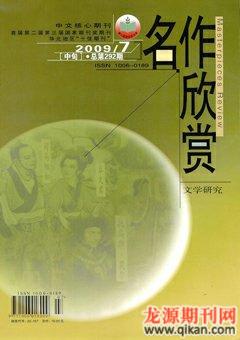从《六祖坛经》看不立文字
陈 燕
关键词:不立文字 《六祖坛经》 明心见性 当下即是 真如境界
摘 要: “不立文字”为禅宗法法相传之内核,究禅宗,必究“不立文字”。但由古而今,由于各人心性福慧的差异,对其演化出诸如“不要文字”、“文字说不清楚”、“文字性空”等论说。而“不立文字”作为禅宗之究竟理地见解,若未见本来,则对其难有圆满极致之了知。本文就是以释心法传人六祖之《坛经》为切入点,冀能得出较微妙而圆满之解读。
“不立文字”语句可追根溯源至释迦佛灵山法会之语句:“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还可从《达摩血脉论》中得有:“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而,作为禅宗法法相传之内核,究禅宗,必究“不立文字”。而“不立文字”作为禅之究竟理地见解,若未见本来,则对其难有圆满之解读。从此点看来,六祖慧能作为释心法之三十三祖,其《坛经》就“不立文字”之演绎,应是极致圆满的。
《佛学大辞典》里,对“不立文字”的注解为:禅家之悟道者,不涉文字言句,单以心传心之玄旨,谓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五灯会元》世尊章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此时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从此些话语里,我们可知,“不立文字”为“悟道者”境界,即明心见性境界。迦叶破颜微笑,是因为其从“拈花”中契见本心,当下了然世尊心即迦叶心,世尊之本性即为迦叶之本性,因而《坛经》云:“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坛经》行由品第一)诸佛、诸祖皆是为了让众生明本体,见本心,“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坛经》般若品第二)众生开悟时,即了其心是佛,其心与佛心等无有二,这就是所谓的以心传心。而“悟道者,不涉文字语句”又如何理解?看《坛经》里这一片段:
祖(五祖)一日唤门人总来,吾向你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所救,汝等齐去,自看智慧,取之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坛经》行由品第一)
从此段话语里,可看出,五祖叫门人作偈,条件是“自看智慧”、“取之本心般若之性”,其显现的是,能否传承五祖衣钵,在于可否自见本心之般若之性,而能见“本心之般若之性”的条件又是:“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其显现的是见本心般若境界为非思量、当下即是境界,亦即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境。这也可从《文殊师利所说不可思议佛境界经》里得知:“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非思量境界是佛境界。何以故?非思量境界中无有文字,无文字故,无所辩说,无所辩说故,绝诸言论,绝诸言论者,是佛境界。”因而,要见自性如来,须是“非思量境界”,而“非思量”即为灭诸忆持寄依,绝诸来去生灭,离诸概念思维言意分别之当下即是,本来即是境界。而这里的“无有文字”、“绝诸言论”其仅为能恰好而完整地表达这个“当下即是、本来即是”之非思量无为真如境界。这就是所谓的“悟道者,不涉文字语句”。所以黄檗禅师言:“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因此,见性之人,“不得迟滞”,哪怕“轮刀上阵”。因此,经文中或祖师言语中的“不立文字”,其根本是为了抉择何为如来境界的问题,它只是心灵的默契、安住、现量。若仅仅从此四个字的表面去见字解字,拘泥于“要文字”与“不要文字”,显然已离其实际。
下面我们看神秀之表现: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神秀作偈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流汗,拟呈不得……(《坛经》行由品第一)
得道之人,为大丈夫,直下承担,当下便是,无去无来,如如不动。本自无为,本自具足,何须彷徨、恍惚、流汗。从以上情形,很明显,神秀不能见性,尽管其是教授师,学富五车。再看其所作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从此偈可看出,神秀跟五祖多年,而五祖爱教徒弟看《金刚经》。《金刚经》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等等皆为般若见解,但神秀却完全不能领会,他还是一乐小法者,即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在其看来,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他完全不明了烦恼本空,菩提亦空,神秀亦空,万法皆空,方为不惹尘埃。不明万法本源,算你日日拂拭亦只是凡夫,亦只是尘埃。所以五祖给其定论为“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坛经》行由品第一)。神秀连最初地的般若见尚不知晓,更不用说无上菩提之圆满地不立文字见解。甚至直至最后,他还是不晓,看神秀当上国师后,令志诚去曹溪听法之细节便可得知。
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你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于身,于理何益。(《坛经》顿渐品第八)
从此环节里,神秀的见地与当初作偈时的见地并没有任何进步。有心可得,有静可得,有坐卧可得,完全没有涉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坛经》行由品第一),“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己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坛经》忏悔品第六)之境界,离自性说法,执迷名相分别。可真是悟则刹那间,迷则千里劫。
再看六祖慧能之情形:
慧能自从见五祖后,尽管六祖知其“根性大利”,尽管其有“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坛经》行由品第一)之见地,五祖怕恶人加害,于是令慧能去槽厂作务。神秀作偈不得后,慧能方知五祖有令人作偈之事。此时慧能求法心切,亦作一偈,便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此境地里的慧能,并不算真正见性,禅有初关、重关、牢关,唯有牢关才是不立文字境,即是见性境。初、重关,有所悟,但不全悟,不圆悟。因而,此偈之境地落点在初关,简而言之此境仅为文字相空、诸法皆空之境,并不是不立文字之微妙圆满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菩提本空,明镜亦尔,一切法本自不得、不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比神秀高明之处在于抉择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之般若境地。般若了生死,不了般若,求到彼岸,无有是处。六祖目不识丁,却比神秀有智慧,有灵性。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就是慧能与神秀的写照。而五祖看了慧能偈后,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这里,五祖确实怕人害慧能,因慧能之悟性太令人吃惊,能悟初关之般若顿见已是很了不得,这是悟不立文字之实相般若必经前提。所以五祖之言并不是假言,有赞叹慧能之智,但又明白,此时之慧能仅顿见般若并未圆见自性般若、亦即实相般若,所以才有后来之:
祖以杖击礁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坛经》行由品第一)
前者讲到慧能作偈时,未彻悟,即未完全见道,“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慧能作偈后,五祖还要为其讲《金刚经》,证明其未圆,未彻,未真正见性。而在这里,慧能圆了、彻了、见性了。这里先要略谈《金刚经》之相关情节。《金刚经》里“应无所住生其心,”出现在“庄严净土分第十”中,而在这之前的九个环节中,是如何得出“应无所住生其心”之关键语句呢?在“善现启请分第二”中,长老须菩提恭敬问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世尊的回答很直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之总起,在释佛看来,真正的安住境界是“如是”境界,真正完全地降伏心念之境界亦是“如是”境界,何为“如是”,如来者,诸法如义,如来者无法不如,如来者,如如不动。因而“如是”境界亦即不立文字之当下即是、不立纤尘之真如境界。因此释佛才可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总起之后,才具体而有步骤地解决“色”、“空”的本来面目,以及“色”与“空”的实际关系,这是“如是”境的两个必要前提。在“正信希有分第六”里,“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在“无得无说分第七”里,“如来所说法,应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此等等,释佛在这里为我们阐明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见地,亦即阐明了初关色空各自抉择之顿见、重关色空一体同时抉择之不全圆顿见。因此,到了“庄严净土分第十”中“应无所住生其心”语句时,慧能方能牢关大悟。可以说,慧能的整个见性过程仅两关,即前面之顿悟及这里的圆悟。也可以这么说,慧能之重关和牢关是一体而行,可见其悟性的了不得。而所谓的“无所住”为无为境,而真正的无为境即为非思量、非造作之境,亦即当下即是、不落文字之境。在此境地里,空圆,有亦圆,一切万法皆本心所印,唯此境方可了了空有,空圆即有圆,所以才能“生其心”。
因此慧能在听了五祖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心,而“心”为色空之当下了不可得,这就是“当下即是”之更原始些的解读。 “人人尽有这个字,所以不能自见,说亦不信,须是亲见,方能信也,唤作一字法门。”(《大颠和尚注〈心经〉》)八万四千法门,多种方便,皆从此个“心”字流出。“而本自清静,本自不生灭,本自不动摇”皆是自心不立文字、非思量之当体即是境界,有思量,有来去,即有生有灭,有动有摇,即不能毕竟清静。本自清静即能本自具足文字,即能“生万法”,“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坛经》行由品第一)“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般若品第二)“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坛经》机缘品第七)“夫《心经》者,未曾举起,已是分明,何须注解。”(《大颠和尚注〈心经〉》)
从上可看出,慧能目不识丁,但能见性,即能现量无师智自然智。神秀饱读诗书,但还只能呈现凡夫智。“是福德即非福德,故如来说福德多。”(《金刚经》依法出世第八)“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福德多。”(《金刚经》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再看《坛经》里,六祖弟子见道之情形,从中可更具体地解读不立文字。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即如是,吾亦如是。(《坛经》机缘品第七)
怀让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师傅,属六祖“一花开五叶”之一。是慧能认为之“决定无疑,堪任大事”者。再看其见地,当六祖问其“什么物,恁么来”时,他的回答是“说似一物即不中”,带什么来呢,看似带了一颗心来,但一切了不可得,“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何为不见一法?万缘俱绝,永休我人,毕竟空寂,行如鸟道,坐若太虚。此亦即不立文字之绝来去双运,不生不灭之境,因而,六祖云“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即如是,吾亦如是。”师再问:“还可修证否?”前者谈到本自圆成,本自具足,何来还问“修证”?原来,见道与证道是两码事,无为果必要有无为因,见道只为证无为果之因,“觉性本圆,妄法本寂,实无所修,但以初悟之人,迷习难为顿息,是以请于无修之中,假说修习方便。”(《宗密注〈圆觉经〉》)佛本是而勤修,惑元无而须断,“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四家语录之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如何修?但不污染自性,即为修。“若开悟顿者,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坛经》般若品第二)因此,“污染即不得”,即为自心之应物应事过程中的法身显现,不从外修,属于内熏,属内心之清静安住境。随时安住具足相续,方易有自在法身。
永嘉玄觉禅师……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坛经》机缘品第七)
永嘉玄觉亦为六祖之五叶之一,有《证道歌》盛行于世。永嘉禅师参拜六祖前,已“看维摩经,发明心地”,禅之悟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仅差一验证而已。因而,其参拜六祖就显得潇洒多了。因为,其与六祖仅就悟境而言,已是“同此心,同此理”。再者,禅门亦有掺水不实者,试过才知,过招才晓。因而,初见六祖,仅“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当六祖斥其“生大我慢”时,他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真正出家人,具足智慧,善能分别一切轻重缓急,大行不拘细谨,无常何其迅速,解决生死才是大事。如何解决生死大事?六祖便言:“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在六祖看来,最圆满之解决生死大事,自觉觉他,便是当下安住空寂,毕竟空无去来。而永嘉的见地为自性本自无生,本自寂灭,了义圆境本无来去何有速度?师曰,如是,如是。六祖验证了永嘉之圆顿觉悟之境界,心心相印,心心不异。于此,永嘉方具足威仪礼拜,“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南岳怀让禅师语)至于后者之“本自非动”、“无生之意”、“仁者自生分别”等语句,皆是显示真如境地之如如不动、不立文字,且具圆了智慧之境地。因而,时人称永嘉禅师为“真觉焉”。
与上二例相反之例子,前者不立文字,后者立于文字,亦即有文字相可得,不能如是如是显现无师智、自然智。
僧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祖呵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是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坛经》机缘品第七)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坛经》般若品第二)如来出世,现种种相,说种种法,广辟玄门,目的为诱导群品。“悟在于心,非关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尽是化门接物度生边事,设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非关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黄檗禅师传心要法》)《法华经》出现于世,为度群迷,使其了然自心,明白本性,因而,读《法华经》,须口读心行,“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坛经》行由品第一)佛是心做,不是口做,心即是无一物可得,心即是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但法达不明此理,执着经论名数分别,“若心取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第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因而,法达并不见自心如来,不能具足智慧,于是,不能转《法华》,而被《法华》所转。因此,所谓的教外别传,即经教通过言语文字让众生去明自性,了本心如来之无住无得,“汝若得其经意,与吾偕行”,而不是说经教文字的外面另要传什么秘密,若是经教文字的外面另去传什么,如来讲四十九年法,岂不愚痴浪费?有这样的如来吗?只是文字为标月之手指,得“月”而圆满一切,因而得鱼忘筌,得渡忘筏。文字仅是方便度门,因而法达领旨后,“亦不辍诵经”。
神会亦为六祖五叶之一,六祖灭后,其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有《显宗记》。下面是《坛经》里有关神会的一个片段。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你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坛经》顿渐品第八)
此情形中的神会,虽知万法皆空,但未能作实际安住,亦即就此段话语判断,神会此时之表现更倾向于文字般若。佛本是自心去做,那得自文字中做。“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是佛?祖(马祖)曰:为止小儿啼。”(《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在马祖看来,佛法文字仅为止小儿啼之“黄叶”,而解决生死大计之“黄金”是本心,莫错把“黄叶”当“黄金”。再看六祖道“无名无字”,神会便道“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很明显是倾向于由忆持、逻辑、意言分别而来,亦即其尚有文字惑,尚有文字相可得,更勿论不立文字、非思量境界之如是如是当下安住。释宝志公禅师言:“未了之人,听一言。只如今,谁动口。”因而,此情景之神会,仅为自己带了个“茆盖头”,虽名神会,实未心领神会,所以六祖唤其“知解宗徒”。
《祖庭事苑》五曰:“传法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后达摩祖师单传心印破执显宗,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住住谓屏去文字以默坐为禅,斯实吾门之哑羊尔。且万法纷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犹通也,岂拘执于一隅。故即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即尔,余法亦然,所以为见性成佛也,岂待遣而后已也。”
中国禅宗,从达摩以《楞伽经》为教授手段至五祖教人念诵《金刚经》便可入道,因而,尽管他们皆如如了知佛是心做,师徒相承之根本在于心心相承,心心不异。但他们从不排斥经教在教人明心方面的重要方便作用。“达摩西来一字无”,如来者,说具体点,其实为心灵的一种圆满自在境界,而要达到此种境界,经教则为极其系统而完善的引导诱发要素。因而“一字无”显示的只是真如境界的不沾不执,亦即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但要达到“一字无”境界,经教的启发度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道宣《续高僧传·可大师传》)“大师(五祖)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坛经》行由品第一)而到了六祖慧能,由于其特殊因缘显现于目不识丁,由他而始才不特别教徒弟看某部经典,但他从来不说不要文字,屏去文字,因为他亦是由文字,即《金刚经》得见自性的。“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坛经》般若品第二)愚痴之人,闻空着空,闻不立文字,便不要文字。法性圆融,具足文字。法身处处,事则从它事,理则从它理,文字则从它文字,本自不缚,其谁求解?“道须流通,何以却滞,心不住于法,道即流通。”(《坛经》定慧品第四)于文字而不立文字,于一切法而不立文字才是究竟,岂遣去文字,方为不立文字?一切法皆是佛法,而到文字就行不通?语默动静皆是本心,皆是本佛,谈话说经就不是本心、本佛?舍利舍宴坐林中,百物不思,唯令念绝,可被维摩所呵。所以如来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经》离色离相分第二十)表明的是说法者,知法如幻,无说法之执,仅假名为说法。并不是如来什么也不说,否则三藏十二部何处而来,说足四十九年大悲度生,难道不算说法?只是不沾于说,不沾于分别,随缘而作。“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坛经》顿渐品第八)所以如来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六祖不立文字,却留有一部《六祖坛经》,达摩不立文字,却有《达摩四观行》等。
还有人认为,不立文字,即是言语文字说不清楚,其认为佛法超越于思想意识,不是言语、文字、理论可以尽其极致之“微妙法门”。这样的言语,把佛法弄得玄乎其玄。我们这么说就清楚了,有文字可得,或者尚有一尘之沾,即不可能现量真如之圆满自在福慧,亦即有极之心不能至无极之境。佛为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之真如境界,其是法身之无为而无不为,“三身四智体中圆”,弥纶六极,细入无间,在圆满自在之中又如何不能尽其极致地言说、经教、理论呢?若不能具足微妙圆满之文字、理论,又何能“狮子吼,无畏说”(永嘉玄觉《证道歌》),又何能“出没舒卷,纵横应物咸成事宜!”(慧海禅师《顿悟入道要门论》)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 燕,广东湛江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六祖坛经》。
[2] 实叉难陀译之《大方广佛华严经》。
[3] 鸠摩罗什译之《妙法莲华经》。
[4] 玄奘译之《心经》。
[5] 求那跋陀罗译之《楞伽经》。
[6] 鸠摩罗什译之《维摩诘所说经》。
[7] 大颠和尚:《大颠和尚注〈心经〉》。
[8] 达摩祖师:《达摩血脉论》。
[9] 达摩祖师:《达摩悟性论》。
[10] 佛陀多罗译之《圆觉经》。
[11] 大珠和尚:《顿悟入道要门论》。
[12] 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
[13] 普济编集之《五灯会元》。
[14] 善卿编之《祖庭事苑》。
[15] 道宣《续高僧传》。
[16] 《佛学大辞典》,上海佛学书局,1999年版。
[1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18]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6月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