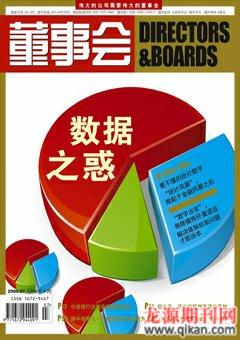“数字出官”,根除痼疾任重道远
“数字出官”何时休?
社会上曾经流传过一段顺口溜叫“四大虚”:领导的肾、秘书的稿、小姐的感情、统计局的表,其意虽偏激,但由此不难窥见统计数据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受创之深。
统计数字没有公信力无疑是可怕的,统计工作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管理中的重要职能,准确的统计数字无论是对决策、规划,还是对问题的总结、发现,都将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参考作用。然而,统计造假,数字“注水”之事屡有发生,屡禁不绝。让中央高层领导对统计数字“很不放心”,反复要求下面“讲真话”。这种“统计无信誉”的状况如果不纠正,一步错,则步步错,最后或会酿成不可设想的可怕后果。
记者从这次《统计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上发现:从近年来全国统计执法检查的情况看,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约占全部统计违法行为的60%。这类造假行为无非是三个来源:地方领导、统计机构人员、统计调查对象。
为何三者之中,地方官员造假的民愤如此之大?恐怕不是老百姓存心要和官员过不去。从现实情况看,各级统计局包括国家统计局旗下调查总队大都有统计执法队伍,对调查对象主动造假的情况,本来即是这个队伍严查严打的范围,这在体制内基本能解决。而对于统计机构,从绝大多数统计人员来讲,作为一个职业统计工作者,内心里都想以真实的统计数据示众,不愿被人背后“戳脊梁骨”;而国家统计局层面,更不存在造假的直接动力。
因此,从体制机制的角度讲,三者中,只有地方政府官员的造假行为所受约束最小,也只有地方官员有能力一手遮天地实施这项“集体性”违法行为。正如原国家统计局一位副局长所说:“如果面对的各级领导需要的是真正的数据,那么中国的统计工作并不难;如果面对的各级领导需要数据来证明什么,那么统计工作确实太难。”
某地市统计局执法检查大队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坦承,“我们主要的工作还是针对统计调查对象弄虚作假的行为处以罚款,或者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查处地方领导干涉数据的案件还没有碰到过,即使地方领导要求改数据,那也只能叫做调整,不能叫造假。”“调整”一词,显然将地方官员的造假行为给“洗白”了。毕竟,统计是一项复杂工作,正常工作中也会有调整,反正外人也实难去查证此“调整”和彼“调整”的详细差别。
众所周知,让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千夫所指的“统计罪人”的造假行为背后,其实有着强大的动力,即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机制,不客气地说,就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长期以来,“效率优先”的发展观使中国偏重经济发展,甚至在一段时期、一些地区被扭曲为“唯GDP论”。官方统计也受此影响偏重经济指标,而轻视甚至忽略了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
曾有篇文章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地一位乡长对文章作者说,由于多年来吃够了虚报数字的苦头,他们决定告别“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习惯,如实上报成绩,结果报了三次都被县里退了回来,并受到主管副县长的严厉批评。主管副县长说,他们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没有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要他们回去“解放思想”,修改报表。否则,他们就将面临取消年终奖金甚至撤消职务的后果。这位副县长的逻辑显然是:弄虚作假就是讲政治,就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着想。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也说过他的感受:“我曾率队去四川、重庆、贵州等地进行执法检查,碰到很多类似情况。比如说,你是统计人员,我是地方官员。我会说,你看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我们这个地方,怎么他们的人均收入比我们还要高?他们的工业还不如我们,怎么我们的总产值比他们低呢?”贺铿说:“你作为统计局长就得好好考虑,如果你不能领会领导的意思,很可能就会丢掉‘乌纱帽。现在统计工作就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地位。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相当普遍。”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嘎玛就指出,下面确实存在瞒报、虚报的情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政绩与统计有直接关系,年初下达各项指标,比如财政收入指标、农民人均收入指标,如果完不成,要采取很多措施以争取达到上面的要求。二是发展比较快的地方瞒报的现象比较普遍,如财政收入超过预计的部分不报,只报预计完成的部分。问他们为什么不报,他们说今年一下子报多了,明年如果完不成,领导会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反之,比较穷的地方怕领导说没有完成指标,本来没有那么多数字,到年底的时候有些部门领导和统计部门经常一夜一夜加班调整数字。这些问题都比较普遍。
往往是,在下达计划指标时,“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上报统计数字时,“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 5月6日,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也承认,统计造假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可能还有加重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通过各基层单位的统计机构或统计人员,按照统一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再由各系统、各地方的统计部门逐级汇总上报而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单位、乡(镇)、县(市)、地(市)、省(市)、国家统计局六个环节。由于环节多,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失了真,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失真的数据;如果数据在多个环节受到扭曲,那么最后汇总的数据就必然是多重扭曲了的数据。
一步错,步步错,统计造假会酿大祸。可以肯定,在作为干部业绩考核指标的统计数据不能独立之前,统计数据质量的这个“硬伤”势必难以消除。
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今年提出GDP增长8%的目标,与之对应,许多地方都提出了高于8%的经济增长目标,形成了巨大的政绩压力,也埋下了巨大的造假冲动。
为此,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甚至建议,把GDP指标从地方指标中取消,地方政府只管卫生、教育、就业、环保等硬性指标,只对环境和公共服务负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委员认为,目前,我们对统计数据或统计工作赋予了很多不属于其范围内的功能。所以,首先要保证统计数据使用的独立性,主要用于形势分析等经济管理,不能把它和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以减少弄虚作假的动力。
有业内专家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因处于争取中央投资大干基建的高峰期,一些地方政府之前可能说得“灾情”惨重,之后说得花团锦簇,以显示治理之功,证明中央给本地的投资非常英明。
无论如何,根本之道在于破除其背后的利益驱动,如果地方政府的GDP数字不再是官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则“数字出官”可破,统计造假的冲动也可渐除。
“命门”被扣:独立性缺失之痛
不少西方国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事情有些奇怪,因为在它们看来,一个独立的统计系统的数据是不可能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干涉的。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地方统计系统缺乏独立性。
翻看《统计法》第三条: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国务院设立国家统计局,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统计工作。正是这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被指责为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体制根源。
在这种体制下,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总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统计数据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相关,是地方干部的“政绩单”。而这张“政绩单”由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怎能不遭破坏?这也是导致乡、县、地(市)三级为了追求“政绩”,或凭空编造统计数据,或授意和指使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的原因,有的还规定上报统计数据必须由党政领导研究决定。
就连上海,目前仍有部分中心区的统计局挂靠在区发改委,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区县政府统计部门的独立性。
不但如此,现行《统计法》第七条还规定: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如果发现数据计算或者来源有错误,应当提出,由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和有关人员核实订正。这显然为一些弄虚作假的地方干部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成为造假者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是必须正视的法律漏洞。
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就认为,当前统计法实施当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现在由于统计部门隶属于同级政府来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地方的领导进行干预,令地方统计机构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当然,国家统计局也曾在体制机制上“大动干戈”,2005年年底其将原属于地方统计局代管的城调队、农调队和企调队三个调查队纳入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在国家统计局成立了城市司、农村司和服务业调查中心,地方成立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这些地方调查队伍的财务、人事以及实际调查项目直接受国家统计局管理。
统计局的目的显然是为保统计真实,比如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以及工资价格、失业率等等,都由国家统计局直接获得,地方只能共享。尽管2005年修订后的《统计法实施细则》曾规定了调查总队统计以及执法的权限,但是这个组织架构设置还没有写进《统计法》。
据了解,目前地方统计局可以自己统计一些数据,如工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利润率等。上述数字,为了保证质量,比如GDP,目前需要由国家统计局联合审查后才能发布。但即便如此,统计局的GDP数字和地方的GDP总数仍不一致,尤其后者虚报现象相当严重。
统计界专家建议,及时改变现行统计机构内部体系,实行省级统计部门对地(市)、县统计部门垂直管理,实行编制人员、经费、工作任务统一配置,干部由上级统计局任免,可提高各级统计部门的抗干扰能力。
贺铿曾多次提出,可以学西方,地方需要的一些数据由地方统计局提供,但是地方可以不要统计局,由国家统计局派给省的统计局做,这种行为可以是有偿服务,如果国家财政把钱给足了,也可以是无偿服务。考虑到有些省想保持独立性,也可以有自己的统计局,但是要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为准。这样,“数字出官”就出不了了。
贺铿认为,要想把统计工作做好,就要有一套独立统一的统计系统,没有哪国的统计系统可以分散到各级去做。国外甚至连财政和银行从事统计工作的一把手都是由国家统计局委派的,绝对服从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领导。我国的《统计法》在体制上也要解决该问题。
无论最终如何定位,着眼点都应在于,从体制机制上增强统计机构的独立性、尽力消除地方政府的干扰,从而根治统计数据失真的体制“痼疾”。
“统计新法”仍难斩断干预之手
可喜的是,2008年年底提交全国人大一审的统计法修订草案中强调,修改重点是:完善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的法律机制;加重对领导干部人为干预统计工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参与弄虚作假、调查对象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草案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的“三个不得”,即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拒绝和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而且,草案取消了现行统计法关于“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领导和监督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执行本法和统计制度”的规定。取消了现行统计法中“如果发现数据计算或者来源有错误,应当提出,由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和有关人员核实订正”的规定。
特别是,统计局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和公务员主管部门推出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也是应对干预数据行为的重武器。而以前,《统计法》对于官员干预行为的制约是软弱无力的。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统计学权威对记者表示,新草案和《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尽管在处罚力度上进步不小,但是,统计独立性问题的根源依然是体制机制问题,也就是在机构、人员、经费上保证统计系统独立性的问题,以上两法案依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要在实践中斩断干预之手恐怕很难。根除体制痼疾依然任重道远。
配套机制亟待完善
除了难以根治的体制机制问题,统计经费、基层统计力量薄弱和提高统计科学性等配套机制也亟待完善。
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列力汗・马米汗认为,经费投入不足是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县以下统计部门经费非常困难。统计法草案加入了保证县级以上统计机构统计经费的规定,但是县以下统计部门经费却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邹萍也建议,对统计经费保障问题要有明确规定,比如全国性普查,应该直接由财政给予保障。
而问题是,现行统计法中没有关于统计业务经费的规定,在开展大型统计调查时,统计业务经费通常实行分级负担办法。由于各地的财力和对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差别,不少地方的基层统计部门严重缺少统计业务经费,开展统计工作很困难。
基层数据采集困难,人员配备不充足同样被认为是个大难题。一位基层统计人员告诉记者,以居民收入调查为例,由于是采取抽样统计的方式,抽到的居民是随机的,因此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信息搜集首先就会遭遇到信任问题,为了建立对方的信任感,经常需要三番五次的走访和电话联系。此外,由于收入调查材料极为复杂,每天需要登记收入和支出,小到一袋酸奶、一根油条的支出也要登记,会给受访者生活增加极大的麻烦,因此需要做很多说服工作。
而我国目前基层统计力量却很薄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龚学平就表示,我们国家统计队伍呈巨型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严重制约了政府统计工作的发展。区县统计局的统计人员明显不足,编制不够,兼职太多,一个人要做几个统计专业报表,经常加班,没有时间进行统计分析。至于乡镇、街道统计机构的设置,以及统计人员的配备更难以保证。比如乡镇在机构改革中把统计站撤掉了,统计工作放在乡镇经济管理事务所。乡镇统计人员在开展统计工作时,企业把经济管理事务所当作中介机构,严重影响了乡镇政府统计的权威性。
“目前区县一级政府统计机构和乡镇、街道的统计机构,其力量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越来越繁重的统计任务,这些状况如果不用法律的手段加以彻底改变,势必对我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发展形成重大障碍。应抓住这次《统计法》修改的契机,加强基层基础统计队伍的建设,彻底改变我国统计人员队伍呈倒金字塔的现象。”他说。
此外,统计科学性也亟待加强。统计方法的改进与统计数据的分析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科学而详实的统计方法与犀利的分析能力,统计局会被假数字蒙蔽。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就认为,目前有一些统计指标不太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登记失业率,从公布的统计数据上看,登记失业率并不高,但是社会反映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统计的分子、分母都有一部分就业人员被撇在外面,这就不能反映我们全社会的实际就业情况。
当然,统计局官员正在作出努力。近日,许宪春表示,零售额数据存在不足之处,这印证了经济学家认为的该数据并不是反映中国家庭消费情况的可靠指标的说法。许宪春坦承,官方公布的零售额数据包括一些不能被视为消费者支出的项目,如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对象的零售额,建造住房用的建筑材料——它其实应算作家庭投资的一部分。
马建堂也表示,为了进一步夯实我国统计的基层基础,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加强基层统计机构建设及人员配备,另一方面要健全统计的制度方法和标准分类。“对于一些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过去没有但需要迫切建立的,一些已经建立但与国际通行做法不尽一致的统计项目与方法,统计系统正在着手改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