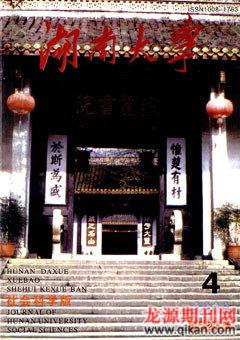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殷 慧 肖永明
[摘要]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输、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祧庙;永嘉学派;礼学理学化;朱熹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4-0021-07
宋绍熙五年(1194年)闰十月七日,朱熹上《祧庙议状》就孝宗祔庙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是朱熹在朝四十六日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朱熹晚年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涉及昭穆次序、始祖尊卑、捕袷祭享等礼制问题,加之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学术派别的暗中较量,宋代太庙之争断断续续长达二百多年,最终以朱熹议祧庙失败而结束,正了太祖东向之位。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自宋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论及。对于朱熹在祧庙议中的表现,学者们也多有评价。如马端临认为朱熹力主僖祖不祧之议,“则几于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束景南先生认为朱熹参与的“这场祧庙争议,不过是以僖祖为始祖还是以太祖为始祖的无谓争论”,并且导致了道学内部的分裂。的确,从整体情形来看,议祧庙不论对朱熹个人的政治生涯、学术思想的发展还是道学群体的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说朱熹固执难化,这不是与他一贯主张的因时制礼有冲突吗?朱熹为什么要冒着理学阵营分裂的危险不顾一切地来讨论这件事情呢?在桃庙议中朱熹到底要坚持什么?这一事件与朱熹晚年不遗余力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试图从学术分歧、政治纠葛以及礼学思想等角度来深入考察朱熹议祧庙的动因,以期确定祧庙议事件在朱熹礼学思想中的地位。
一制度与义理——与永嘉学派的礼学之争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嫡、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这从朱熹及其后学对祧庙议的记载和评议可以明显看出。朱熹说:“赵汝愚不以熙宁复祀僖祖为然,给舍楼缔、陈傅良又复牵合装缀以附其说,其语颇达上听。”据李闳祖记载:“祧僖祖之议,始于礼官许及之、曾三复,永嘉诸公合为一辞。先生独建不可祧之议。陈君举力以为不然,赵揆亦右陈说。”这表明,赵汝愚、陈傅良和楼缔是朱熹在祧庙议中的主要对手,而陈、楼二氏主要承担了理论论证的工作。关于这点,楼翁也不否认:“艺祖东向,宗庙大典,集议至再,始正百年之礼。而台谏有异论,输极论之,丞相赵公宣旨,蝓又执不可,公从旁力赞其决,而事遂定。”正是因为陈傅良在太庙议中为赵汝愚、楼缩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精神支持,因此才能使赵汝愚迅速作出决断,祧迁了僖祖,正了太祖东向之位。
陈傅良曾撰《僖祖太祖庙议》一文发表自己对太庙祭祀的意见,相当自信地认为:“汉魏以来,诸儒考经不详,或得或失,王、郑二家,互相诋毁,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专以经为断,以赞庙议之决。”此文以博引经传、力求考据的形式论证了另立别庙的合理性,陈傅良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讨论僖祖该不该祧迁的问题,而是提出僖祖从太庙祧迁后另立始祖庙并万世不毁的建议。陈傅良罗列经传引文,逐条加以解释,最后考证出周代的始祖庙和太祖庙是分开的:“周监二代,郁郁弥文,于是以受命之君为祖,继祖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目的在于论证宋代“受命之君”是太祖,“继祖”为太宗,而僖祖为“始封之君”。这样就为祧迁僖祖,但仍承认僖祖世世皆享的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朱熹看来,陈傅良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主要在于他所引用的经、注,都不能证明太庙和始祖庙是他所设想的方式分立的。因为在西汉和东汉前期,实行的一庙一世的制度,即不管是始祖、太祖、太宗,还是以下诸世,都是各自一庙,合为七数,故称“天子七庙”,但是自东汉明帝带头不另立庙,而以神主人世祖庙后,章帝也仿效明帝不立庙,汉代的太庙最终过渡为“一庙多室”体制,到汉献帝完成了“一庙多室、同殿异世”的格局,宋代沿用的就是此制。由于在两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嬗变,到了宋代已经弄不清到底一世一庙是周礼,还是后世沿用的一庙多室为周礼。而单从时间先后看,反而是“一世一庙”更加接近周礼。朱熹就抓住这一点批评陈傅良“今各立一庙,周时后稷亦各立庙”的观点,认为“周制与今不同,周时岂特后稷各立庙,虽赧王也自是一庙!今立庙若大于太庙,始是尊祖。今地步狭窄,若别立庙,必做得小小庙宇,名日尊祖,实贬之也!”朱熹认为,既然周礼是一世一庙,那么陈傅良所谓的始祖庙与太祖庙分立和宋代的所谓太庙完全是两回事,既非古制,也不符合经典原义。
陈傅良“以经为断”的论证过程,引用了《诗经》、《周礼》、《仪礼》、《尚书》、《春秋》等经典的原文和传、注。朱熹则一一加以了批驳。陈傅良曾引用《周礼·司服》:“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髂冕。大司乐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漤以享先妣。”并自注:“先妣姜螈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螈无所配,是以特立庙祭之,谓之围宫。”刘知父不解陈傅良引《田宫》为故事,朱熹的回应是:“《圈宫》诗,而今人都说错了。”
陈傅良引用《诗经》,认为“文武每庙各有乐章而后稷庙无专乐。则见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庙之列,于是有先王先公之庙”,“假如后稷为太祖,则不应但有郊乐而无庙乐。”那么肯定是存在先公先王之庙。陈傅良又举《春官宗伯·守祧》以及同属宗伯的“天府”两条经文及其郑玄注为证。陈傅良认为,将这两条经文注文连起来理解,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文武之庙”的“后稷之庙”。继续引用《仪礼·丧服传》的一条注文:“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表明,始祖和太祖所指不同。又举本条注文下马融、韦昭的两条注为证。总之,陈傅良意在证明始祖之庙与太祖之庙是分开的,现在的僖祖也应从太祖庙中迁祧。
据李闳祖记录,朱熹对陈傅良这种引用经文下小注的做法不以为然: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处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只如韦玄成《传庙议》,渠自不理会得,却引《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注云:‘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遂谓周后稷别庙。殊不知太祖与三昭三穆皆各自为庙,岂独后稷别庙。”又云:“后稷不为太祖,甚可怪也。”
朱熹认为陈傅良的庙议“皆是临时去检注脚来说”,而自己所论“都是大字印在那里底,却不是注脚细字”。因此,朱熹在所论《褚袷议》中只引用《仪礼》以及《礼记》中《王制》、《曲礼》、《檀弓》等篇中论述,并且引用《韦元成传》云“宗庙异处、昭穆不序”来说明汉制与周制已不同。又据叶贺孙记录,朱熹对陈傅良庙议所引文献逐一审过,认为多不可靠。总之,朱熹从观点到论据对陈傅良的太庙议进行了评点与批驳。
实际上,具体礼学分歧背后反映的却是陈傅良和朱熹在政治态度和学术主张上的不同。据《宋史》记载,陈傅良“于
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及是,因轮对,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之。……退以《周礼说》十三篇上之。”这是记述绍熙元年(1190年)陈傅良与光宗廷对的情景。由于光宗对陈傅良经史之学颇感兴趣,后来陈傅良将《周礼说》献给了光宗,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叶适曾言:“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这表明陈傅良“综理当世之务,考核旧闻,于治道可以兴滞补蔽”的学术,赢得了皇帝和举子们的青睐。朱熹对此高度重视、密切关注,曾向胡大时打听陈傅良廷对的具体内容。
陈傅良的《周礼说》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考虑,希望在经典中找到依据从而能为南宋统治者提供进行制度建设的良方。他曾说:“《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为谬,尝试者为大谬,乃欲一切驳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数十家如此者,去其泥而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亦几于理矣。”陈傅良认为,完美的制度近乎天理,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研究《周礼》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考证周制以为当代所用。而朱熹却认为:“如今学问,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采摭故事,零碎凑合说出来,也元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到说制度处,只‘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尝闻其略也。”就朱熹的治学取向喜好而言,他也非常注重考证功夫。但是朱熹以为考证也需建立在对圣人旨意和礼制中蕴含的义理完整全面的把握上,同时应该像孟子那样,信信存疑,如果拘泥于尚未了解的制度,一味采摭故事,就会陷入繁琐零碎的境地。
有学者曾分析朱熹与陈傅良学术分歧背后的原因,认为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求制度之学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陈博良认为从制度到制度就几近天理,而朱熹则认为从理会身心出发去体悟周制中蕴含的天理,才是正途。朱熹认为如果不能把握、体认天理,就无法理会《周礼》的精妙完美之处。陈傅良的弟子曹叔远曾在绍熙二年来竹林精舍问学,朱熹曾明确表示:
曹问《周礼》。曰:“不敢教人学。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舍做底,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而令且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朱熹在给胡大时的信中也指出,“君举先未相识,近复得书,其徒亦有来此者。折其议论,多所未安。最是不务切己,恶行直道,尤为大害。”总之,在朱熹看来,陈傅良之学多重制度经史,不重身心义理之学。重制度经史,不免照搬成制为世所用,表现为功利的倾向。在祧庙议中,朱熹认为陈傅良、楼翁二人主张的正太祖东向之位正是其功利主义倾向的表现。南宋高宗无嗣,选太祖后裔孝宗承继大统,这就导致当时朝廷上下开始重新理解并试图复兴太祖开创的以“祖宗家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而陈傅良潜心研究太祖建立大宋基业的丰功伟绩以及开创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各种制度,这无疑是顺应了当时统治者及士人不甘心偏安一隅而欲雪靖康之耻、求国家之兴的精神需求。陆游就曾发出:“今乃独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余年,太祖尚不正东向之位,恐礼官不当久置不议也。”许及之甚至发出“太祖皇帝开基,而不得正东向之位,虽三尺童子亦为之不平”的言论,虽被朱熹责为“鄙陋”,但也确实传递出当时朝廷及其臣僚群体欲正太祖之位的强烈要求。在祧庙议中,陈、楼二人作为讲究制度名物的专家主张正太祖东向之位,无疑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朱熹却认为,不能以功业来论庙制,如果现在正太祖东向之位,虽然暂时达到了恢复太祖至尊地位的政治目的,但这无形中却否认了自太宗以来的政治脉络,会导致“一旦并迁僖、宣两祖,析太祖、太宗为二之失”,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无益的。
另外,在朱熹看来,如果要从功业来说,僖祖生产繁衍并培育了优秀的子孙后代,这就是功业。朱熹引程颐之说,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安得为无功业?”那么朱熹之意非常明显,承认僖祖是始祖,是太祖、太宗两脉共同的祖先,不要用功业去衡量僖祖与太祖,有利于团结高宗和孝宗两脉的政治力量,增强统治内部的凝聚力,这才是百世之利、礼制之义。因此从朱熹议祧庙中针对永嘉学者的功利主义倾向提出“僖祖不可祧”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礼学重义理的解剖,这与其一贯主张学者应首先明义利之辨是相符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熹尖锐的批评和强烈的态度相比较,无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政治人事上楼、陈二人对朱熹却是宽容、尊重的。陈傅良在著作中极少明确地批评或反驳朱熹。但为什么朱熹会在议祧庙上对楼、陈进行毫不留情、不遗余力的批评呢?宁宗即位后,赵汝愚首荐朱熹和陈傅良,至少在赵汝愚看来,朱熹和陈傅良同为当时的硕儒。两人在祧庙一事上各持己见,既是向来学术取向不一所致,同时也是各为自身学术地位而争。朱熹力主以僖祖为始祖,其祭法“不用汉儒之说,刻画周制,禁后王之损益”,反对毁庙。永嘉学派以研究名物制度的礼学为长,关注汉唐以来的典章制度名物的历史沿革。在祧庙议中最终以永嘉诸儒的主张取胜,这无疑给朱熹的学术自信以重创,因而不惜辩口利辞。永嘉学派注重“内外交相养成”的思想建构,尤其注重“外5E"层面的制度建设,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研究礼仪制度,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士大夫集体对南宋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对于同样致力于用学术来引导、影响政治的朱熹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或者警醒。
朱熹意识到明析礼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早年朱熹曾发出“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的感叹,在州县郡任职时朱熹主要推行礼仪,强调因时制礼,其目的在于向下推广实施礼仪。而在朝参与国家礼制讨论,朱熹发现皇家礼仪之难不在于行之难,而在于难以行得正确、适当。出任朝廷职位之前,朱熹主要以教学生活为主,只有短暂的州郡、地县的任职经历,可谓秉笏披袍之日少,传业授道之时多。一旦进入朝廷层面的制度讨论,不免以自己所认为的大经大本来议论国事,没有注意到政治大势以及具体的制度沿革,因而受挫也是必然。议祧庙的失败使朱熹痛不欲生③,同时也给了朱熹一个反思学术的机会,对永嘉学派的批评与吸收也是重新清理、调整自身学术的开始。朱熹开始意识到自己孜孜以求的天理如果不能和具体的礼制结
合起来,终究难以服众。《仪礼经传通解》正是在朱熹百念俱灰、痛定思痛后正式开始编撰的,表明了朱熹强烈要求回归礼学本经的学术要求。
二私欲和学术局限——对赵汝愚的批评
朱熹议祧庙的主张,是得到过宁宗承认和肯定的。朱熹曾回忆宁宗亲口所说:“说得极好。以高宗朝不曾议祧,孝宗朝不曾议祧,卿云‘不可轻易,极是。”“僖祖乃国家始祖,高宗时不曾迁,孝宗时又不曾迁,太上皇帝时又不曾迁,今日岂敢轻议!”据黄斡《朱熹行状》:“上然之,且曰:‘僖祖国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迁,今日岂敢轻议?”其实,宁宗的态度并非如朱熹所言那么坚定。宁宗作为太祖后裔的新君,亟需在皇统问题上返本清源,正太祖东向之位无疑在政治上具有正名的作用。而且,宁宗也认为“朱熹言多不可用”。宁宗对祧庙的态度,表面上看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实际上最终还是倾向于赵汝愚、陈傅良的观点。
当然,朱熹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恰恰关键是被当时的丞相赵汝愚破坏所致。本来在朝廷或学界,大家都认为赵汝愚属理学同道。在此之前,赵汝愚多提拔服膺程学之士,对于朱熹所提倡的社仓法,也曾在福建数县推广。朱熹入仕经筵,也有赵汝愚引荐之功。无论在学术倾向和政治理念上,赵汝愚和朱熹应该是有不少共识的。可是他却生硬地拒绝刊出朱熹的奏议,并且在争议并未明朗化时就连夜拆毁了僖祖庙,并迁了四祖庙,使之成为既成事实,不再有任何商议的余地。朱熹后来曾气愤不已地对弟子们说:“赵子直又不付出,至于乘夜撤去僖祖室!兼古时迁庙,又岂应如此?”在给赵汝愚的信中,他还不无怨恨地说:“其罪不在楼、陈,而丞相实任之也”,并且失望而痛心疾首地表示不敢再与赵汝愚交往。前面提到的学者们关于导致道学内部分裂的判断正基于此。那么朱熹认为赵汝愚到底错失在哪儿呢?
首先,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赵汝愚不采王安石的庙议,早在朱熹议祧庙之前就有所反映。朱熹在朝廷时并不知情,有书为证:
“赵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后来到家检渠所编《本朝诸臣奏议》,正主韩维等说,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说于其下,此恶王氏之僻也。”
这般事,最是宰相没主张。奏议是赵子直编。是他当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将那不可祧之说,皆附于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许多要祧底话,却作大字写。不知那许多是说个甚么?
赵汝愚主编的《名臣奏议》是一部150卷的北宋奏议选集,收录了241位臣僚的1630篇奏议,约134万字。赵汝愚编此书时,朱熹曾建议他“只是逐人编好”@,但赵汝愚未加采纳,而是将全书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方域、边防和总议等12个门类;有君道、帝学、政体、慈孝、恭俭、总议等113个子目。清代学者就曾指出两种意见之间的不同:“以人分,可以综括生平,尽其人之是非得失,为论世者计也;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为经世者计也。平心而论,汝愚所见者大矣”。从总体来看,此书对于了解宋代政治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确实也达到了赵汝愚所预期的经世致用的目的。
在此书中,赵汝愚不同意王安石提出的“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与稷契疑无以异”,对于王安石的观点只以小字附注。朱熹认为赵汝愚在祧庙议上至少以下几方面没有认识到。
朱熹认为,赵汝愚之所以不能在祧庙议上与自己有相同的见解,主要是因为对王安石其人其学认识不足。1196年,在给张洽的信中,朱熹还在不断总结分析王学与祧庙议之间的关联:
所论新法,大概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谓胜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压诸贤,只是见理不明,用心不广,故至于此。若得明道先生与一时诸贤向源头与之商量,令其胸中见得义理分明,许多人欲客气自无处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与有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胜之流俗亦真有未尽善处,则亦非所以为天下之公,而自陷于一偏之说矣。顷见赵丞相所编诸公奏议,论新法者自有数卷,其言虽不为不多,然真能识其病根而中其要害殊少,无惑乎彼之以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庙一事,当时发言盈庭,多者累数千字,而无一言可以的当与介父争是非者。但令人只见介父所言便以为非,排介父者便以为是,所以徒为竞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论率定于一也。
朱熹在祧庙议中取的是王安石不能祧迁僖祖的观点,这并非表明朱熹就对王安石之学有认同的一面。但从整体来说,朱熹对王安石的礼学有着针锋相对的、深入的批评。朱熹认为二程的理学正是弥补或者挽救新学之失的良药。在祧庙议中,与其说朱熹取的是王安石的观点,不如说是取的程颐的观点。朱熹曾明确说:“庙议当时只用荆公之说,盖伊川先生之意也。”
程颐曾有《稀说》一文,赞同王安石所论祧庙的意见,认为“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朱熹在读了程颐的《丰帝说》后更加自信自己的祧庙主张为至当,撰文如下:
熹未见此论时,诸生亦有发难。以为僖祖无功德者。熹答之日:“谁教他会生得好孙子?”人皆以为戏谈,而或笑之。今得扬子直所录伊川先生说,所谓‘夸天下基本皆出于此人,安得为无功业,乃与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决之是非,于此乎定矣。
在朱熹看来,不能祧迁僖祖的建议虽然是王安石提出的,但得到了元祐大儒程颐的认同,因而可以作为天下之正理。朱熹认为,赵汝愚不能正确看待王安石之学,未能“识其病根而中其要害”,一味地以王安石所是为非,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掌握批评荆公新学的精义。
其次,朱熹指责赵汝愚“以宗枝人辅王室,而无故轻纳鄙人之妄议,毁撤祖宗之庙以快其私”。那么赵汝愚的“私”心在何处呢?由于赵汝愚是汉恭宪王元佐七世孙,也就是宋太宗长子赵德崇七世孙,是属于太宗一脉的。正是因为宗室的身份使他的仕途遭遇了种种尴尬。
乾道元年(1165年),赵汝愚在殿试中程文第一,孝宗按照当时的宗室管理政策,第一名必须取普通举人的传统,没有取他作状元。除了进士及第时的优异成绩,赵汝愚还是第一个省试知贡举的宗室,第一个被提拔到执政岗位上的宗室,并最终成为宋代第—个也是唯一的宗室宰相。这样的政治履历使得赵汝愚对自己的宗室身份总是小心翼翼,而这样的身份也不时受到了同时代官员们的注意。绍熙二年(1191年),他从福建入京,自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升任吏部尚书。虽然当时宗室任吏部尚书在宋代尚属先例,但此次升迁并未引来太大争议。1193年,当赵汝愚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时,监察御史汪义端反对,援引祖宗故事,以为没有用宗室为执政的先例,并且污蔑汝愚“发策讥讪祖先”。但这并未减少皇帝对赵汝愚的信任,反而命他兼权参政事。留正执政后,汝愚乞免兼职,乃除特进、右丞相。赵汝愚辞免不拜,说:“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仍乃命以特进为枢密使,赵汝愚又辞特进。孝宗将横,赵汝愚议横宫非永制,欲改卜山陵,与留正议不合。后来,韩馆胄欲
逐汝愚而难其名,有人提示说,赵乃宗姓,只要诬以谋危社稷的罪名就可以罢免其职,置其于不义之地。韩惋胄于是擢用曾向赵汝愚求节度使而不得的李沐上奏说“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乞罢其政”。总之,姓赵以及是太宗后代的事实使赵汝愚不免遭受种种非议,他也时常如履薄冰,不得不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唯恐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
那么以此为背景来看赵汝愚在祧庙议中刚劲果决的态度、连夜毁庙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他不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主张正太祖东向之位,势必会给早有睥睨窥觎之意的人更多把柄。而朱熹批评赵汝愚有私心也正基于此,认为其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无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礼制秩序。从朱熹一贯申讲的天理人欲之辨来理解,那就是因为赵汝愚没有克尽私欲,有挟势弄权之嫌,因而使天理蒙蔽了。眼光肤浅必然表现为行动中的小廉曲谨与阿世循俗。综合种种情形,我们认为朱熹还是过于严苛了。
朱熹与赵汝愚因祧庙议的分歧直接导致了道学群体内部的分裂,这给以韩健胄为首的官僚集团以可乘之机。因为赵汝愚的大力推荐,朱熹得以进入朝廷供职,但是“韩馆胄用事,既逐赵汝愚、朱熹,以其门多知名士,设伪学之目以摈之”。朱熹后来不无叹息地说:“庙议固可恨,然自有衬之,乃有大于此者,令人痛心。”这里所言“大于此者”一方面是指道学群体遭到了全面而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则是朱熹所倡言的理学学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朱熹刚烈倔直的性格而言,这种打击最终必然表现对学术的调整与反思,“一切从原头理会过”和逐一讲究礼文制度成为朱熹着力的重点,据《语类》记载:
先生言:“前辈诸贤,多只是略绰见得个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会者。须是专心致意,一切从原头理会过。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又如礼书冠、婚、丧、祭,王朝邦国许多制度,逐一讲究。”因言:“赵丞相论庙制,不取荆公之说,编奏议时,已编作细注。不知荆公所论,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讲究毁庙之礼,当是时除拆,已甚不应《仪礼》,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编奏议。今则诸人之学,又只是做奏议以下工夫。一种稍胜者,又只做得西汉以下工夫,无人就尧舜三代源头处理会来。”
很明显,朱熹将对赵汝愚的批评与讨论须一一从三代源头处理会礼文制度联系起来,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在朱熹看来,赵汝愚一生只在编奏议,而陈傅良、陈亮等学者,只做得西汉以来的史学工夫,仅仅满足于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而根本没有从表现三代经典如《仪礼》等中仔细体会人心义理。在祧庙议之前,朱熹自认为在道德性命之学上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议祧庙失败之后,朱熹在强调从三代经典中理会义理应该本着从礼文制度人手的原则,注重礼与理的统一,主张同时在刑名器数和道德性命上用力。
三礼学理学化——特色及其不足
宗庙祭祀主要表达追养继孝、敬亡事存、收族报本的礼意,具有安邦定国的象征意义,不外乎表现为亲亲尊尊的精神内涵。但是,历代对于什么才是太庙礼制中的亲亲尊尊之精神,却是一个聚讼不已、莫衷一是的话题。高明士先生分析中古的宗庙制度认为,自汉以来的发展,争议最多者即太庙与祧庙之设定,甚至始封君与受命君也被讨论,也就是如何来表现尊尊精神问题。到唐代终于确立所谓功德论,正面的意义,即以“德”来定位太祖不迁之庙,其相对意义,仍以“德”来制君,这是值得注意的礼制发展。从思想渊源来说,陈傅良无疑接受的是唐代以来所强调以及在实际礼制中践行的太祖功德论,也是在政治实践中试图体现亲亲精神;而朱熹着重考察的则是宗庙制度中所应该坚守的尊尊精神,主张跨越汉唐直奔三代制度精髓。朱熹深知“宗庙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的道理,议论祧庙的着眼点是“尊祖敬宗、报本返始”这一主题。自始至终,朱熹都紧紧扣住在宗庙祭祀、祧迁上该如何体现尊尊精神,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本返始”。
对于当时出现的三种主张祧迁的说法,朱熹都一一做了批评,其标准就是是否体现了尊敬祖宗的精神。第一,对于“欲祧僖祖于夹室,以顺翼宣祖所祧之主柑焉”的主张,朱熹认为“夹室乃偏侧之处,若藏列祖于偏侧之处,而太祖以孙居中尊,是不可也”。“藏于太庙之西夹室,则古者唯有子孙祧主上藏于祖考夹室之法,而无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孙夹室之文。昔者僖祖未迁,则西夹室者,僖祖之西夹室也。故顺、翼二祖之主藏焉而无不顺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则夹室者乃太祖之夹室。自太祖之室视之,如正殿之视朵殿也。子孙坐于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于礼安乎?此不可之一也。”朱熹认为让祖居偏侧之处,而让孙居中尊之位,不足以体事死如事生的宗庙内涵。
第二,对于“欲柑景灵宫”的说法,“元初奉祀景灵宫圣祖,是用篮簋边豆,又是蔬食。今若柑列祖,主祭时须用荤腥,须用牙盘食,这也不可行。”在祭祀时可能因为要体现差异而难以传递尊祖之意。“至于袷享,则又欲设幄于夹室之前而别祭焉,则既不可谓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当太祖神坐之背,前孙后祖,此又不可之二也。”
第三,关于“欲立别庙”说,朱熹认为太祖庙四周一带地步狭窄,别庙的大小也不好确定。尤其是袷祭时会引来许多混乱,引来更多的纷争。朱熹说:“如日别立一庙以奉四祖,则不唯丧事即远,有毁无立,而所立之庙必在偏位,其栋宇仪物亦必不能如太庙之盛,是乃名为尊祖而实卑之。又当袷之时,群庙之主袷于太庙,四祖之主袷于别庙,亦不可谓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同时朱熹认为,当时的临安太庙本来还不足以体现东向之位为尊。他说:
其说不过但欲太祖正东向之位,别更无说。他所谓“东向”,又那曾考得古时是如何?东向都不曾识,只从少时读书时,见奏议中有说甚“东向”,依稀听得。如今庙室甚狭,外面又接檐,似乎阔三丈,深三丈。祭时各捧主出祭,东向位便在楹南檐北之问,后自坐空;昭在室外,后却靠实;穆却在檐下一带,亦坐空。如此,则东向不足为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东向乃在西南隅,所谓奥,故为尊。合祭时,太祖位不动,以群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飨,此所以有取于东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无所自出。
朱熹此论的目的在于强调,既然目前的太庙东向也未必体现至尊,也就没有必要一定正太祖东向之位。
总之,在朱熹看来,祧庙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体现尊祖之精神。而在僖祖与太祖祖孙关系之间,无疑僖祖为至尊,因此礼制变动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是否体现僖祖的至尊地位,是否表达太祖的尊祖敬宗之心愿。如朱熹指责如依郑侨祧迁僖祖之说,“特以其心急于尊奉太祖三年一袷时暂东向之故,不知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庙威灵,相与争较强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摈,傍徨踯躅,不知所归,令人伤痛不能自已。”又上推设想当年太祖追尊四祖之心,相比于今日群臣之议:“尊太祖以东向者,
义也;奉僖祖以东向者,恩也。义者,天下臣子今日之愿也;恩者,太祖皇帝当日之心也。与其伸义诎恩,以快天下臣子之愿,孰若诎义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朱熹认为体察、抚慰太祖敬宗尊祖之心比满足、顺遂当今臣子之心更能体现宗庙祭祀的真正用意。
在朱熹看来,继承太祖之统绪不在于是否让太祖正东向之位,而在于思考行太祖之礼乐,对于太祖所尊所亲的祖宗,更当爱敬兼尽,事死如生,方为至孝。在提出第一种庙议方案时,保留僖祖,祧去宣祖、真宗、英宗,太祖、太宗仍为一世。朱熹认为这样在“三岁袷享,则僖祖东向如故,而自顺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则于心为安,而于礼为顺焉。”不仅强调人心之体察,朱熹还以人情论庙制,认为庙室的建设应该与生前祖先所居相衬,如果随意让其处之夹室或简陋的别庙,就很难体现宗庙建设的本质内涵所在。朱熹说:“人情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损其数,孝子顺孙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从这些论述看来,朱熹均是在以心体心,以心说理,以人情推定礼仪。
朱熹想以理服人,却遭致以理说礼的惨败。这似乎可以看作宋代以降礼学理学化之后,理学家论礼的某种预示性的结果。“礼学理学化”的特征在于学者论礼时不免刊落制度、名物、典章而直抒其意;而且一旦将“礼义”从具体的制度中抽离出来,就容易造成以“理”代礼,从而产生对礼的误解与扭曲。王安石、程颐、朱熹之所以会在祧庙议上达成共识,是因为他们在追求礼义上特别是在体认宗庙制度中的亲亲尊尊精神时无疑倾向了尊尊,认为这是天理人心之使然。朱熹以天理、人心、人情来论礼制时,不免忽视宗庙礼制在现实政治中演变的历史轨迹。
尽管朱熹议论祧庙在当时和后来还是有不少人赞同或服膺,如赵彦卫也认为“撤安陵,而止有八庙,虽号为正东向之位,而临安庙制有堂无室,卒无东向之位可正。”清代汪师韩在维护朱熹庙议的基础上,仍以心、理、情论宋代宗庙之礼王夫之也撰文体察朱熹议论祧庙之用心,认为朱熹“独于祧庙之说,因时而立义,诚见其不忍祧也”。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朱熹在设计具体的祧迁方案时礼学工夫有不足之处。朱熹前后曾提出两种庙议方案,第一种方案,保留僖祖,祧去宣祖、真宗、英宗,太祖、太宗仍为一世。第二种方案是“不若上存僖祖为初室,东向如故,而迁宣祖一世于西夹室,太祖、太宗二室亦为百世不迁之庙,将来永不祧毁。”这两种方案都与当时现行制度差异过大:首先是确定世室,已列的太祖、太宗、仁宗以及待六世亲尽的高宗,将突破崇宁九庙之制而使庙数再次增加;其次,迁祧真宗、英宗,与时人观念差别太大;再次,虽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同为穆庙,但哲宗与徽宗,钦宗与高宗皆是兄弟,却昭穆不同,前后标准歧异,自然难以服人。朱熹后来也提到:“当日议状奏刳,出于匆匆,不曾分别始祖、世室、亲庙三者之异,故其为说易致混乱。”
另外,朱熹关于始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与礼学、礼制不合。据李衡眉先生考证,古代昭穆制度中实无“始祖”这一称呼。东汉时的《白虎通》的作者班固与《礼纬》的作者们是宗庙之制中有“始祖”之称的始作俑者。即使隋朝以后,“始祖”之称已被普遍乱用于宗庙之制中。元、明两代仍坚持使用太祖这一称呼,而不被“始祖”之称所惑乱。很明显,朱熹作为一代大儒,仍然困惑于“始祖”之称,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称呼的历史渊源。据《旧唐书一礼仪志》记载,其实早在唐中宗时,张齐贤就曾指出:“太祖之外,更无始祖。”又据《旧五代史·礼志上》,五代晋天福二年(937)正月,议立晋宗庙时,御史中丞张昭远上奏日:“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又日:“自商周以来,时更十代,皆于宗庙之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无追崇始祖之例。”所以“始祖”议者,实不能成立。
因此,朱熹议祧庙失败似乎预示了礼学理学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在学术上很难致用,在政治上表现出不成熟与不合时宜。但是,朱熹超乎寻常的学术反思能力使得他在奉祠去国后的两年内,还在不断反思、讨论祧庙事件。1196年,朱熹正式启动私人修撰《仪礼经传通解》。朱熹意识到在考察具体礼制时也应注意礼本身的制度沿革,义理优先的前提应该充分认识到礼中所蕴含的理。如果不注意承袭原有的礼制规范,就容易导致混乱。这些反思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编撰《通解》所制定的体例中。后来朱熹在编撰礼书的过程中多提醒学者留意有关庙制、稀袷、郊社等问题,在讨论中多次提及关于祧庙的主张,足见此事对朱熹编修礼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