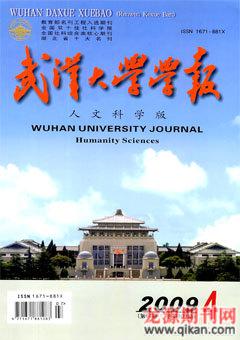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问题
周文华
[摘要]蒯因和怀特反对把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蒯因用他的整体论否定了这种区分的合理性。怀特则认为,某些陈述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分析的或综合的,二者就如温度高低那样只有程度之分。普特南则用定律簇概念来说明为何某些陈述不能二分。在这方面他们都没有重视句子与命题的区别。按照文化共同体与命题的关系,可将一切命题分为三类。句子也许不能二分,但任何命题原则上都是可以二分的,只要是相对于适当的文化共同体。
[关键词]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分析与综合的二分;蒯因;普特南
[中图分类号]B81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4—0486—06
一、怀特和蒯因对分析一综合二分的批评
把命题区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或把陈述句区分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在哲学史上曾经是显而易见的。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怀特(Morton G,White)和蒯因(wlIIard V,0,Quine)就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怀特的结论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下述观念:……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有截然区分。……不曾给出任何一个这样的标准(指分析性和同义性的标准),……一个合适的标准很有可能使分析和综合之间的区分成为一种程度的区分。”(第529—530页)怀特用“温度比喻”说明了这种程度区分的性质:“温度的不同是程度的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的温度计上注明像0℃这样的固定点。但应该指出的是,‘分析的只是处于一个刻度上较高的位置,而‘综合的,则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这种看法打碎了分析和综合作为不同类型知识的表述的根本区分。”(第525页)
蒯因也指出:“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线却一直根本没有划出来。认为有这样一条界线可划,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第35页)
但是蒯因比怀特要激进和彻底。怀特认为有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但二者的区分“不是一种鲜明的区分”,即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陈述,怀特认为例句(1)就是这样一种陈述:
(1)所有的人是理性动物。而蒯因则根本否认有分析陈述。他以例句(2)为例,指出它可以从下面的逻辑真命题(3)通过同义词替换而得到。
(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3)没有一个未婚的男子是已婚的。蒯因把逻辑真命题称为第一类分析陈述,把(2)这样的命题称为第二类分析陈述。他明确反对“第二类分析陈述”是分析陈述。那么蒯因是不是没有反对逻辑真命题是分析陈述呢?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tiller)说:“对蒯因来说,即使逻辑真命题也不是分析的、不可修正的命题。”(第208页)这一思想是令人震惊的。蒯因用他的“力场比喻”说明了他的思想:“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除了由于影响到整个场的平衡而发生的间接联系,任何特殊的经验与场内的任何特殊陈述都没有联系。……要在其有效性视经验而定的综合陈述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有效的分析陈述之间找出一道分界线,也就成为十分愚蠢的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反之,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第40-41页)就是说,任何命题——所谓的“逻辑真命题”也不例外——可以是假的。这个“力场”是一个整体,一个知识或信念的整体。只不过逻辑陈述处于场中“内部比较中心的位置”。这就是蒯因的科学知识整体论。这个整体论与他的意义整体论(即主张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蒯因等人的观点在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反驳蒯因的人当然不少,较为著名的有麦特斯(B,Mates)、考夫曼(A.S.Kaufman)、格莱斯(H.P.Grme)和斯特劳逊(P,F,Strawson)等人,但是在他们的文章中‘‘(第525—534页)[5(第421—426页)(第141—158页)却都没有去反驳蒯因的整体论。而蒯因的整体论既反击了还原论这个“教条”,又阻止了分析一综合的二分。尽管蒯因以多种方式对他的论题进行了论证,但其某些论证仍然存在问题而不足以支持其结论。
二、对蒯因、怀特、普特南的反驳
(一)对蒯因的反驳
蒯因指出,他要反驳的现代经验论的一个教条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第19页)。因而可以认为,蒯因所说的这个经验论的教条中“分析的”与“综合的”的意义是:
Q1:一个命题是分析的,当且仅当该命题的真值与事实(matters of fact)无关,而只取决于该命题的意义。
Q2:一个命题是综合的,当且仅当该命题的真值取决于事实。
显然,蒯因对Q1作为“分析的”定义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其定义项中出现了“意义”这个概念,他认为“意义”像“分析的”一样难以理解、模糊不清和需要加以解释。蒯因也考虑了“分析的”有可能的其他的定义。麦特斯就指出过,蒯因和怀特考虑了“分析的”八种意义(第525页),蒯因认为其中每一种“分析的”的意义都导致问题,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对此作了论证。我们要驳斥蒯因,无须考虑各种各样的“分析的”概念,而只要证明在Ql和Q2的意义下,分析和综合的二分是成立的就足够了。如下的论证是很容易想到的:
P1:一个命题的真值,要么取决于事实,要么与事实无关。而任何命题的真值,当然与其意义有关;换句话说,任何命题的真值,除了可能取决于事实外,还取决于其意义。如果一个命题的真值与事实无关,那它就只能取决于该命题的意义了。这样,根据Q1和Q2,一个命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这就是对任何命题可以进行分析一综合二分的根据。
蒯因是如何反驳论证P1的呢?蒯因指出;“陈述的真理性显然既取决于语言,也取决于语言之外的事实。”(第39页)“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所以,任何陈述都是综合的。换句话说,分析陈述的集合是空集,因而分析一综合二分是无意义的。
可见,蒯因在反驳分析一综合二分的同时,他实际上还反对了Q1与Q2本身的合理性。因为根据其意义整体论,谈论“单个命题的意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说“单个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其意义”也是成问题的说法,而定义Q1和论证P1都预设了“单个命题的意义”。
但是蒯因大概也不能不承认,人们对知识的学习、理解是从一个个的词和句子开始的。对于任意一个句子来说,人们只有理解了全部的知识才能理解它,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是荒谬的。具体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了解作为整体的知识,而只能了解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实际上,许多单个的句子、命题,其意义是被大多数人了解的,如“今天在下雨”、“张三今天上课”,还有逻辑命题“p—p”等等,每个命题都是有意义的,表达它们的句子也被公认为有确定的“字面意义”。谈论这些命题的“单个命题的意义”是适当的。
这里,我们要把命题与句子作一区分。任何命题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言中的句子表现出来,例如“今天在下雨”这个命题在汉语中的表现可以是“今天在下雨”,在英语中的表现可以是"It is raining today'。一个命题与一个句子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词义可以变化,同一个句子在一定时期表达一个真命题,却完全可能在另一个时期表达一个假命题。原来的句子要保持为真,则应该修改该陈述,但这不等于说该句子原来所表达的命题现在也要修改了。因此,蒯因的“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若解释为“没有任何命题是免受修改的”,是缺少证据和论证的。
我们认为,任何命题是有真值的,没有真值就不能称为命题,而句子则不一定有真值,哪怕从语法上看它是一个合格的句子。命题一定得具有意义才能有真值。两个句子表达相同的命题也就是说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若它们的意义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不同的命题。所以,句子与命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对于句子,也许不能进行分析一综合的二分,但是对于命题,我们认为论证P1是成立的,可以有分析一综合的二分。像“p—p”这样的逻辑命题,就是一个能免受修改的命题。
不仅在语言学习等实践问题上整体论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在理论上,命题这个概念也是与意义整体论相对立的,因为单个命题就具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讨论命题的二分问题时,就预定了意义整体论的失效。蒯因式的整体论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否认单个命题的存在。蒯因在其晚期著作中指出,“被看作句子意义的命题,只会是一种更确定的句子的意义”(第69页),他企图借用奥康剃刀(Occams Razor)的力量去掉“命题”这个概念,但却无法避开谈论句子的意义。他指责句子意义这个概念“空洞无力(tenuousness)”、“难以捉摸(elusive)”(第68,69页),那么他所谓的“固定句(eternal sentences)”有无确定的意义呢?如果其意义不确定,似乎不宜称为固定旬;如果其意义确定,那么蒯因就不能指责它“难以捉摸”了。蒯因的另一个论证是:“忽视可看见或可听见的句子而集中在句子意义上,把它们作为真之载体,似乎也是违背情理的。因为只有诉诸句子,我们才能说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句子意义。”(第68页)一幅画可见,一首歌可听而不可见,但不能因此说一幅画比一首歌更基本,因为一幅画和一首歌都是可以感觉的。同理,从句子可见而句子意义不可见的角度论证句子比句子意义更为基本也是不对的,因为句子意义之不同正如句子之不同一样可以辨认。所以,虽然我们只有用句子来说出意义,但并不因此在逻辑上句子在意义(命题)之先,因为离开意义,无意义的符号串并不能称为句子或陈述。翻译的不确定性只能说明意义问题的复杂,并不能否定意义的存在,因为只有诉诸意义,才能谈论一个句子是不是另一个句子的翻译。我们讨论命题的二分问题,其预设前提就是单个命题的存在。固定句恰恰直观地表明了单个命题的存在,而单个命题的存在使整体论不攻自破。
(二)对怀特的反驳
怀特没有否认逻辑真理是分析的。但是他提请我们判定一下(1)这样的命题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以及我们判定的根据是什么?怀特指出(第519—521页):从逻辑真理(4)可以推出(5)。
(4)所有的P是P。
(5)所有的人是人。在“人”与“理性动物”是同义的前提下,用同义替换可以把(1)变成(5),于是(1)是分析命题。想象一下两种语言L1和L2,它们都含有“人”、“理性动物”、“无毛的两足动物”等词汇。在Ll中“人”与“理性动物”是同义的,但与“无毛的两足动物”不同义。在1、2中“人”与“无毛的两足动物”是同义的,但是与“理性动物”不同义。对比考察下面的句子:
(6)所有的人是无毛的两足动物。于是,在L1中,(1)是分析的而(6)是综合的;在L2中,(6)是分析的而(1)是综合的。那么(1)到底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呢?所以,怀特认为(1)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陈述。
为了说明分析综合的区分是一种程度之分,怀特设想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追问这些土著人。……‘在你们由某些东西不是理性动物这个事实得出它不是人的结论时,难道不是比由某些东西不是无毛的两足动物这个事实得出这个结论更为确信吗?如果这些原始人是有礼貌的,并且回答‘是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某种形式的标准。但是要注意,正是一个标准使区分成为程度之分。”(第527页)这里,怀特是想说,对于那些土著人来说,(1)和(6)都是分析的,但(1)比(6)更是分析陈述。
怀特很机智地看到,在判断(1)这样的句子是否是分析的时候,需要判断一些词语是否同义。而词语间不同的“同义”关系意味着相应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给定一种语言,其中两词语是否同义也应该给定。如果在给定的语言L中“人”与“理性动物”是同义的,则(1)是分析的,反之是综合的。总之,我们得不出(1)是在这两者之间的结论。
一种土著人确实可能相信(1)甚于相信(6),因为信念是有程度之分的。但信念只是心理现象,还不是知识,而(1)和(6)是不是分析的却是知识方面的问题。如果对于这些土著人来说(1)是分析的,由于“理性动物”与“元毛的两足动物”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则他们不会认为(6)也是分析的。这些土著人可以想象海洋中有某种鱼形理性动物,它们也是一种人,但不是两足的,所以(6)对于他们而言是综合的。
所以,怀特在这里错误地由信念有程度之分推出相关的知识也有程度之分。因为,相信的程度有高低之分,不等于相应的信念的内容也有程度之分。
(三)对普特南的反驳
今天谈分析和综合二分问题,除了蒯因和怀特以外,另一个必须谈及的人就是普特南(Hilary Putnam)。普特南主张有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认为下面的两个句子中,(7)是分析的而(8)是综合的(第35页),因而他认为蒯因是错的。
(7)所有的单身汉是未婚的。
(8)这张桌子上有一本书。但是普特南又说:“在更深的意义上我认为蒯因是正确的,远比他的批评者更为正确。”(第36页)为什么普特南说这些看似矛盾的话呢,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普特南考察了下述四个句子(第39—48页),认为它们既非分析的,又非综合的。
(9)仔在过去。
(10)如果琼斯知道p,那么他必定有表明p的证据。
(11)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能量是守恒的。
(12)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有洛伦兹不变性。普特南说:“如果人们想要一个关于语言的模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一‘一切陈述分为三大类:分析的、综合的、以及大量的其他类型的,要比从这样的观念出发——‘除了在边界处有些模糊外,每个陈述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好得多。”(第39页)但是普特南也不是主张三分,他说:“我所提到的那些陈述并不归于第三个范畴,这些陈述实际上属于多个不同的范畴。以明显的是语言规则为一边,以明显的是描述性的陈述为另一边,此外还有大量的陈述,它们很难被
归为分析的或综合的陈述。”(第38页)
故普特南反对分析一综合的二分是毋庸置疑的。普特南甚至认为陈述的类型是“一个多维的连续统”。为了说明这些现象,普特南提出了“定律簇(1aw-cluster)”概念:“定律簇概念并不是由一组性质构成(像‘人、‘乌鸦这样典型的通名就是由一组性质构成其概念的),而是由一簇决定该概念的身份的定律构成。概念‘能量,就是一个定律簇概念的好例子。它出现在大量的定律中,充当很多角色,这些定律和推理角色是集体地而不是单独地构成了它的意义。……一般说来,这些定律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抛弃而无损于辨认该定律簇概念。”(第52页)尽管普特南对什么是“分析陈述,,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分析陈述中不能有定律簇概念则是明确的…(第65页)。例如,“能量”、“物理定律”都是定律簇概念,所以(I1)、(12)都不是分析命题。但它们也不是综合命题,因为经验的事实(试验)不能推翻它们。与此相对照,通名“单身议”这个概念就不是定律簇概念,而是个单判据概念(one-criterion concept)。对于单判据概念,相关的陈述如果放弃或修改,就改变了该概念的意义,因而它所在的句子就改变了其所表达的命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修改,故(2)与(7)是分析命题。
普特南的这一套语义学的确把分析综合二分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深入。限于篇幅,详细考察这一语义学的细节是甭合理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其提出以下几点疑问和批评:
第一,我们注意到,普特南对“分析陈述”的规定,主要强调其可免于受经验事实的修改(immune from revimon)这一点(第49,50页),但这是不是就是“与事实无关”呢?“可免于受经验事实的修改”与“不能受经验事实的修改,,还是很小一样的:前者与“受经验事实的修改”是相容的,后者则与之不相容。所以,我们认为普特南的“分析的,,概念,很难说是与“综合的”这一概念相对立。如果普特南所持的“分析的”和“综合的”概念与通常的不同,特别是与我们的以Q1、Q2为其规定的概念有所不同,则他对我们所主张的二分的批评就不那么有力了。
第二,在普特南所举的(9)至(12)这些例句中,每个句子都有意义不是十分明晰或不确定的概念。首先,每个定律簇概念都是意义不确定的概念,因为,假设决定“定律簇概念”N的身份的一簇定律是T1,…,Tn,而其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抛弃而不影响N的意义,这样,N是满足还是不满足TI是不清楚的,这就表明N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其次,(9)中的“存在”、(10)中的“知道”也都是有歧义的、意义不确切的概念。我们认为,“分析的”定义Q1中有一个预设,那就是有关的命题的意义是明确的,这也意味着出现在该命题中的概念的意义均是明确的。意义模糊不清的陈述,当然不能判断它究竟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它也不够资格表达一个确切的命题。所以,这些例句不构成反对命题的分析一综合二分的理由。
第三,对于(9)至(12)这些例句,如果它们的意义是确定的,并且如通常的那样,那么我们可以说,(9)、(11)、(12)均是综合命题,它们是可能为假的。且以(11)为例:设(11)是意义明确的命题,那么其中“能量,,的概念是什么也是明确的,所以事先应该能确定一种对能量的计量,为了使这个例子易于理解,设我们的能量概念还只是机械能,则某个封闭系统中的能量可能不守恒,(11)将被实验证伪。要坚持(11),就需要改变能量的定义,使其包括热能、化学能等等。而能量的定义和{1算方法一旦定下来,则(11)又可能被新的实验证伪,故(u)是综合命题。如果坚持(11)不可能被证伪,那么其中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和是多少就不能有明确的计量方法,从而使该概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科学的概念。至于(10),我们认为它是分析命题,因为按照“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Knowledge-s justified true behef),,这种观点,加上“知道”是主体对知识的拥有,可知(10)就是由其意义而必定为真的命题。所以,对于普特南的这些例句,c。二分”并未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三、命题的三类与二分
从以上我们看到,对于意义确定的命题而言,它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但这绝不是说,人们对于一个句子到底表示的是分析命题还是综合命题没有争论。事实上是有争论的,我们对蒯因、怀特、普特南的反驳正是这种争论的一种反映。如何理解这种争论和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会不会导致对命题二分的否定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一个概念很重要,我称之为“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由人组成的,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文化、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科学知识、语义约定。由于有这些共同的因素,所以他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较为一致。他们不必说同一种语言,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也许甲说的是英语而乙说的是法语,但是他们之间能够相互充分地交流;如果需要翻译,那么翻译也是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人。相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未必处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因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对科学知识的把握也可能十分悬殊。
在判断命题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三类命题。第一类是所有的文化共同体都认为是分析的命题,逻辑真理就是这样的命题。如果所有的文化共同体都认为“单身汉”与“未婚的男子”是同义的,那么(2)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分析命题。这一类命题的否定命题也属于这一类,因为矛盾命题虽然是假的,但它的真值也与事实无关·第二类是所有的文化共同体都认为是综合的命题。例如“今天在下雨”,这类命题的真值取决于经验事实。第三类是这样的命题,有的文化共同体认为它是分析命题,有的文化共同体认为它是综合命题,有的文化共同体不能确定它是分析命题还是综合命题。(1)和(6)就是这样的命题。上节我们所说的那种土著人所属的文化共同体c1认为(1)是分析命题而(6)是综合命题。当然可以有另一种土著人,他们属于另一个文化共同体C2,他们认为(6)是分析命题,他们可能相信世界上会有些人总是处在疯狂或者白痴的状态,或者一生下来就是植物人,从来就没有过理性,所以(1)对他们而言是综合命题。
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对一个命题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意见不一致时,这意味着这个共同体c至少可以更细分为A与B两个(亚)文化共同体,而A和B各自对该命题的分类则是一致的。因此,逻辑上一切命题可以分为这三类。
事实上,人们对每一类是些什么命题意见已经比较一致,格莱斯和斯特劳逊就说过:“人们使用‘分析的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形,拒绝用‘分析的也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形,对是否用‘分析的感到犹豫不决的还是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形。”(第143页)这就印证了命题分为这三类的合理性。
怀特注意到:有人认为(如密尔信徒)同义这个概念应该相对于一定的语境,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中的词语是模糊的——在一种语境中“人”与“理性动物”同义,在另一种语境中与“无毛的两足动物”同义。但“根据这种相对的同义概
念,密尔信徒仍然远远没有解决我所提出的困难”(第528-529页)。我们认为,相对于一定的语境来谈同义关系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的确可以很不一样,这会导致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不一样,但这时它表示的是不同的命题!而我们关注的是区分命题的分析与综合,而不是句子的分析与综合。
怀特相对于一定的语言来谈同义关系的这种方法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说“词A与B在语言L1中同义,在L2中不同义”,这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词是语言的构成元素,无论A是什么,语言L1中的词A与语言L2中的词A根本就是不同的两个对象。所以那种说法就如同说“词A1与B1在语言u中同义,词A2与B2在语言L2中不同义”,那又怎么样?没有结果。句子也是语言之中的句子,“不同语言中的同一句子”——这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容易引人误解的说法。
我们这里的方法是相对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来谈同义关系。若一个文化共同体C3有着这样的价值观:是人就应该有理性,没有理性就不配被称为人,那么在该文化共同体中“人”与“理性动物”就是同义的,因此该文化共同体就会认为(1)是分析的,而(6)是综合的。这样就避免了跨语言的“同一词”和“同一句子”这种奇怪的说法。
就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与命题的关系而言,命题被分为这三类。但给定一个文化共同体,命题还只能二分。这是因为,对于有争议的第三类命题,根据Ql、Q2这种对“分析的”和“综合的”的理解,它只能要么是分析命题,要么是综合命题。对于任何命题,可以存在一个文化共同体,相对于这个文化共同体,该命题要么是分析命题,要么是综合命题,而不会是模棱两可的:即这第三类命题也有被二分的可能。例如怀特认为成问题的陈述(1),它相对于共同体c1和共同体c3来说就是分析的,而不会是在多大程度上是分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综合的。而对于共同体C2,(1)则是综合的。虽然相对于我们这个共同体C4,对于(1)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可以存在某个共同体c5,c5中的人一致地不能确定(1)到底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从某个命题被某个共同体认为“既不是分析的、又不是综合的”,并不能得出这个命题本身“既不是分析的、又不是综合的”的结论。
当人们对一个命题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有争议时,这往往意味着人们对它的意义是什么的看法并不一致,于是我们需要去确定表达这个命题的句子的意义。所以考夫曼说得有道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能够作为一个引发更清楚的表达的工具。我们通过固定句子的成分表达式的意义来使句子成为分析的或综合的。札”(第426页)但这后一句更准确一点应该这样说:我们通过固定句子的成分表达式的意义来把握该句子所表示的命题,而对于意义明确的命题,它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
[参考文献]
[1][美]怀特:《分析和综合:一种站不住脚的二元论》,冯艳译,载苏珊·哈克:《意义、真理与行动——实用主义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2][美]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责任编辑涂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