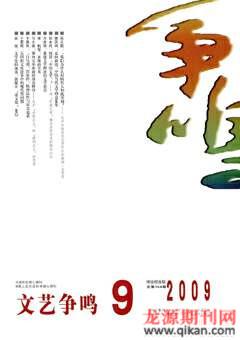“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力
金 理
“文化恐吓”中的奴役
梁任公先生留下的那些“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文字,世多以为诟病,但其中实不乏诚恳而可爱的自剖,值得人记取,比如以下这段: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上面引语描述1902—1903年间的现象,但已击中后发国家在现代化与启蒙过程中的持续性困境。之所以想起这段话,缘由来自《小批判集》中的一篇《惊慌失措的文化》,论及《百家讲坛》的如日中天,郜元宝先生慨叹:“我们的电视节目至少目前还很不像话,广大人民群众整天被迫吞吃大量文化垃圾,偶尔来点绿色食品,就犹如久旱逢甘霖,禁不住要感恩戴德、誓死捍卫了。”同80余年前梁任公的发言相比照,其锋芒所向、忧虑乃至出语思路均若合符节,真让人感叹历史的循环(当然在梁那里还多了一层通过翻译的“输入”)。二者所述的情形中暗藏的危险也一脉相承,在“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的同时,是否应该冷静思索“消化”问题?“久旱逢甘霖”的迎合加上“誓死捍卫”的不容质疑,会否走入歧途?“到了新世纪,一种巨大的文化恐吓机制完全撇开文化人而单独由隐含着巨大商机的强势媒体非常轻巧地建立起来,……在这种书商叫卖和类似国家行为的硬性摊派合力制造的‘文化恐吓之下,文化匮乏时代经典的高玉宝式的‘我要读书的底层诉求,变成文化泛滥时代或极其吊诡的后现代自上而下的‘你必须读书的绝对命令,‘我要文化变成了‘你必须拥有文化,结果文化不再是人类精神自由翱翔的蓝天与自由驰骋的绿野,书也不再是人类精神可以自由结交的良师益友,而成了压抑个人乃至压抑整个族群的崇拜对象。”由上述商业垄断与文化统治包括政治规训合力制造的时潮,郜元宝形容为“文化拜物教”。
从“我要读书”到“你必须读书”、从“我要文化”到“你必须拥有文化”——表面上又一轮的文化普及与启蒙,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变异中滋生出崭新的压迫、奴役机制。当新世纪的读经说史运动几乎膨胀到全民响应的地步时,知识界并不乏与之缠斗的声音;但似《小批判集》这般清朗说理而一针见血的恐不多见。就此不妨先揣摩一二书名的意味。《自序》中说:“微尘如我者,也只能在混乱的街上陪假先知们蹒跚而行,偶尔学阿Q掷出几粒不满的小石子,表示还不肯一起沉沦。”出语谦退但别有怀抱,正如书名一般,虽以“小”修饰但终究不掩“批判”的峥嵘。在康德那里,“批判”大概不是指一般的批评或驳斥,而是针对形而上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教条,而先行去分析理性的认识能力,这多少有点于不疑处有疑的味道吧。“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小批判集》的工作,正是在看似“神圣不可干”的文化洪流中出声示警。
如何应对“文化拜物教”
“文化拜物教”中暗藏着一种欠缺正当性的启蒙结构。在这一结构的一端,虚伪的启蒙者恰似鲁迅所谓的“伪士”。强势媒体设立的讲座栏目、众文化明星的一夜成名、以及历史剧的狂轰滥炸等,看似盛况空前,其向大众所“灌输的内容之沉重,文化含量之丰富”,大有新一轮文化启蒙的架势。不过郜元宝揭示其本质是“文化恐吓”:“文化机构恐吓大众必须更多地具备文化知识、必须积极地参与文化造神运动,必须踊跃地购买在这过程中不断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否则好像就会丧失某种‘人之为人的根本,就会错过某种造就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会落后于某种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就会被唯一合法、健康、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洪流所抛弃”。今天的“文化恐吓”,可直接对应于鲁迅在20世纪初叶揭批的“伪士”对“恶声”的炮制、应和,其中的危害(当年“科学”、“进化”等新学话语沦为沸反盈天的“恶声”,今天本应健康的文化产品变成“逼迫人、威吓人、控制人、勒索人的偶像崇拜”)、心理机制(唯恐落后于“大势”、“洪流”)、奴役形式以及与启蒙困境的纠缠,无不一脉相承。鲁迅批判的“恶声”,是“文化恐吓”最早的源流之一,它们裹挟着强大的权力关系向人袭来,“灭裂个性”、“灭人之自我”。“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参见《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鲁迅清晰地勾勒出“中无所主”者被蒙昧、虏获的情形。而“伪士”们操持着“新名”、“正信”,自命权威,却往往斫伤他人的精神自由。这个过程中,又是“中无所主”者最易“心夺于人”,被“伪士”所“殖民”,甚或变成新的“伪士”——这几乎就是恶性循环。
在启蒙结构的另一边,当然就是上述被“伪士”所俘获的被启蒙者。出于“身外强力迫使”而对“外在于己身”的“价值”的趋附,并不是启蒙的实现而是启蒙的异化(奴役)。自上而下的“你必须读书”、“你必须拥有文化”的绝对命令,正显现出赫尔岑洞察到的由“强迫的敬重”而走向“拜物”:“人惟不屈物以从其理,亦不屈己以就物,始可谓自由待物;敬重某物,如果不是自由的敬重,而是强迫的敬重,则此敬重将会限制一个人,将会狭隘其自由……这就是拜物——你被它压服了,不敢将它与日常生活相混。”
在盛行“文化拜物教”的时代,形形色色以“名”掩“实”的标语、口号、时髦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早在1996年《在新的“名教”与“文字游戏”中穿行》一文中,郜元宝就表示过忧虑(《小批判集》中《“次殖民地”·“语言游戏国”》延续了相关思索)。值得珍重的是,他回到了鲁迅所提供的经验:以心应世、“白心”。“越是‘扰攘之世就越应当尊重个人内心的声音,评判问题的标准只能从个人内心寻求,并不存在和个人‘心以为然的标准漠不相干的‘真理或‘终极究竟的事。” “白心”是为了鼓励执著于内心的真实状态并真率地加以表达,摆脱外部制约或众数的意见。这种真率直白的态度中还含茹着原初性与创造性交相激荡的精神能力,这当是中西思想资源会通的产物。比如儒释道三家都讨论的“初心”,李贽揭举的“童心说”,袁枚《随园诗话》中标示诗人的“赤子之心”等。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童心说》)当“闻见道理”取代“童心”则“人而非真”,恰如鲁迅说“精神窒塞”、“灵觉且失”而沦为“伪士”。其后袁宏道力倡“性灵说”时,鼓吹“无闻无识真人”(《叙小修诗》)、讥讽“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之人(《叙陈正甫会心集》),与李贽的意见异曲同工。倘若转向西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尼采,他认为哲学家须有“初次(有创始性地)看察事物”的特性,“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10)。李贽反对“闻见道理”、袁宏道鼓吹“无闻无识”,与尼采“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正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能草率地以反智主义来一笔勾销上述见解(“白心”与肤浅的反文化之间的辨证,可参见《被委以重任的文化》一文中的相关探讨),因为在形形色色、潮来潮往的“闻见”中,积聚着太多看似天花乱坠实则人云亦云、“莫知其可”的舆论、甚至斧钺人天性、使得主体的内在空间被悬置、漠视的“俗见”。如果对此无所警惕,就为名教的生成与膨胀大开方便之门。越是身处信息爆炸、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越容易为“文化恐吓”所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鲜的第一眼”与“白心”共享的自由畅达的“创始性”(而不受强制灌输),它们对人天性、内在精神空间的守护,以及对“毛孔骨节”俱为俗见所缚的警觉,可以帮助个体抵抗“文化拜物教”的污染。
鲁迅在上世纪初叶感叹“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但他“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破恶声论》)。“内曜”、“心声”,都不是靠着“多数”、“外来”、“自上而下”的声音,而是人发自内心的真的声音(“诚于中而有言”),这才是启蒙。西文中Enlightenment一词的原义(“照亮内心”)同样指向人内心的自觉,即康德意义上“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1)。鲁迅褒扬“白心”,珍视其中与生命本源相接通的自由畅达的创造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与“内曜”、“心声”、“白心”本无扞格,原为同一。在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潮中,因民智未开而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将概念、主义话语、知识体系等赋予落后的民众是言论的主流,但鲁迅的启蒙不求诸于身外的权威而试图在自我内面寻求契机。
整全性的“文学”与批判的可能
《小批判集》开篇谈吃喝,从韩国人饮食的背后提取出“洁净的精神”,以此警醒中国人饮食习惯中的粗俗、豪奢。这种追究“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的指向,似乎颇合于余英时揭橥的中国在哲学突破时代的“内在超越”特征(12),世间和超世间的不即不离,“道”超越于日用事物同时又遍在于日用事物。
《小批判集》谈吃喝、谈创作、谈文学史、谈电影、谈“韩流”,与此杂文集似的体例相配合,在种种日用事物间探寻今天精神流向的奥秘。很不“整齐”的编排恰恰见出整全性。这样一种观察世相的眼光,是文学的眼光。在知识共同体日益破碎、学科分化日益琐细的今天,文学似乎仍然提供着一种整全性。请允许我再次回到鲁迅,在他的理解中,文学在“神思”的涵养下,接通着人类一切超越的精神渴求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活动。当然,这里的“精神”并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所谓“内在超越”,基点仍然植根于生命的血肉真实与生活的切身实在。
《“语文”·“文学”》一文中郜元宝抱怨道:“试到大学附近书店去逛逛,不难发现那里出售的是些什么书籍!各种‘专业书籍堆积如山,文学经典只在某个角落羞羞答答蹲伏着。有些书店根本找不到文学书。”(13) 类似的不满在几年前就表示过:“中国一大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离开了文学,……他们把自己和已然失败或早就失败的文学区别开来,或干脆弃置不顾,正正规规做起学问来了。”(14)在文学被认为早就丧失批判的可能而频遭炮轰,只能“蹲伏”在角落里的今天,像郜元宝这样旗帜鲜明坚守文学性立场的并不多见。他甚至具体阐释了“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概念:“他的知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与生活的丰富细节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思索非常靠近。知识不单单是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文学性知识分子”同样视野开阔,讨论公共话题,“他未必能解决那些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帮助你消除了和那些问题之间容易产生的隔膜”,而不是傲然俨然地将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切问题都驯服和安顿到密如蛛网的“学术话语”中(15)。
坚守文学性立场不是姿态,首先应该具备一定的“理据”。郜元宝先生近年来的文章往往围绕此中心展开。比如讨论竹内好的鲁迅论时,指出:“在鲁迅那里,启蒙不是先验的绝对命令,而是带着生命体验的自觉追求。或者说,启蒙不是第一位的,即不是诸新价值的发源地;相反,启蒙必须接受更加本源性的东西的检验,必须从更加本源性的东西中顺其自然地产生。”(16) 这种本源性的存在,竹内好以为就是“文学”,“在他,是有着一种除了称作文学者以外无可称呼的根本态度的”,“文学家鲁迅是无限地产生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的场所” (17)。由此,文学成为根本性的态度,这一“终极的场所”使得思想消逝于其间复又诞生于其间。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应该“肉身化”,被生命气息所浸润。而启蒙与批判,必须在这样诚实的生命源头上确立自己的资源。
郜元宝先生近年来的著述(尤其《鲁迅六讲》和《为热带人语冰》中的一些篇章),探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学性智慧与非文学性智慧的分裂,清理文学与学术的关系状态,揭示文学教育中非文学的规训,以及梳理鲁迅、竹内好等先辈的经验……归根结底是重新确立文学者的基本立场。《小批判集》应该在上述工作的延长线上得到理解,我以为正是理论阐述之后的“亲证”。有了“文学性知识分子”立场的支撑,《小批判集》背后那位批判者的形象已呼之欲出;或者说,《小批判集》正是一位“文学性知识分子”沟通现实的实践。如果不将文学狭隘化地理解为当前流行的那般精巧和烦琐,而释放其“与人生际会”的体贴、“放笔直干”的自由、“直语其事实法则”的爽快、“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般的敏锐,那么知识分子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放弃用文学的方式观察、评论和应对世界的信心。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80页。
(2)郜元宝:《惊慌失措的文化》,《小批判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2页。
(3)参见郜元宝:《被委以重任的文化》,《小批判集》,第18、19页。
(4)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原刊《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第193页。
(5)郜元宝:《被委以重任的文化》,《小批判集》,第18页。
(6)参见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76页。这段话出自伯林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转述。
(7) 赫尔岑:《法意书简》,转引自以赛亚·伯林:《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10页。
(8)郜元宝:《在新的“名教”与“文字游戏”中穿行》,《钟山》1996年第6期。
(9)郜元宝:《“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3页。
(10)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转引自周国平:《尼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47、48页。
(1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页。
(12)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余英时文集》(第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
(13)郜元宝:《“语文”·“文学”》,《小批判集》,第276页。
(14)郜元宝:《等待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页。
(15)参见郜元宝:《智慧偏至论》,《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
(16)郜元宝:《竹内好的鲁迅论》,《鲁迅六讲》(增订本),第154页。
(17)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108页。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