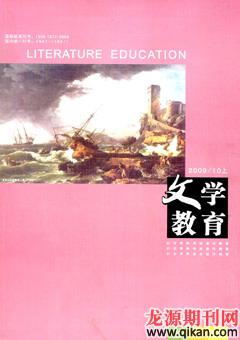评晓苏的《我们的隐私》
李遇春
晓苏的这篇小说写了时下流行的农民工的故事,而且还是农民工的“隐私”的故事,这在如今充斥着政治投机和市场投机的文坛中,难免会让严肃的读者生疑,人们疑心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纯净。然而,读罢这篇朴实晓畅的小说后,读者的疑虑应该可以打消了。这是一篇严肃而认真的小说,作者表面上是写农民工的隐私问题,实际上却是想探究我们这个时代里传统的家庭形态所面临的困境。
在新世纪转型的中国社会里,由于城市化进程愈趋快速,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农民工在现代化城市里的遭遇是严峻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物质待遇和精神尊严上,而且表现在他们的私生活领域里。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离开了农村的配偶单独到城市里闯荡,而让另一半留守乡村。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私人性问题出现了,这些苦斗在城市里的单身农民工,他们(她们)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生理需要的?与此同时,那些被他们(她们)抛置在乡村里的另一半,又是如何克服同样的身体欲求的?总之,农民工的“性”成了一个待解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的家庭形态遭到了冲击,那些留守乡村或者城市苦斗的孤男寡女,他们在无法压抑的性本能的驱动下,明知违背了传统的家庭婚姻伦理道德,最终还是选择了暗中出轨,由此带来了,他们的不可告人的隐私。可叹的是,他们(她们)并非想抛弃各自的配偶,他们不是当代的陈世美,她们也不是当代的潘金莲,因为他们(她们)与配偶之间还有感情基础,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道德规范来批判他们(她们)。但毋庸讳言,这种即使是无奈的婚外情也还是会损害他们(她们)原来的夫妻感情,而且他们(她们)的婚外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也会日久生情,由此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心理痛苦。晓苏的这篇小说既写出了这种无奈的婚外情的快乐,同时也正视了由此带来的心理痛苦。作者没有简单地做道德评判,而是对男女主人公的精神遭遇充满了同情和悲悯。
作者的构思是精巧的。小说里出现了三个家:男主人公“我”和女主人公麦穗组成的临时的家,“我”和妻子在油菜坡的家,麦穗和丈夫在羊村的家。“我”和麦穗在南方城市的家虽然不具备合法性,但事实上随着叙事的进展却合情也合理起来。这个家是作者的叙述中心,因此在文本中是显性的家,而恰恰是这个显性的家申隐藏着巨大的隐私:“我”和麦穗都是从内地山区来南方城市谋生的农民工,困偶然的邂逅熟悉,随之感情日深,最后发展到租房同居,组建了当代中国城市里并不鲜见的临时家庭。这也是一个仿真之家,它的真实性甚至逃过了房东的法眼,在房东的眼中。他们是标准的恩爱夫妻,夫唱妇随,情投意合,让人想起黄梅戏中“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温馨。作者用了很大篇幅写了“我”和麦穗之间营造的这个仿真之家,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在这个仿真之家中的生活状态,“我”和麦穗之间的那种默契和相互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但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才明白,这不过是两个远离家乡的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而已。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彼此完全独立,而且互不干涉对方原来的家庭生活。但这个临时家庭似乎比真实的家庭还要真实,因为,他们都活在一种仿真的或者说是虚拟的家庭形态里,因此没有现实家庭中日常的争吵和烦恼,只有性的欢愉,亦不乏情感交流。总之,这是一个假而真,真而假的特殊家庭形态,折射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原理,家在这种消费语境中成了临时的消费品,就像现代都市人一次性的快餐消费一样。
然而小说中与仿真之家相对立的还有另外两个现实之家,它们的存在其实是对仿真之家的颠覆,暗示了仿真之家的幻象性质。作者以男女主人公的返乡之旅为叙事线索,中间穿插关于两种不同形态的家的故事,返乡之旅的结束正预示了仿真之家的幻象的崩溃。这两个现实之家在文本中处于边缘位置,属于叙述上的隐性之家,与作为显性之家的仿真之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但和仿真之家一样,两个现实之家中同样充满了隐私。在“我”和油菜坡的妻子之间有隐私,妻子在丈夫长期在外的情形下背地里和人私通,丈夫明知隐情却就是不愿或不敢公开面对尴尬的现实,他选择了原谅但同时也选择7暗中的报复,于是隐私愈益深重,终止无法解脱。出乎“我”的意外的是,小说结局处,“我”终于明白原来麦穗也有她的隐私,她说的老家的残疾人哥哥其实就是她的丈夫。所有人都殊途同归,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自己的隐私。隐私无处不在,隐私成了消费品。这正是现代人在消费社会里的存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