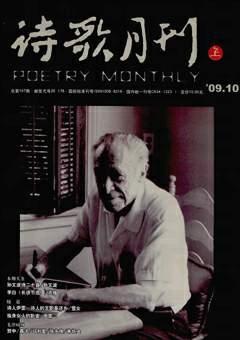当代诗人的艺术使命(外一篇)
张德明
人类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与搏斗中发明语言的。在语言未曾诞生之前,人类社会一直处于自然的、无序的蛮荒状态,在蒙昧蛮荒的时代,手势和眼神这些传递思想情感的介质,无法准确道明人与人、人与世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语言的诞生是人类社会的质变,语言的最大功绩是用词语把事物一一标划出来,规定事物各自的名称、属性和功用,词与物的一一对应使整个世界呈现为有序的整体的形态。对世间万物的一一命名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创设了无限生机,从此,人类就在同世界的联系与交往中,尽情歆享语言所能给予的愉悦和快感,接受语言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文化产品,但语言一经发明,又会相对稳定下来,反过来给人类的思想和言说提供规范。我们面临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是语言表述了我们的生命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即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如果说先民在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就创造了诗歌,这话是一定不错的,因为他们手中诞生的语言是原初形态的,闪烁着神性的光芒,他们发现语言的同时,也发现了世界的诗意存在。但是,语言一旦固定下来以后,便在人类反复使用的过程中逐渐世俗化,诗意的光泽不断消减最终黯淡下去。语言的日常化扩散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能力,但最大程度地遮没了诗意的直接呈现。当代诗人的使命在于,给语言重新命名,重新发明语言的诗意化质素,拆散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庸俗化、惯常化联系,重建语言与世界的诗意性联系。这样,诗人创作的艰难就成了语言的艰难,诗人思想的痛苦就是语言的痛苦。词语,这个显在的意义怪兽,时时抓伤诗人的思维神经。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只有诗歌才能表述人的这种生命样态。但尘世的雾霭密密丛丛,在语词的密林里,诗人要找寻到诗意的表达,必须历尽万苦千辛。在诗意的找寻中,诗人总会遇见语言的困苦与表达的焦虑。然而,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里,诗人既然行使重新发明语言的诗意这一神圣职责,诗歌写作就意味与日常语言搏斗,就是在语言的流沙之中汰出诗歌的金子,让诗性的语言如旗帜一样在日常语汇中脱颖而出。
诗歌表达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把所有思想到、感受到的物象与语词毫无遗漏地分行排列起来就会成为诗歌。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新诗不如古诗,为什么我们总认为新诗可能无法达到古诗所已达到的较高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古诗是锤炼之下生成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都充分证明了古人作诗的认真与谨慎。而新诗受制于胡适提倡的“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的创作观念,多为仓促草率之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其实语言表达上的困难并非是新诗创作才有的,古人作诗时也同样遇到。陆机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媸妍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文赋》)刘勰也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管,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文心雕龙·神思》)同样是面对语言与思想的不同步性,面对诗歌表达的语言困难,古人将它化为为创作的动力,化为“苦吟”的逻辑起点,而现代诗人却极力驱避这个问题,不惜以散文化来消解语言表达的困难。中国新诗经过了80多年的发展历程,至今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也许与从起步处开始诗人们就没有注意到对日常语言进行诗意再造有很大关系。
诗性语言的发明与再造还是以日常生活语言为起点的。尽管日常生活语言总是将诗意的成分重重遮蔽,但我们又不可能摆脱它去另设一个语言系统,而是必须依照这些语言所提供的线索进入诗思,同时抓攫这些语言进行熔炼、锻造,从而组合出属于诗语的新成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现代汉语赋予诗人的机遇与挑战。重新塑造语言的诗性空间,这是历史赋予当代诗人的神圣艺术使命。
对“中间状态”的诗歌说“不”
诗歌写作有多重维度,这些维度与诗人的艺术感悟、审美理解和诗性自觉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的维度支撑下也就生产出不同的诗歌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前卫的、反常的、小众的诗歌常常是更具有诗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诗歌,而时尚的、流行的、大众的诗歌因为易于上手会被许多人作为自己从事写作的基本形态,尽管在这些诗人意识之中并不完全明确这样写作的致命性,这类诗歌常常就是文学史意义不强的诗歌。后一种诗歌样式,正是我们应时刻警惕、戒备并果断说“不”的“中间状态”的诗歌。
有必要先区分一下文学意义与文学史意义的关系。应该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有文学意义的。文学意义建立在文学借助语言来表达世界的审美艺术图式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正是以语言为表达媒介来生动显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复杂隐秘关系,这些关系编织成具有多重思想蕴涵的立体空间来,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某种生活真实和世界奥义。不过,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史只收纳那些独创性意义更大的、具有一次性特征和巨大穿透力的先锋性文本。文学是厚的,但文学史必须很薄。在这个基础上,“中间状态”的诗歌或许是具有文学意义或者审美意义的诗歌,但绝不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诗歌。
“中间状态”的诗歌首先是原创性不太突出的诗歌。我们有时读一些诗人的诗作,乍一看去似乎并不觉得它有什么毛病,文字也简练,结构也自然,也表达了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某种理解。但仔细分辨一下就不难得知,这些作品似乎似曾相识,似乎总能找到前此的摹本和影子。这些作品都应看成“中间状态”的诗歌。语义承接上的因循守旧太合乎语法、意象择选上的小心翼翼且循规蹈矩、思想传递上的四平八稳并绝对正确,都是这种“中间状态”诗歌的基本表征。这些表征从某种程度上注定了这类诗歌的复制性质量和常规化水准,它们阻止着这类诗歌向更令人仰视的艺术高度攀升。文学史只偏爱那些个性独一、难以重复的艺术作品,模仿和复制永远是文学史的天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诗歌是不讲理的艺术,所谓“无理而妙”,太符合生活之理的文字组合常常是最缺乏诗性的。诗歌是喜新厌旧的艺术,它总是时刻在寻找摆脱“影响的焦虑”的前所未有的表达路线,以便开创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属于写作者个体独享的特定审美世界来。安琪有一首诗叫《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写道:
可以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
我的亲爱的
亲爱的杜拉斯!
我要像你一样生活
像你一样满脸再皱纹些
牙齿再掉落些
步履再蹒跚些
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
快些
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
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
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
像你一样生活。
这是一首剑走偏锋的诗,诗中充满了反常规的语言符码和思想踪迹。语词之间的暴力组合、强行扭断,不断放快的语势呈现出主体剧烈裂变中形成的重力加速度,语意结构上的杂多而不紊乱、分跨而不断裂,以及个体生存焦虑的超语义透视,等等,都对前有的诗歌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与反叛,同时也建构出属于诗人自己的特定秩序和空间来。这种诗歌就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和再生,因而绝不是“中间状态”的诗歌。一次性诗歌较为典型的还有很多,诸如伊沙《结结巴巴》、赵思运《毛主席语录》、刘不伟《拆那:诗歌批评家》等等,或许一些诗歌读者初读起来对这些诗歌并不太习惯并不太接受,但这正是具有先锋气质的诗歌所具备的特性,先锋诗歌是具有反叛色彩和开创意味的诗歌文本,是与读者的阅读惯性相违逆的,读者一开始不能理解和接受实属正常。先锋是为了改变读者而降生的,不是为了让读者来改变它,只有“中间状态”的诗歌才接受读者的改编。
“中间状态”的诗歌其次是缺乏穿透性和震撼力的诗歌。诗歌是一种最需要心智和脑力的文学艺术,不是随意为之就能得其所窍的。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诗歌创作遵循“作诗如作文”的审美逻辑,一时间似乎变得异常简单。不过,艺术规则的简单对于智力并不发达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美丽的陷阱,你或许认为能轻易进入,但没有充分的智商和悟性做保证,你就最有可能终生不得其法,一直只是一个诗歌创作的门外汉。优秀的诗歌应该是对世界充满锐利穿透力、给读者带来强大震撼力的诗歌,这些诗篇在那看似平常的语言文字背后显露出对于人生与世界、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发现与惊异书写。诗歌写作中的姿态可以崇高,可以建构;也可以走低,可以解构,这都不妨碍生产出具有穿透性和震撼力的诗来。前者如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等,后者如伊沙《车过黄河》、胡旭冬《太太留客》、沈浩波《一把好乳》等,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来碰触人生与世界的本真意义,给人带来悠悠不绝的文化思考和心灵撞击。与之相比,“中间状态”的诗歌就范于语言表述的字顺文从和意义传递的原样再版,生怕出现语言组合的越轨违规、意与象搭配的超远距离、意义呈现的多重歧义等,到最后只能是由平淡开场、从平淡收局,它能使读者迅速捕捉到诗意的终究,但无法在他们心中产生环生性、缠绕状的意蕴交响,进而无法刺激他们反复进入文本、探索个中奥妙的阅读兴趣。诗歌的意义是在反复阐释中不断增值的,先锋诗歌往往需要借助阐释与再阐释才能走入读者的阅读界面和文学记忆中,因而就具有不断增值的可能性,那些“中间状态”的诗歌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认知持平,它们无需借助太多的阐释就能为读者所把握,因此其增值的空间非常狭小。诗歌作品的增值效应,体现的正是它在历史穿透性和阅读震撼力上的强度大小,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一作品在艺术上具有的品质、力量和高度。从这一点看来,“中间状态”的诗歌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究其原因,“中间状态”的诗歌大都是依循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旧有惯性而生产出来的作品。一方面,“中间状态”诗歌的生成依赖于创作者对读者群想像与理解的惯性思维。每一个写作文本背后都有着隐含的读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作者在创制一部作品时都有对其作品阅读对象的基本预设。在新诗创作中,不少写作者将自己作品的读者想像为拥有一定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的普通大众,以为这样写就能赢得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其实这是明显的思维误区。普通大众是文学阅读中的乌托邦存在,具有不切实际的虚幻性,不光是诗歌,即使对阅读水平要求相对低下的小说、散文,也无法想像会有一个所谓的普通大众读者存在。我认可诗歌是写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这一观点,诗歌是一种精神贵族,不能因大众读者可能一时接受不了而止步不前、而改弦易辙、而看汤下面以迁就读者。“中间状态”的诗歌恰好就是在这种想像的乌托邦里生产出来、为迁就大众读者而不惜令艺术成色为之消减的作品。另一方面,创作者本人基于传统而保守的审美理念,认定这类写出来让大众读者迅速接受、无甚分歧和反对的诗歌是好诗。先锋是一种自由的艺术探索,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失败与成功与否,有时往往不是创作者本人能完全控制的,还取决于历史、社会与时代等方方面面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所以的先锋创作都可以看作是艺术尝试上的冒险活动,而且,这样的冒险是以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为代价的。比较起来,遵循旧有的诗学逻辑和审美范式而展开的创作,因为有此前的艺术成功为范例,所以这种创作不太具有冒险性,只要一个写作者经过一定的文学实践,几乎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顺畅地迈进。所谓得失相倚,这类写作虽然减少了尝试的冒险性,但因为写作的难度系数不过,劳动强度不大,故而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功性价值和意义。客观地说,遵循旧有的诗学逻辑和审美范式而创制出来的“中间状态”的诗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为流行的文本形式,充斥于中国的大小刊物之间,它们在消耗着写作者的青春和热情,影响着后继者的阅读与写作,同时也将一些具有探索性意义和精神的诗作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到了对“中间状态”的诗歌大声说“不”的时候了,如果你对中国新诗还存在着一分责任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