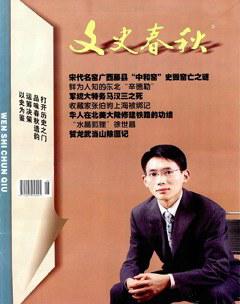老舍的北京情结
熊坤静
“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这是生于北京,并在此生活和工作长达42年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生前的一句肺腑之言。在4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总计创作了250万字的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文学作品,其内容多以北京作为故事和地理背景,仅北京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和店铺名等,在这些作品中就出现了240多个,其中北海被写的次数最多,有50次之多。爱北京、想北京、写北京,构成了老舍浓厚的北京情结。
在北京长大成人
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后面的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曲折狭小的胡同(“今小杨家胡同”)。这里的居民大多一天只吃两顿饭,且住在夏漏雨、冬透风的破屋子里。他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回忆说:“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然后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白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使老舍能够更多地接触下层居民,体察生活的艰辛。
老舍1岁半时,在正红旗当皇宫护军的父亲,因抵御八国联军进攻,在镇守北京正阳门的巷战中负伤阵亡。最后,侵略者攻进了城,在挨家挨户烧杀抢掠时,闯入了老舍的家。只因当时熟睡中的老舍恰巧被这些洋鬼子掀翻的一只大木箱子扣在下面,才侥幸躲过了一难。
此后,老舍的母亲每月仅得到清政府发放的饷银一两五钱,比父亲在世时的薪俸少了一半,且发得越来越不准时。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老舍的母亲不得不拼命地洗衣、缝补,把大批的衣裳揽回来做。老舍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中,有关“妈妈整天的给人家冼衣裳”的几段描写,实际上就是作者母亲的真实写照。
由于老舍总是吃米汤和糨糊,所以直至3岁他还不会讲话和走路。他虽然有个哥哥,但两人相差9岁,很少在一起玩:母亲和三姐忙着赶活,难得有空逗他、哄他,因此他只能整日坐在炕上,在玩耍小线、小棉花和小布头之中,消磨了幼年的大部分时光。
母亲坚强、豪爽、勤劳、诚实、待人热忱的品格,以及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的习性,给老舍以深刻的感染和影响,后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怀感谢之情说:“我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1905年,老舍在正觉寺开始了他近3年的私塾生活,后转入西直门大街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小学毕业后,亲友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老舍却毅然坚持要继续升学,于1913年1月23日考入北京市第三中学。只上了半年,他又偷偷地考上了一切费用全免的北京师范学校。
5年后,年仅19岁的老舍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国民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前身)校长。由于工作出色,他于1920年9月30日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兼教育部京师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
在这些岗位上,他本想大刀阔斧地干点正事、实事,不料却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一度失意消沉。同时,因他擅自退了由母亲包办订的亲,以致母子俩产生了隔阂,他自己大病了一场,独自入住西山卧佛寺静养了一个月才好。这段经历在他4年后所写的初女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有所反映。
这期间爆发的“五四”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老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在当时勃然兴起、势不可挡的白话文运动的冲击下,已有一定文言体散文和旧体诗词底子的他,开始着了魔似地偷偷用白话文练着写小说。不过,这些习作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他也没想去投稿。
1921年春夏之际,老舍从西山养病回来,搬到由自己兼管的京师儿童图书馆去住。当时,他志在学习英文,便参加了缸瓦市基督教堂举办的英文夜校,一周上5次课,每次两小时。在夜校,他与宝广林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许地山等结为好友,并通过宝广林结识了“伦敦会”派往燕京大学任教的牧师埃文斯,老舍遂在业余时间跟埃文斯学习英文。
1922年8月,老舍辞去北郊劝学员之职,赴天津南开中学任教,并于次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小铃儿》。
客居英国写北京
通过已返回英国任教授的埃文斯推荐,老舍受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聘期5年。他于1924年9月14日乘船来到伦敦,起初与来此留学的许地山合租一套房子,整日沉溺于小说创作的许地山对老舍产生了影响。此后,老舍又搬了几次家,多是廉价的学生公寓。作为讲师,最初他的年薪仅有250英镑,后虽然增至300英镑,但他除了自己开销,还要寄钱回国养活老母,因而只能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生活的清苦倒在其次,让他最难堪的是房东对他的奚落和白眼。
老舍在东方学院所授课程,除了教授官话(北京话)和“四书”之外,还有《史记》、佛教和道教等等。按照该学院的学制,每年共有近5个月的假。每逢假期,他便一头扎进学院图书馆,或饱读英国文学原著,或创作小说。
像许多身在异国他乡的人一样,来伦敦还不足半年,老舍便寂寞难耐,开始想家、想母亲、想朋友、想北京、想故国。正是这种浓烈的思乡之情,激起他最原始的创作冲动。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一木一石,当追忆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好多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能产生好的作品……这种作品里,也许是对于一人或一事的回忆,可是地方景况的追念至少也得算写作动机之一。”
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更为了借鉴写作经验,老舍杂七杂八地读了许多英国文学原著,其中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让他感到写小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于是,他有了模仿的念头,他后来回忆说:“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尼考拉斯·尼柯
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
灰暗惨淡的童年时光、艰辛备尝的青少年时期,对于这些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老舍总想把它抖擞出来给别人看,写作由此成为他一吐胸中块垒的绝好途径。1925年,他回忆着自己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一幕幕经历,开始在东方学院图书馆里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断断续续一年后才完稿。有关当时的写作情景,他后来回忆说:“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些,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
适逢国内《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正在伦敦,老舍就把《老张的哲学》原稿拿给他看,得到的评价是“很好”。不久,这部小说在《小说月报》1926年7月号上,以本名“舒庆春”开始连载,第二期即改署笔名“老舍”,半年后才登完。次年,这部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因其文风幽默?京味”十足,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状况描写真实、揭露有力,故而轰动一时,销路很好。
此后,老舍继续沿着这条创作路子,又写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群住在北京某公寓里的学生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生活。该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又出了单行本,颇受广大读者欢迎,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再版了7次。
老舍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一半写北京人,一半写伦敦人,且故事发生在伦敦。当这部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老舍已离开伦敦,在欧洲大陆游历了3个月后,于1930年春返回祖国。
成熟的“京味”作家
回国后,适逢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时刻觊觎着华北大好河山。在民族危亡日渐深重的形势下,老舍辗转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抗日救亡事业而奔波。1946年3月以后,他应邀赴美国从事讲学和文化交流活动近4年之久。
在离乡背井、流落外地的近20年间,老舍很快成长为一个“京味”浓郁、风格独具的作家。
1930年7月至1937年11月,老舍在济南和青岛工作、生活期间,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创作丰收期。在此,他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此外还有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等,其中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和短篇小说《月牙儿》是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特别是《骆驼祥子》的问世,奠定了老舍作为一个成熟的“京味”作家的重要地位,这部作品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作为老舍写作生涯中的破釜沉舟之作《骆驼祥子》是他成为职业作家的重要标志,因此他说:“这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做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
《骆驼祥子》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老舍与山东大学一位朋友的闲聊,这位朋友在闲谈中,说起他在北平时曾接触过的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朋友说这个车夫曾买了一辆人力车,后又被迫卖掉,如是者三买三卖,到头来依旧一穷二白。老舍听后脱口说道:“这可以写一篇小说。”继之,这位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谁料因祸得福,他乘着军队仓促转移之际,顺手偷偷地牵回3匹骆驼。老舍说道:“自此,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10多万字的小说。”
老舍开始进行资料积累工作,首先去信向生长于北平西山一带的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因为西山脚下有许多养驼人家。很快就得到了回信及有关的简单介绍。由于对骆驼没有真切的认识和感受,老舍感觉到,要写这部小说,就必须以车夫为主,而以骆驼作点缀和陪衬。于是他决定,把骆驼与人力车夫祥子结合在一块儿写,而骆驼只起到引出主要人物的作用。
老舍又分别写信给自己的哥哥、表哥、同学以及有关的专家,打听关于骆驼、洋车、车厂以及人力车夫的琐事,打听有关的口语字、词。他甚至还利用回北平给祖母操办80大寿之机,采访熟悉上述情况的下层百姓。
在此基础上,老舍一鼓作气开始写《骆驼祥子》。这部作品从1937年1月起,始在《宇宙风》杂志上连载,一期两段,年内刊完,后来被陆续翻译成26种文字、以38种不同的译本流传海内外。在这部优秀的小说中,老舍通过对主人公祥子在北平的7次行动路线的具体描写,使人们对书中的古都北京的认识更加立体。
3卷本计80万字的《四世同堂》,是老舍毕生卷帙最为浩繁、耗费精力最多的长篇小说。当时,因故滞留于沦陷区北平,过了5年亡国奴生活的妻子胡絮青,终于带着3个孩子逃了出来,辗转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从妻子口中,他了解到许多关于北平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惨状。于是,他深怀家破国难之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于1944年初开始动笔,并自11月起在重庆的报纸上连载。但由于深受贫血、打摆子和肠胃病的折磨,加之时局动乱不安,直至1945年底他才完成《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第三部《饥荒》是老舍赴美国后完稿的。
《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该小说在美国翻译出版后,立即入选“每月佳作俱乐部”的优秀新书,美国评论家康斐尔德对老舍给予高度评价:“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老舍的出生地北平小羊圈胡同,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写入这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中。
一代“人民艺术家”
1949年7月,客居美国纽约的老舍,收到一封来自解放了的北平的信,信末附有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等30多位知己好友的联合签名。信中说:“第一次文代会即将在北平举行,老朋友们已经全部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来吧,老朋友!祖国的文艺繁荣等着我们的笔,包括你的笔……”
这封信就像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巨大召唤,让老舍归心似箭。他刚做完手术不久,就急匆匆地辗转回国,于当年12月11日抵达北京,很快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
切接见。此后,老舍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
1950年4月,老舍购置了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一所普通的四合院,一家人从此定居在这里。直至“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老舍在此生活了16年,期间除了继续写些小说、散文之外,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大众曲艺事业和话剧创作中。
建国初期,北京的相声艺术事业陷入了危机,相声演员一味地表演旧社会的老段子,与新中国的时代氛围相距太远,逐渐失去了听众。但是,说新段子,又缺乏现成的本子,因为当时的相声演员绝大多数文化水平都不高,自己动笔很困难。为此,他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并派侯宝林、侯一尘等专程拜访老舍,请他帮助写新段子。老舍慨然允诺,请他们回去选几个老段子,把本子送给他看。
很快,老舍就交出了三篇新段子《维生素》(改编《菜单子》)《假博士》(改编《文章会》)和《逛隆福寺》,他对来拿新本子的相声演员说:“请先试着说说,听众要是喜欢,咱们接着往下搞;要是不成,咱们再改辙。上演的时候,一定先告诉我一声,我也去听听。”
后来,在曲艺场上演的时候,老舍如约前来观看,见听众们反应热烈,他也颇感欣慰。接着,老舍又陆续改编了《绕口令》《铃铛谱》《对对子》等段子。与此同时,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京韵大鼓《别迷信》,在《说说唱唱》杂志上发表了鼓词《生产就业》等,以其不懈的创作实践,为促进北京市大众曲艺事业出了力。
龙须沟是北京城南一条有名的臭水沟,尽管这里脏、乱、差,解放前却从来没有人过问。1950年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把对龙须沟的治理作为建设新北京的举措之一。很快,龙须沟一带的面貌就大为改观,赢得了市民的热烈称赞。这时,老舍的好友李伯钊等建议他据此写一个剧本。老舍经过一番实地采访,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三幕话剧《龙须沟》,第一幕写解放前,后两幕写解放后,通过新旧社会龙须沟面貌的巨大反差,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本色。
不久《龙须沟》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执导排成话剧,于1951年2月2日在北京解放两周年纪念日上演,盛况空前,一直演到年底。全国文联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周扬为此发表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高度赞扬了《龙须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认为“从《龙须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并倡议让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和他一同学习,并向他学习吧”。
鉴于老舍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紧贴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为繁荣北京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授予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使他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受此鼓舞,老舍又先后创作了《一家代表》《柳树井》、《春华秋实》等30多部新戏剧,其中公开发表的有22部,包括15部话剧、3部歌剧、一部曲剧和3部京剧。特别是极富创新意义的《柳树井》,标志着一个名叫“曲剧”的新剧种从此诞生。
转眼到了1957年,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指引下,老舍开始创作一部关于宪法和民主选举的话剧剧本,名为《茶馆》。他从清朝光绪时期写起,写了北京的一个大茶馆,通过到该茶馆中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反映整个社会。第一幕完稿后,他照例朗诵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导演听,结果大受好评,大家都争着要演这个戏。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该剧应通过一个茶馆的变迁写出5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要力争成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老舍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第一幕作了修改,又一气呵成很快写出了第二幕、第三幕。
这年7月《茶馆》剧本在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号上发表。1958年,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话剧舞台,每次演出都是观者如潮,盛况空前。但在后来的极“左”风暴中,它却受到猛烈批判,自此停演尘封16年,直至1979年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半个多世纪以来《茶馆》一共在国内外上演了400多场,它不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而且还曾于20世纪80年代漂洋过海,在联邦德国、法国、瑞士和日本等国上演,颇受欢迎。作为老舍的代表作之一《茶馆》已然成为新中国话剧史上极富艺术魅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作。
老舍具有浓郁的北京情结,可以说,没有在北京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就没有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是北京古老而厚重的文化沉淀,给了老舍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