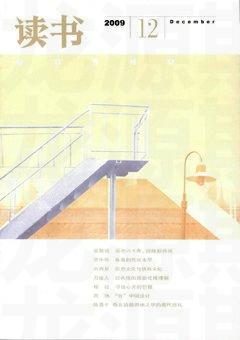德国名师手下的中国高徒
陈洪捷
季羡林成为一名印度学大师,应当感谢哥廷根大学。正是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季羡林找到了他终生的事业。他在晚年说过:“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将近六十年,今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如今斯人已去,季羡林一生的梵学探索之路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称哥廷根是他的“第二故乡”,因为他在此度过了十年的青春岁月。其实,这座位于德国中部的大学城更是他的“学术故乡”,他在此师从两位印度学大师,受到一流的印度学训练,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十年前,我在哥廷根大学开始寻找有关季羡林的材料。在大学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季羡林的博士论文。那是打印本,青蓝的封面显得陈旧,内页纸质不好,已经发黄,共一百一十八页。扉页上打印的署名是Hin-Lin Dschi,这是德文的写法,而他本人在旁边特地手书签名Shiann-Lin Jih。看来季羡林不喜欢德文的拼写,更喜欢用中国自己的、或者他已经习惯的拼写方法。我随手翻看着论文,仿佛看到青年季羡林当年在哥廷根寂寞苦读的身影。按照德国的习惯,博士论文前面要附上作者的简历。季羡林在简历中专门提到他的两位导师,对他们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我要特别郑重感谢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他是我进入印度学的领路人,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提出了建议,并在整个论文工作期间自始至终给予支持和指导。西克教授平时就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其宝贵的指导,在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从军期间,更是评阅了我的博士论文,并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在此我谨对西克教授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应该说,季羡林非常幸运,由于特殊的机缘,同时得到两位印度学大师的指导,一位是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教授,一位是西克(Emil Sieg,1866-1951)教授。
瓦尔德施密特是柏林大学著名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的学生,后来以研究在吐鲁番发现的梵文佛典残卷而著称。一九三六年,年方三十九岁的瓦尔德施密特被聘为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教授。也就是在同一年,季羡林经过几番考虑,最终决定攻读梵文。事后看来,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对季羡林的一生意义重大。据季羡林回忆:“一九三六年春季开始的那一学期,我选了梵文。四月二日,我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这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同他会面。”
瓦尔德施密特第一次走上讲台,来听课的居然只有一个学生,而且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第一次讲课,第一次听课,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初次见面颇有戏剧性。按中国的说法,这师生二人看来缘分不浅。
季羡林从此喜欢上了梵文,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业上。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季羡林便向瓦尔德施密特提出写博士论文的愿望。季羡林不屑于像许多中国留学生那样,取巧写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发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其实导师开始就建议他在选题时应该考虑利用汉语文献的优势,但季羡林更想成为一名与欧洲同行平起平坐的梵文学者。经与导师商量,他最终选择《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所谓《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用“混合梵文”写成,文字艰深难解,这种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的语言对于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所谓“偈陀”意译为“偈”或者“颂”,是佛经常用的一种体裁,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它虽然只是《大事》的一个部分,但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部分,而且篇幅很大。季羡林从此就“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两年之后,博士论文基本完成,题目直接而具体,就是《〈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
关于他的博士论文,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提到哥廷根大学克劳泽教授的评价:“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法》)被认为能跟西克、西格灵、舒尔策的吐火罗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耦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意义。”但两位导师对他的博士论文究竟评价如何,季羡林并没有提供具体的信息。
其实他本人很可能只是听过导师口头的评价,没有看到过导师给他博士论文的书面意见。哥廷根大学档案馆中至今保存着两位导师对季羡林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这对我们了解季羡林博士论文的贡献,特别是季羡林的学术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看看两位名师是如何评价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的。
瓦尔德施米特是季羡林的导师,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应征入伍,去了德国北部的叙尔特岛(Sylt),只能利用假期抽空对季羡林进行指导。季羡林说:“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瓦尔德施米特对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就写于叙尔特岛,时间是一九四○年十二月一日。评语这样写道:
担任语言教师的季先生(季羡林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在汉学所担任中文语言老师——译者注)两年前就其博士论文题目向我咨询,我首先建议他参与佛教文献中的某些问题的研究,并建议他从事一个可以利用一些汉语文献的题目。季先生在考虑之后告诉我,他更愿意从事语法方面的研究题目,并成为一名印梵文语文学者。今后他显然会运用汉译的佛教文献从事比较研究,所以首先想通过其处女作成为一名接受欧洲训练的印度学者。我觉得,他放弃一个对他来说相对容易的、而选择一个更有难度的题目,其志向可嘉。从此我注意到,季先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从事其工作,论文在逐步成形。
关于论文研究对象的一般意义以及语言方面的难点,同事西克在其评阅意见中已经有清楚的说明。该论文对于理解和认识“混合梵文”,做出了有分量的贡献,它虽然没有对《大事》的语言做出完全的描述,因此没有结论性的意义,而且讨论的只是文献中诗歌部分的动词,但是诗歌部分篇幅巨大,也是核心的和语言方面最有意思的部分。找出所有相关的材料,并系统和明确地给予排列组织,这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感悟力。就所研究的文献部分而言,分析可谓穷尽无遗。其研究为本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实际的便利,在阅读这些迄今只是节译的文献时,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供查阅参考。
我在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指导,知道季先生的研究扎实而可靠。在我应召入伍期间我与季先生保持着联系,利用休假时间多次看他的论文,一直到九月份论文提交之前。
正如西克教授所指出,在文献翻译中还存在若干不顺和不清楚的表达,但这些在付印之前不难修改更正。总体看来,季先生虽然在教育背景和语言背景上如此不同,但作为一名东亚人,他对德国学术训练的掌握达到罕见的完美程度。季先生一定会有所成就。
因此,我同意西克教授的意见,同意他参加博士答辩,论文成绩为优秀。
可以看出,瓦尔德施米特对这位中国弟子的评价很高,首先肯定论文的选题,认为选择了有难度的题目,“其志向可嘉”,其次赞扬研究工作“扎实而可靠”,最后在总体评价时,认为季羡林“对德国学术训练的掌握程度达到罕见的完美程度”,而且坚信季羡林“一定会有所成就”。瓦尔德施米特没有看错,季羡林在后来果然没有辜负导师的栽培,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印度学家。
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季羡林很可能完全在瓦尔德施密特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但由于战争,导师瓦尔德施密特应征入伍,西克教授才得以“返聘”,季羡林也有了接触另一位印度学大师的机会。
西克一九二一年到哥廷根大学任梵文教授。他早期以研究《吠陀》而著名,后来由于参加了中亚古卷文字的破译而转向吐火罗文研究。在一九○三到一九一四年中间,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四次派出考察队前往新疆地区,考察队在格伦维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Le Coq)的带领下带回了大量的古文献和实物,其中有大量的用不同文字写成的残卷。这些残卷出自公元一世纪,具有很高的价值。柏林大学的梵文教授召集了若干年轻的梵文学者开始研究这些残缺不全的手卷。西克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负责解读一组主要用婆罗谜字母写成的残卷,他与助手西克灵(Wilhelm Siegling)很快读通了这一语言,并证明了此种语言为一种印度日耳曼语言,将其命名为吐火罗语。西克又经过数年的努力,于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吐火罗语语法》。关于此书,季羡林说:“这一本五百多页的大著就成了欧洲学术界划时代的著作。一直到现在,研究中亚古代语言和比较语言的学者还不能离开它。”
瓦尔德施米特入伍后,已退休的老教授西克重返讲坛。季羡林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西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作为吐火罗文专家,西克一心想将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传授给勤奋好学的季羡林。恰好一位名叫古勿勒的比利时学者也来到哥廷根,意欲学习吐火罗文。季羡林说:“时机正好,于是一个吐火罗文特别班就开办起来了。大学的课程表上并没有这样一门课,而且只有两个学生,还都是外国人,真是一个特别班。”
季羡林的博士导师虽然是瓦尔德施米特,但在申请答辩考试过程中,由于导师从军在外,所以具体是由西克教授操办的。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克就为季羡林的博士答辩向哲学院院长写了一份推荐意见,内容如下:
尊敬的阁下,我十分荣幸地在本月二十七日致信之后再寄上如下评议意见。
同事瓦尔德施米特一直很称赞季先生的能力。我上学期开设的《梨俱吠陀》阅读课和相关课程,季先生积极认真参加了这两门课程,由此我也深信他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季先生异常聪明。我可以说,在我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来自远东的学生中无人能像季先生这样能对印度学有如此的理解和深入的研究。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同事瓦尔德施米特帮助选定的,题目本身就体现了导师对他研究能力的特殊信任。只有完全掌握德国的研究和学术方法的人,才能完成如此之题目。我虽然迄今尚未阅读论文,但我从与季先生的数次交谈中感到,论文的框架和论证合理,达到其语言学研究的目的。
季先生对德语的掌握如此之纯熟,可以很好地参加讨论,将外文翻译成德文,这也证明了他超凡的语言能力。
关于季先生的性格,我只能说,他始终是一位谦虚、可亲和正派的人。对此,我完全可以作证。
总之,我全力支持季先生关于参加博士考试的申请,而且深信,我们可以自豪地将此年轻的博士送回其家乡,他一定会在那里为德国的学术增添荣誉。
看得出来,西克对季羡林的学术能力和人品非常了解,虽然还没有看论文,但对其论文已经做出了完全的肯定。特别是最后一句对季羡林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深信季羡林能够在中国“为德国的学术增添荣誉”。
西克在一九四○年十月四日还为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写了正式的评阅意见书。内容如下:
佛教的梵文文献中,有一部分、主要是在韵文部分,文字很不规范。这些文字开始被认为是Gatha方言。但后来发现,同样的语法错误不仅在诗歌中,而且也在叙述文字,特别是在铭文中出现,因此被称作“混合梵文”。关于这种方言或者混合梵文的来源,尚有争议。根据多数专家的看法,这可能是一种(印度中部)被梵文同化的方言。方言的使用者想使用更加高雅的梵文,但梵文知识有限。如果能有计划地搜集和梳理所有变化形式,将有可能对此做出结论。之后才可以肯定地说明,是否在“错误的”构词中也存在一定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其中部印度民间语言的来源。
该论文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位,是系统搜集其中词型变化的最初尝试,虽然仅限于变位动词的变化,但结果已经相当可观。《大事》是混合梵文的主要文本,规模宏大。而且篇章之间缺乏联系,所以除了语言问题,理解起来还有其他重重困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好季先生的能力,故建议他以此问题为其博士论文的对象。季先生出色回报了导师对他的信任。论文对动词的搜集和梳理在我看来是完全可靠的。其构词形式得到正确的解读,并通过与其他印度中部语言的对照和比较澄清了其来源。对于难以理解的部分,附有译文,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相关的动词形式是否理解正确,是否排列正确。作者不是完全有囿于文本或者编者勒纳特的注疏,而是参考了其他手写文本的读法,有时并不限于现成的解释,而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整个论文显示,作者彻底掌握了德国的研究和教学方法。我非常高兴地推荐作者参加答辩。关于成绩,我毫不犹豫地建议给予一分。论文中有若干小问题,主要是由于外国人对于德语掌握不甚娴熟所致,应该在付印之前进行修改。
西克在评阅书中对季羡林论文研究的背景进行了说明,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论文的学术意义,以及研究工作的难度。同时,西克一如既往,对季羡林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作者彻底掌握了德国的研究和学术方法”,所给的成绩是一分,这是德国五分成绩系统中的最高分,如同“优秀”。
总之,两位导师都非常欣赏季羡林的学术才能,无论对其研究工作,还是对其学术能力,或是他的为人,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季羡林的未来学术之路,寄予了极高的希望。名师的指导和殷切的期望显然对季羡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在谈到瓦尔德施米特时说:“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有什么成就呢?”他又说,西克“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甚至几十年之后,他还说:“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季羡林似乎一生也没有忘记两位名师的教诲和期望,勤奋地从事印度学的研究,终于成为德国名师手下的中国高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