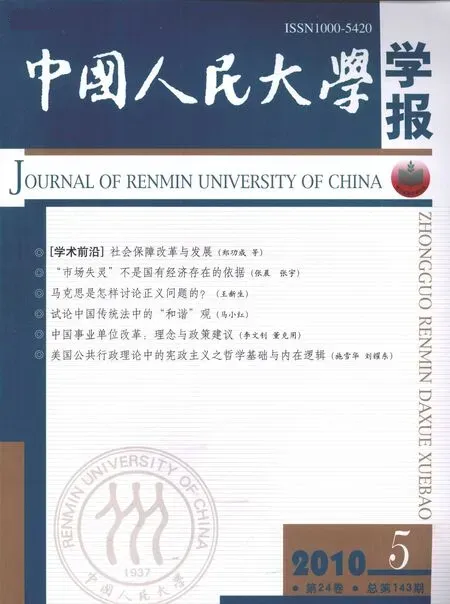试论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
——兼论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马小红
试论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
——兼论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马小红
中国古代法律所维护与追求的和谐原本出于“乐”,是“一统”与“多元”的有机协调,这种和谐观造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多样、礼乐政刑综合为用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和谐”虽然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但其却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理想,也是不同时代和地区法律普遍追求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理念经过改造、更新,完全可以成为促进现代社会法律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法;和谐;法理念
古今法理念连接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法学研究工程。中华法文明蕴含着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智慧,其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比如,中国古人对“立善法”的追求,对立法须“法自然”的强调,主张法律应兼顾社会公正与秩序,“惩恶”与“扬善”并重,等等,都可以通过今人的阐释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法理念。所以,古今法理念的连接绝非一篇论文甚至一本专著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本文之所以选择“和谐”的理念作为研究分析的目标,原因在于:首先,“和谐”是中国古代法中的重要核心理念之一,其与古代社会“礼乐政治”相匹配。其次,“和谐”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与学界的流行用语,受众面甚为广泛。但是,对“和谐”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并不多见,和谐的原意是什么?古人赋予它怎样的内涵?作为法理念的“和谐”是否有制度的体现?等等。也许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谐理念在古今的连接中才可能真正地获得新生。
一、“和谐”与“乐”——和谐原意
和谐,在古代中国与“乐”的联系最为密切。
《礼记·乐记》(以下简称《乐记》)对“乐”做了这样的描述:心有所感而有“声”,声分“宫、商、角、徵、羽”五种,这五种声音有高有低,有扬有抑,单出而为“声”;“声变”,即五声组合在一起则成“音”,“音”即歌曲;音配以乐器、舞蹈,组成“乐”。[1]
乐,对于人类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与“政事”相通,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乐记》这样阐述人类社会的文明及其发展:“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如果说“音”是人类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那么“乐”则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人们可以通过“乐”观察一个社会的兴衰和治乱,即《乐记》所言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
关于礼与乐的关系,笔者将在后文中论述,在此着重对“乐”的核心进行探讨。乐是音、器、舞的组合,音是声的组合,因此,这种组合体现了“乐”的核心之义——“和”,唯有“和”,才能有“乐”。《乐记》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和”造就了“乐”,而“乐”也体现了“和”。
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乐与和谐的关系,以探求和谐的原意。
和谐中的“和”字,原本是形容“音正”的,即五音各有高低扬抑,在组合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清代经学家孙希旦在解释《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时,言:“乐以养其心,而发于声者乃和,故曰‘乐以和其声’。”喜、怒、哀、乐、爱、敬之心,人不能无,“惟感之得其道,则所发中其节,而皆不害其为和矣”。中节的“音”即为《康熙字典》中对“和”的解释:“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和谐中的“谐”字为“协调”之义,“谐”与“和”之义大致相同。晋人杜预在注释《左传》时言:“谐,亦和也。”[2]对乐而言,“谐”就是将诸音合为一体并使“各得其所”。汉经学家郑玄言:“八音并作克谐曰乐。”[3]“谐”也含有“成”的意思,《后汉书》记汉光武帝刘秀欲将新寡的女儿湖阳公主许配给大臣宋弘,宋弘对光武帝说“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委婉拒绝。光武帝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后汉书·宋弘传》),即无法协调、事不成之意。
《乐记》开篇这样定义“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方成,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即不同的声音,配以乐器舞蹈谓之“乐”。而“和谐”的本义也是协调多种声音、乐器、舞蹈而成有机的体系。所以,在古人观念中,和谐即乐,乐即和谐。《左传·襄公十一年》记晋侯将郑人所送之乐师、乐器等一半转而赏赐给魏绛,表彰魏绛在“合诸侯”中的功劳,晋侯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杨伯峻先生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下注“如音乐之和谐”。[4](P993)
由此而言,乐体现的和谐有两层含义:
第一,和谐不是一种声音或一种乐器所能完成,它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即必须是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之间相互配合而发出的,若只是一种声音,或只有音而无器与舞,就谈不到“和谐”。所以,古人认为,音须“变”而“杂”,方有和谐,方能成“乐”。郑玄解释“音”时说:“宫、商、角、羽、徵杂比曰音。”孙希旦又言:杂糅五声之音尚不可称之为乐,须“比次歌曲(即音),而以乐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舞蹈以为舞,则声容毕具而谓之乐也。”[5]和谐的关键是不同的乐器和声音在“乐”中能各得其所,恰到好处地表达或抒发人们的情感,以达到“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礼记·乐记》)的境界。“乐”的理念是和谐的理念,而和谐的乐章一定是发自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声音。
“审乐以知政”。君主治国也是如此,一定是多种意见的综合与协调。先秦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和”与“同”的区别,最能反映乐的这一理念。齐国晏子对齐君说,君臣之“和”在于“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君臣之“同”则是君谓可而臣亦谓可,君谓否而臣亦谓否。“和”不是“同”,同是一种声音,“如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所以“和”与“同”不一样。[6]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和”是多种声音的协调、多种意见的统一,而“同”只是对一种声音和意见的盲从和依附。
第二,乐由多种声音构成,可谓“多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的“音”在乐中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乐记》用子夏之言区别“音”与“乐”的不同,即“德音之为乐”。德音,也就是合乎“道”的“君子”之音,而不是“小人”无节制的情感发泄之音。“乐者,乐(le)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在子夏看来,“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的古乐,即为德音。德音为乐,而德音的标准则是“律”。律为定音之器。《晋书·挚虞传》记载,晋武帝时,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而古尺较当时晋所用的尺短近半寸,有人建议说因为用“今尺”已经很长时间了,不宜再用古尺校正长短。挚虞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古人效法天地自然而定的律(定音之器)、度(计量长度之器)、量(计量容积体积之器)、衡(测定重量之器),是“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徴。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挚虞坚持认为古人所确定的量物定音的标准之器是“象物制器”而成,可以使万物各得其所(皆正)。文中所言“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意为只有符合古人的定音标准——律,才有和谐之乐。所以,德音是律之“一统”的产物,是乐之正音。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乐所体现的和谐模式是“多元”之音与“一统”之“德音”的结合。
二、“礼乐政刑,其极一也”——和谐理念的发展
乐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乐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有着多种功能,向神表达敬畏之心需要乐,战争的指挥需要乐,族群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感需要乐,氏族日常的生活也需要乐。中国古人更是将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即以乐来反映自然界的变化、反映阴阳的消长。乐的基础为“律”,前文已述律是定音之具,是音“发而中其节”的检验标准。古人之所以将定音之具称为“律”,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中“律”之音所反映的是自然界节气的变化。《汉书·律历志》按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设定十二音,称为十二律(或称六律,即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十二律名称见《史记·律书》)。律“所以述阳气”(《释名》)。“吕,助阳气也。”(《汉书·律历志》)律音展现了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阴阳变化,其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在古人的观念中,尤其是在初民的观念中,毋宁说是神意的体现,人间的法度只不过是神意的延伸。司马迁在《律书》中开篇即言:“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史记·律书》)由此,乐沟通了神意与人间的法度,即《乐记》中所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音是否“中律”、乐是否“和谐”,关系到神的庇护与族群的兴衰。《乐记》将“音”分为“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在人类社会早期,乐在国家的治理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后人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因为乐是与自然、与神圣沟通的渠道,所以它几乎是当时人们全部的精神寄托。《乐记》言:“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治乐以治心,则易、直、子(慈)、谅(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在此,乐的作用可比拟于宗教,其是人类心灵与天则、神则相通的枢纽。明代真德秀这样解释礼与乐的关系:“礼之治躬,止于严威,不若乐之至于天且神者,何也?乐之于人,能变化其气质,消融其渣滓,故礼以顺之于外,而乐以和之于中。此表里交养之功,而养于中者实为之主,故圣门之教,立之以礼,而成之以乐也。”[7]乐所到之处,无不和谐:“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礼记·乐记》)这种重乐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也就是上文说到的人以不仅知“声”而且知“音”为标志脱离了“禽兽”界而进入了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称为“乐治”时期。
礼,最初作为祭祀鬼神的仪式而成为乐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演变成社会风俗和秩序。礼、乐的区别在《乐记》中是这样描述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则群物皆别。”随着社会的发展、族群的融合、人类社会治理经验的不断丰富,礼、乐的内容和含义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众所周知,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尽管历代统治者对周公“制礼作乐”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囿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至今也无法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原因和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只是从后人追记的资料归纳,我们可以看出周初的统治者在夺得政权后,面临着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的双重难题:在意识形态方面,周人必须对商王朝笃信鬼神却又被鬼神抛弃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周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会受到天下质疑;在秩序制度方面,周人的经济发展原本落后于商人,王权远不如商强大,只有利用族人和传统的亲和力,才能稳定政权和局势。所以,周初统治者对以往的制度观念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周人的统治寻找理论与制度的支持,而改革的结果是“礼治”或“礼乐之制”取代了“乐治”。这场改革的烈度,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8]笔者在《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中,曾将西周的礼治体系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礼义”,即礼的精神之所在;二是“礼仪”,即礼的外在制度表现。[9]令笔者遗憾的是,虽然笔者当时意识到了礼义的内容应该是古乐的演变,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而未敢涉及。其实,礼义所体现的礼的精神正是古乐“和谐”宗旨的延续,西周时期的为政、为国,已然从“乐治”进入到了“礼乐之治”或“礼治”时代。从《论语》来看,孔子对周礼的论述远远超过了乐,将西周政治社会模式作为理想的孔子,提出的救世之道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礼治更换了乐治,显然是因为讲究秩序的礼比注重人心熏陶的乐更好把握。①孔子认为,即使周人之乐也不如古乐完善。《论语·八佾》言“: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为舜时乐《,武》为周武王时乐。古乐经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又经秦政,已难复兴,故《晋书·律历志》言“:汉室初兴,丞相张苍首言音律,未能审备。”可见,汉代古乐已经失传,只能复兴礼教。因为,体现人们宗教情感的“德音”,唯有德才兼备的君子才能够体会,民众知音而不知乐,乐在国家的治理中缺乏普适性。此外,更有一些失律之音会给国家与社会带来混乱,如“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等。与乐治相比,讲求“异”、“别”、“序”、“敬”的礼治,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这就是《乐记》强调的“乐”须以“礼”节制方能成“和谐”之音的原因。②《乐记》言“: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即以乐抒发人们的情感,须合于礼,只有合于礼,才能恰到好处。身处礼崩乐坏之际的孔子,在总结周人统治的经验时,将乐的“和谐”精神纳入到了“礼治”体系中,孔子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原本“和”是乐的核心,而孔子认为其也是礼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不以礼“节之”的“乐”会偏离“和”音,孔子总结的周之礼因此兼有了“别”与“和”的双重含义,乐的和谐精神也就变成了礼的宗旨。
从初民的乐治到西周的礼治,乐以养心的和谐精神并没有中断,随着礼的内容的拓展,乐转化为礼义,即“德”。
乐与德在儒家早期的经典中几乎有着同等的含义。《论语》中的“德礼政刑”在《乐记》中则为“礼乐政刑”,试将两者比较如下:
《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乐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论语》中的“德礼政刑”之“德”,与《乐记》中的“礼乐政刑”之“乐”同义,即发自人内心的神圣情感,即乐治时代的“德音”、礼治体系中的“礼义”。《乐记》自释“乐者,所以象德也”。经学家孙希旦亦言“乐在于示德”。[10]
由于“乐与政通”,所以乐所体现的“多元”与“一统”的和谐模式渗透到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西周时的礼治,还是汉代以后的礼法并用,“和谐”始终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最高境界。孔子将和谐的理念用于治国,总结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开明的统治者及有道德修养的人,可以和具有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人和睦相处。这种主张既是西周“明德”、“保民”思想的总结,也是儒家“民本”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中主张君主“兼听”、主张民众“议政”的思想亦源于此。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注重将“和”与“同”相区别的思想仅见于先秦儒家。秦以后,统治者在治国中往往更注重和谐模式中的“一统”含义,即强调“德音”的主导地位。秦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政治上出现了“琴瑟专一”的状况自不待言。即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也只是有限度地“杂糅百家”,文化上较秦暴政略有宽松,但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已有很大的区别,即对和谐中“一统”主导的强调远远胜于对“多元”并存的关注。于是,东汉思想家仲长统对和谐的解释也就成了:“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依。政专则和谐,相依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慌乱之所起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自汉以来,和谐的宗旨体现于乐、礼、政、刑的各个方面。如果用现在社会的语境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法,我们很难寻找到相互对应的概念,也许我们可以笼统或勉强地将中国古代法的模式解释为礼乐为之精神,政刑为之规范。从乐治到礼治,再到礼法合治,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不断变化着的是制度条文,而不变的则是和谐的精神。
三、“法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古代法律体系对和谐理念的体现
中国古代法律是在和谐理念指导下,或是古人在对和谐理想的追求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其对和谐精神的体现也是全面的。比如,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以家族教育作为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息讼止争以安定社会等等,都与和谐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本文不再赘述。笔者在本文中所要重点阐述的是古代法律体系对和谐理念的充分体现。
所谓体系,是指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关事物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简单地说,法律体系就是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社会,如果与现代社会相比的话,社会的经济活动相对平静,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人们的生活相对简单而安逸宁静。农耕社会是以农为本的“综合”型社会,社会的分工并不精细,人们亦官亦农、亦学亦农,社会的经济中心在“农”,政治文化的核心在“官”。如此社会环境中的“法”当然不会同于今天。在这样一个稳定的以“安居乐业”为追求目标的社会中,“经验”对变化甚微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王朝统治的基础靠历史的经验,家族的壮大靠祖辈经验的积累,个人的发展也须从前人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无论是对国家、对家族,还是对个人,“祖宗”都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祖先之法”常常被奉为圭臬,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王朝来说,帝王祖先,尤其是有兴邦立国之伟业的祖先所订立的制度甚至是祖先的“故事”,都会成为后世必须尊奉的法度。“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守成帝王的为政信条。其实,在古代法律体系中,“祖宗之法”往往就是王朝法律的主旋律。这个“祖宗之法”对于国家来说,并不仅仅指狭隘的有着血缘关系的祖先之成规,而是泛指以往历朝历代历史经验的总结,如《唐律疏议》所总结的那样:“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法律一脉相承,延绵数千年的原因。
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它的表现形式是“综合”。在这个综合的体系中,如同先民的“乐”那样,形成主次分明、急缓有序的体系。说其“主次分明”,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法律精神总是第一位的,在法律精神与法律条文发生冲突时,即经与律相违、礼与法相悖的偶然状况中,“法官”基本上会维护经义。比如,对为亲复仇的孝子烈女、为义犯禁的侠客义士等,法官会网开一面。说其“急缓有序”,是指中国古代法律对“刑狱”案的审判多有严格的程序,属于“急”办之案,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亲属邻里间的“细事”纠纷则属于“宜缓不宜急”之事,多采用调解的手段化解。这种“急缓有序”往往被今人误读为“重刑轻民”。
与现代法律体系不同,我们从古代的经书、政书、官箴书、案牍、律典、蒙书、族谱家训中,都可以看到“法”的内容。律是王朝颁布的统一的法律,而经则是律的灵魂之所在。从法律规范的组合看,围绕着经律,各官署衙门的规范几乎将我们今天部门法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囊括其中,形成了以官署为中心的法律体系。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行政法的一些内容便可以划归到吏部、御史台的职能规定及“吏律”中,刑法的一些规范可以划归到刑部、大理寺的职能规定与“刑律”中,民法、经济法的一些规范可以划归到户部的职能规定与“户律”中,等等。这种体系的形成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官”所处的政治核心地位所决定的。
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法律以这样的一些特点体现着和谐的精神:
第一,以礼为主,多层次。
中国古代法律体现着礼的和谐精神和宗旨,这一点众所周知。就法律体系而言,礼的规范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即使在规范制度中,礼同样占据着主导地位。有许多我们现在称之为“法”的内容,在古人的语言中则往往被称之为“礼”。国家颁行的诏令、律、律疏、典中有大量的“礼”的节文和规范。比如,各王朝的“衣服令”,详细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所应穿着的衣服的质地、纹样和配饰,不同品级的官员上朝、办公服饰也有所不同。龙凤纹样为至尊的皇帝所独有,其他人不得穿用。元初中书省上奏,街市中有人卖仿造皇帝穿的龙纹布料,只是将龙的五爪改为四爪而已。于是,元武宗下诏沿用汉人服饰制度,规定即使蒙古人也不许穿龙凤纹衣服。[11]中国古代对财产、家庭的“争讼”也基本上依据“礼”来裁决。比如,乡规民约与家法族规的订立基本上遵循着“符合礼教”、“注重教化”、“符合国法”三项原则。[12](P28)
第二,执行法律时注重社会效果,旌表与惩罚并用。
中国古代审判裁断以“天理、国法、人情”为依据。当三者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不协调时,裁断者往往会变通法律的条文而以符合天理人情——法律的最终要旨为要。这就要求“法官”不能只理解法律条文而“守文定罪”,而是要求“法官”深切体会法律的精神,以裁断体现法律的目的——维护社会的和谐而不是激化社会矛盾。古代法律对社会效益的注重在立法上的表现是集表彰与惩罚于一体,其中对犯罪的预防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旌表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上至朝廷大员下至草民百姓,只要道德卓著,堪称表率,王朝就会按制度给予表彰。表彰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由官府赐予匾额,修建居所,皇帝敕建牌坊,朝廷给予物质的奖励(如免除家庭的赋税、给付子孙的教育费用),等等。旌表制度使“修身”、“立德”成为全民的追求,也使中国人视荣誉重于生命,而对道德的追求成为社会预防犯罪的最好堤防,正可谓“法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其实,早在16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注意到了中国法律的这一特点,他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13](P217)
第三,官署职能规范完善。
如前文所言,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在“官”,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以行政官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纲目的。这种体系本身也体现了经与律、礼与法的和谐。成于春秋战国至汉时的《周礼》,传说是由孔子整理的。从表面上看,《周礼》是后人对西周历史的追记,其记载了西周“礼治”社会中的政权组织机构——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并叙述了六官的职掌。但实际上,《周礼》的编写者们更多的是通过历史来规划未来,阐述自己的理想,即实现官吏各司其职的礼治社会。这种规划与理想为中国古人所接受,《周礼》自汉代起就具有“经”的地位,此后王朝的制度设计无不以《周礼》为蓝本,而《周礼》所体现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的追求。直至隋唐,国家的行政机构终于如《唐六典》所记载的那样逐渐完备,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演变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地方的政府机构也随之逐渐演变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至明代,律的体例也随之变为名例为首,其后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在以官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行政机构的体系也就是法律的体系。
中国古代有关官吏组织机构的设置管理、官吏的选拔、官吏政绩的考核、官吏的升迁贬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十分严密,而执行这些法律的“吏治”机构也十分发达。有学者称“官僚法”完备发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此言不虚。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政书和会典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完备的官僚机构的设置。
第四,强调刑罚的负面作用,主张多种方式安民富国。
在“律”和“刑”的关系上,现代人对古代的误解颇深。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就是“律”,而律又以罪名刑名为核心,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就是刑,并以此又延伸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以刑为主”,甚至是“有刑无法”。其实,律只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前面所说的礼、官僚法在中国古代都是法,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是“以礼为主”的,而不是“以刑为主”。如果不带有偏见,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不强调刑的恐吓作用,更不以为刑罚万能。相反,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格外注意的是刑罚的负面作用和局限性,如对社会问题治标不治本、激化矛盾、容易形成暴政等等。因此,“恤刑”和“慎刑”而不是“以刑为主”,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真正特色。
古人对“刑”的认识也值得我们深思。在古人看来,刑罚毕竟是“以暴制暴”迫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使用刑罚的目的固然是惩罚犯罪,但更重要的却是保护善良并教育更多的人远离犯罪,弃恶而从善——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于“法中求仁”而非“法中求罪”。由于提倡慎刑,古代立法对于死刑尤为谨慎,死刑的判决和执行权自魏晋后基本上掌握在中央甚至皇帝的手中。即使只看律文,我们也完全可以自豪地认为中国古代的刑罚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是文明而先进的。在幅员辽阔的王朝统辖地区,“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延续性。每一个新王朝,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都会颁行王朝的新律作为“与民更始”的标志。自秦统一后,颁行及修订“律”的权力便归于中央,“律出一门”是为了避免统一的王朝统治下出现因“同罪异罚”而造成的社会不公。为了保障“律”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能高度统一,中国古代的“律疏”(律文解释)学格外发达。《唐律疏议》对于制定“律疏”的原因是这样写的:“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途睽误。”统一解释律文是为了实现官员对律的统一理解,是为了尽量避免因为官员素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律在执行中不统一的状况。
由于对刑罚的负面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思想家和政治家强调治国方式也应该是一个以教化为主、礼乐政刑各司其职的和谐体系,这与《乐记》中的“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四、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和谐理念及法律体系对和谐的体现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笔者惊讶地发现以往的和谐离我们是那么遥远,百余年来更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呐喊。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既成的事实,即在中国实现法理念的古今连接是一件十分困难却又必须进行的事情。
说其十分困难,是因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充满了坎坷。西方古代的法律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内部需求自然而然地得到更新,成为现实法律发展之源和动力,即古代的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解释中延续、更新、发展。正是这种深厚的法文化的积淀,成就了西方风靡世界的“法治”。如葡萄牙法律史学者叶士朋所言:“现今的法在其用语、概念、体制上均是一个漫长传统的遗留物,在此传统中,罗马法的文本占有中心地位。”[14](P66)而中国社会近代化,并非发自社会发展的内部需求,而是被西方殖民主义拖入近代历程的。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社会模式成为中国变革的预设目标,也成为判断古代文化的唯一取舍标准。当这个标准用于法律近代化变革中时,延绵了数千年的传统法律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自西周以来对历史上的法进行“沿波讨源”式的继承被中断了,中国古代法没有在近人的阐释中延续、发展、更新,而是在模仿西法中解体。在失去传统平台的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古今法理念连接的困境可想而知。但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百余年前的那场法律变革是失败的,因为那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的前辈所能做出的唯一的无奈但却明智的选择。
说其必须进行,是因为法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这就是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文化当然也包括法文化不可能也无需全面地移植,而传统的存在和影响也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近代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坎坷进程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拿来西方的法律制度时,传统法理念的影响并不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其虽然支离破碎但却顽强地影响着外来制度在本土的实施。正是因为缺少像西方近代化进程中那种对古代法的整理与阐释,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尚能明显地感到某些“西法”与“中土”的不服。这种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在法文化的培植中过于忽视了传统的因素,这种忽视无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法律的发展陷入困境;还因为现今的国际环境与百余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选择不再唯一且无奈,所以连接古今法理念就成为必须。这种连接是法律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是克服困境选择最佳的需要。当然,古今法理念的连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其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对古代法理念进行梳理与解释,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法理念的契合处,使传统法成为发展的动力而非包袱。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法律在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重视对西方法律的学习与吸收,忽视或回避了对本土法文化的阐述和继承。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5](P524)同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度里,没有对以往历史文化的阐释和继承,现代社会也就难以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法理念的古今连接是传统法律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正在于通过对古代法理念的阐述,将古人的法律智慧变为现代法律发展的基石与动力。
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谐理念演变的梳理,我们可以体会到,和谐在中国古人的理解中是“一统”与“多元”有机结合的体系,这个体系在一统与多元相协调时才能正常运转。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分析,在和谐的体系中,有权力的统一,也有权利的维护,这其中“度”的把握十分重要。自秦以后,对权力的强调是中国古代和谐体系中的主导,这种和谐必然建立在人们的“忍让”自律基础上,对权利难免有所损害。这是我们今天在提倡和谐理念时所必须注意的。然而,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和谐作为一种理想,是古今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古代先贤对和谐的主张与实践未必不可以为现代社会所借鉴。比如,先秦时期对立的儒法两家,儒家主张的是“以理服人”的王道式和谐,法家主张的是“以力服人”的霸道式和谐。与法家相比,儒家更偏重民意,即和谐体系中的“多元”;而法家更注重君权,即和谐体系中的“专一”。现代社会的和谐也离不开这两种因素,即在保护人们应有的多元化的权利基础上,达成社会的共识,形成整体的和谐。
就法律而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法律制度为和谐理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比如,在国家、民族间的交往中,反对以强凌弱,强调相互尊重,“入乡随俗”。据《唐六典·鸿胪寺》记载,唐代中央专设“典客署”掌管对外的交往,“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在社会及家族中,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反复强调“不敢侮鳏寡孤独”。[16]历代法律明确规定官府有收养无依无靠的孤老疾患者的义务。《大清律例·吏律·收养孤老》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和谐的理念在一些司法过程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元人张养浩在总结中国古代裁断民事纠纷的经验时说:“亲族相讼,宜徐而不易急,宜宽而不宜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第下其里中开论之,斯得体矣。”[17]而明代被郡人称为“明日来”的松江知府赵豫则将“宜徐不宜急”发挥到极致,因而深得郡人的爱戴。《明史·循吏传》记载:“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曰:‘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及讼者逾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及赵豫任满,郡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明日来”这种裁断方式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扬,不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裁断者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对人情世故有着切实的体察。如此的裁断避免了公堂上的冲突,运用得当,也不失为维护和谐的方法。其实,在和谐理念主导下,传统法律对罪犯的怜悯和对讼事的和缓处理,其意义不仅仅是稳定了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法文化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对人的尊严的维护。
产生于“乐”中的和谐,经过了西周礼治时代、汉以后礼法并用时代的阐释而不断更新,“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法律体系、纠纷的多种解决方式、体恤弱势群体等更是中国古代法律和谐理念的反映。这种和谐的理念给中国带来过安定,也带来过压抑;带来过整体的发展繁荣,也带来过局部、个体的牺牲;带来过生活安定的保障,也带来过权利的损害。但无论如何,和谐理念中所蕴含着的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导人向善,运用多种方法治理国家的宗旨和智慧,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生命力和借鉴的意义。
笔者还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即在近代法律的变革中,凡是有传统文化作为基础而更新的制度,经过古今的连接在实践中执行就比较顺利并能如人所愿,比如调解制度、综合治理等等;反之,与传统的隔膜较深而又缺乏本土文化阐释的制度,在发展中就难免有“南橘北枳”的现象并充满坎坷。愿和谐的理念在今人的阐释中寻找到传统法文化的支撑,在现实法律的发展中实现古今的连接。
[1] 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之一。
[2] 参见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襄公十一年。
[3]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4]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之一。
[6] 《左传·昭公二十年》。
[7]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之二。
[8] 《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9] 参见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第三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之一。
[11] 参见《通制条格·卷九·衣服》。
[12] 参见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1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4]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参见《尚书·周书》中的“诰”及《吕刑》。
[17] 张养浩:《为政忠告》。
(责任编辑 李 理)
On the Harmonious View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A Concurrently Discuss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Law Concept of Past and Present
MA Xiao-hong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Harmony which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pursued and defended was originally born of music, namely organic coordinated“diversity”and“sameness”.Because of this,Chinese traditional law assumed various forms and“Ceremony,Music,Penalty and Politics”took effect jointly.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harmony though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all times,is common ideal at different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So,harmonious view absolutely can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modern society after improvement and update.
Chinese traditional law;harmony;idea of law
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 本文为朱景文、张春生主持的“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之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