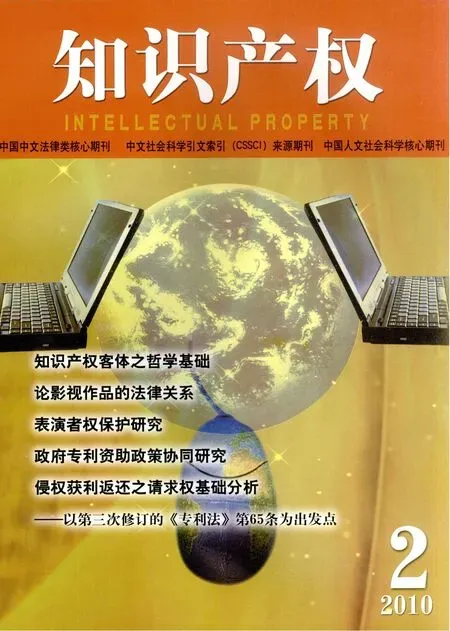论商标法的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
——从商标权的“行”与“禁”谈起
■ 罗晓霞
论商标法的多元价值与核心价值
——从商标权的“行”与“禁”谈起
■ 罗晓霞*
我国《商标法》从“行”与“禁”两方面对商标权进行了规定,体现了商标法是融多元价值于一身的法律制度。在商标法的诸价值中,保护商标权是其基础价值,保护消费者福祉是其延伸价值,促进有效竞争是其核心价值。为实现商标法的核心价值,需防止商标权保护目的化,并从强化商标标识功能和防止混淆入手,完善我国商标制度。
商标法 价值 竞争 防止混淆
我国《商标法》从“行”与“禁”两方面对商标权进行了规定:一方面,商标权人的权利限于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另一方面,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1参见《商标法》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行”与“禁”的规定体现了商标法是融多元价值于一身的法律制度。其一,商标法赋予了商标权人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的权利,同时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既保护了商标权人的利益,也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混淆的利益;其二,“行”的另一层含义是对商标权人在核准使用的商品和核准注册的商标之外使用商标的“禁”,“行”与“禁”从商标权人与竞争性经营者两方面对商标的使用进行了限制,旨在对抗商标权人与竞争性经营者利用商标进行的不正当竞争。换言之,商标法从“行”与“禁”两方面来界定商标权的范围,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有序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标法不是一部纯粹止步于私权保护的法律,而是担负了更多的使命。
一、商标法的价值解构
(一)保护商标权:商标法的基础价值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 IPS协议》)揭示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的范畴,同样具有私权属性。对商标权这一私权进行保护是商标法的基础价值,离开了对商标权的保护,商标法律制度无从建构。
商标权是为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说是为消费者利益而设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国家,最开始对商标的保护源于阻止销售欺诈性商品的仿冒之诉。仿冒行为危害十分明显,一方面,它使消费者无法通过商标选购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商品,而错误地购买了仿冒者质次价高的商品;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如不加制止,由此给仿冒者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会使其他竞争者争相仿效。因此,在制度上确认被仿冒者的商标权对于正本清源、制止仿冒、构建有序的竞争环境极为重要。英国在法律上承认商标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从 1883年的米林顿诉福克斯案开始的。2参见史际春主编:《香港知识产权法》,河南出版社 1997年出版,第 221页。正如美国《兰哈姆法》所期待的,商标权的赋予保护了商标所有人的投资,在商标所有人投入精力、时间和金钱向公众提供商品时,他付出的投资免于被盗版和欺骗等行为盗用。3S.Rep.No.1333,79th Cong..,2d Sess.at 3(1946).不论是从市场效率还是商业道德来说,赋予并保护商标权都是必要的。保护商标权,对仿冒者形成侵权前的威慑和侵权后的打击,使商标的标识功能得以持久强化,既而使商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其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这是商标制度构建的基本逻辑。
(二)保护消费者福祉:商标法的延伸价值
由于商标具有标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由此延伸出商标法的另一重价值,即保护消费者福祉的价值。消费者福祉在商标中体现为,商标能够使消费者买到合乎心意的商品:一是商标使消费者选择商家的自主权得到满足;二是商标使消费者购买质优商品的愿望得到满足。之所以将保护消费者福祉界定为商标法的延伸价值,理由在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并非商标法的主旨,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有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来承担,消费者作为仿冒行为的受害者,是不能直接根据商标法寻求救济的。4参见冯晓青:《论商标法与保护消费者利益》,载《中华商标》2007年第 3期。有学者从商标诉讼的角度指出,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在每一个商标侵权案件中都是一个“没有名义的”第三人。当商标权人起诉商标侵权者时,他至少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他通过控制不正当竞争保护了他自己的特殊利益;第二,他也保护了公众免于被欺骗或者混淆。5SidneyA.Diamond,Practice Approach to Patent,Trademark,7 Copyright,1981/1982.
在商标法中,消费者利益与商标权人利益具有一致性。由于商标是建立在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道桥梁,是指引消费者选择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源。法律通过保护商标权、阻止假冒者的搭便车行为,强化了商标的指示功能,同时也便利了消费者的选择。商标的区分功能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向消费者表明该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二是区分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向消费者表明该商品或服务质量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消费者对某一商标的认知和选择,是对该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围绕质量而形成的包括质量、营销模式、售后服务等综合要素在内的积极评价。防止消费者混淆是商标法保护商标权的意义所在,不断强化消费者对商标的认知也是经营者苦心经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当商标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认牌购物的效应,商标的价值才能得以凸显,商标权人超强的获利能力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消费者福祉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应成为衡量一国商标法对商标权的保护是否恰当的重要指标。根据经济学原理,产权的设定必须考虑公共资源的外部性问题。如果商标权的设定和保护不但未增加反而降低了消费者福祉,这种保护状况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商标制度的设计离不开对消费者利益的权衡,这是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与物权的明显区别。
(三)促进有效竞争:商标法的核心价值
促进有效竞争是商标法的核心价值,对商标法价值表述的这一命题建立在对商标功能的理解上。商标的功能分为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商标的自然功能即商标的识别功能,而社会功能包括广告宣传功能、保证商品质量的功能、促进销售的功能、承载商品声誉的功能等。识别商品来源是商标与生俱来的使命,为商标的主功能;其他诸项功能是在商标使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者说是经营者、消费者及其他相关主体期待商标所应具备的,为商标的附属功能。
商标的主功能——识别功能决定了商标法将以促进有效竞争为其核心价值。如上所述,商标权“行”与“禁”的规定在赋予商标权人权利的同时也对商标权人及其他竞争性经营者设置了限制。促进有效竞争的另一个方面是反不正当竞争,商标法的上述规定正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来实现促进竞争的目标的。商标法的设计基于以下利益预期:商标权人确信其通过商标标识商品的渠道是畅通的,消费者亦能确信其通过商标识别商品、防止混淆的渠道也是畅通的。以上预期利益的实现源于两方面的保障,一是消费者不因商标权人自身越权使用商标而混淆关于商品的信息,如经营者将注册驰名商标用于非核定使用商品,使消费者对该商品信息产生错误判断。二是消费者不因其他经营者对商标的使用而发生商品来源的混淆。由此可见,商标权的设计是围绕商标的标识功能而进行的,商标权的界限在于防止混淆,而防止混淆的核心利益在于促进有效竞争。
二、防止商标权保护目的化是实现商标法核心价值的必然要求
(一)商标法的价值序位:目的与手段之辨
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目前存在工具论和独占论两种思潮。工具论主张运用经济学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使财产安排的分配结果更加透明;主张知识产权应服务于道德上的价值。独占论主张所有权应高于共有利益,并且整个世界及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对所有权敞开的。在商标领域,接受这一观点的结果是,商标成为以自己的权利服务于其所有者的可交易的实体。在早期商标法中就得到确认的消费者的重要性及公共利益,在这里被悄悄漏掉了。6S.Rep.No.1333,79th Cong.,2d Sess.3(1946).对此,笔者更倾向于将知识产权理解为一种工具,主张知识产权保护是为实现更高的价值目标——谋求公共福祉而服务的,在商标法中这种公共福祉体现为市场效率的最优化。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商标法诸价值中,促进有效竞争为其核心价值,即最高价值,而保护商标权为其基础价值,两者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法律为促进有效竞争需赋予商标所有者以商标权,同时,为促进有效竞争也需限制商标所有者的商标权。实际上,商标法是在对商标权人、消费者、其他竞争性经营者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和平衡之后的一项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是市场效率的最优化。
(二)商标法核心价值实现的阻却因素:商标权保护的目的化
《TR IPS协议》对知识产权的私权界定无疑是准确的,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代表知识产权法应被工具化为保护私权的手段,恰恰相反,为实现知识产权制度增进公共福祉的终极目标,有必要对知识产权进行限制。知识产权增进公共福祉的制度价值在商标法中体现为促进有效竞争秩序的形成。为促进有效竞争秩序的形成,需要防止商标权保护的目的化,因为商标权保护目的化的必然结果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目前我国商标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商标权保护目的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
1.不以混淆之虞为要件的商标侵权认定。商标以标识商品,防止混淆为其基本功能,商标侵权的实质在于利用商标权人已经形成的良好声誉制造混淆,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并将侵权者的商品当作商标权人的商品加以购买,其目的是搭乘知名商品的便车获得不当利益。因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造成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应成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确定了商标侵权的认定标准,即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据此,商品类似、商标近似被奉为商标侵权的主要标准,而在结果上是否可能造成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却没有成为认定侵权时应予考虑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一标准的判例不在少数。一些案件尽管客观上并不具有造成混淆的可能性,但仍然被司法认定构成侵权。如“耐克”商标侵权案即为适例。7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1)深中法知产初字第 55号民事判决书。我国商标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这种不问混淆结果,只问商品类似、商标近似的侵权判定标准是商标权保护目的化表现之一。
2.不以商誉形成为要求的驰名商标认定。商标保护的历史表明,最早对商标提供保护的普通法国家通过判例以商标在公众中享有声誉为保护前提,而商标声誉则是通过商标的使用建立起来的。8王春燕:《商标保护法律框架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 4期。然而,我国商标法关于驰名商标的认定却未体现对商品声誉的要求。如 2009年 4月 2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驰名商标界定为“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商标”。与此相适应,《商标法》第十四条从五个方面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3)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4)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5)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这五个要素强调的也是商标的使用要达到在中国境内广为人知的程度,并未涉及商品声誉的问题。而对于使用的界定,《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解释又过于宽泛,根据该《条例》,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对于驰名商标“使用”的宽泛界定导致了一些只注重广告宣传不注重商品质量,甚至没有在中国市场流通,接受消费者检验的徒有其名的商品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笔者认为这一立法倾向的实质是强调了投资者的利益和商标的产权性,忽略了商标的社会功能。是商标权保护目的化表现之二。
3.不以商誉损害为依据的损害赔偿认定。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即有损害则有赔偿,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然而这一原则适用于商标侵权领域似乎存在例外。我国《商标法》充分考虑到无形财产损失举证难的特点,在第五十六条确定了计算损害赔偿额的三种标准:一是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二是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三是法定赔偿标准。以上任一计赔标准的适用均应建立在有无形财产损害发生的基础上。商标侵权行为的实质是对他人商誉的损害。然而,在近年出现的一些商标侵权案件中,无商誉损害却有“侵权所得”赔偿的判决却时有发生。如在上述“耐克”商标侵权案中,西班牙 C IDESPORT公司的“耐克”鞋直接销往西班牙市场,未在中国市场销售,其行为对原告商誉并未造成任何实质影响,而在选择赔偿标准时,法院采用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利益作为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额。在“美得丽”商标侵权案中也存在类似情况。9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通中民三初字第 0004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苏民三终字第 0130号民事判决书。在原告广州保赐利化工有限公司注册“美得丽”商标之前,被告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已经在先使用“美得丽”商标,且在原告提起侵权诉讼时,被告已持续多年使用该商标且形成显著商誉,市场只知廊坊立邦涂料有限公司的“美得丽”而不知广州保赐利化工有限公司的“美得丽”,换言之,原告对其抢注并使用在后的商标并未形成属于自己的商誉,故被告使用在先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的任何损害。尽管如此,一审法院仍然认定被告侵权成立,并以其侵权所得为依据确定了高额赔偿。笔者认为,在损害赔偿计算中不问商誉损害结果的侵权所得认定标准无视了商标识别商品、防止混淆的基本功能。是商标权保护目的化表现之三。
三、强化商标标识功能,防止混淆是实现商标法核心价值的题中之义
商标权是在反假冒之诉中产生的权利,负有反不正当竞争的先天使命,其制度构建和发展应围绕促进有效竞争这一核心价值进行。实现商标法促进有效竞争的核心价值需从防止混淆开始,并以防止混淆为制度归宿。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在商标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应立足于强调商标的标识功能,防止混淆进行如下制度完善:
(一)构建以混淆之虞为要件的侵权认定标准
在商标侵权中,侵权行为的实质是利用商标权人的商誉推销自己的商品,其手段是在自己的商品上使用与商标权人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消费者误认为其商品是由商标权人生产或至少与商标权人存在某种联系。因此,我国在商标侵权认定上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将混淆之虞作为商标侵权认定的主要标准。对仅具商品类似、商标近似之表象,不具消费者混淆之实质的商标纠纷应认定不构成侵权为宜,否则,不结合商标使用的实际情况对商标进行片面保护正如学者所云,将使商标权保护沦落为一种符号崇拜,迷失了立法的本义。10李琛:《商标权救济与符号圈地》,载《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 1期。
以混淆之虞作为侵权认定的主要标准,在商标注而不用的情况下,他人使用该商标是否构成侵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法院态度不一。在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诉河北汇特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及注册商标侵权案中,该案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在注册了“小肥洋”商标后从未实际使用过,不存在消费者混淆的问题,故河北汇特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使用小肥羊的行为不构成对“小肥洋”注册商标的侵害。11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冀民三终字第 4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审理中,法院并未机械套用《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简单以商品类似,商标近似的标准来认定侵权,而是采用了混淆理论,笔者认为,这一求真务实的态度殊值赞赏。
(二)商标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在驰名商标认定中不可偏废
关于商品声誉对于驰名商标认定的影响,学界存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品声誉在驰名商标认定中不可或缺;另一种观点认为,商品声誉在驰名商标认定中可有可无,商标可以因宣传而驰名。对此,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驰名商标不仅具有标识商标来源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表彰商品质量的功能。驰名商标之所以驰名,是因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以其较高的信价比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得到了消费者的积极评价,使消费者愿意花比一般商品更高的价格去购买驰名商标的商品。一个商标光有好的质量,消费者知之甚少,该商标不可能成为联系消费者与商家的强劲纽带;一个商标光有声势夺人的宣传,在质量上缺乏好的口碑,宣传的结果可能不是使商标驰名,而是令商标臭名。因此,知名度和美誉度应成为认定驰名商标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
商标的知名度可凭藉企业的广告宣传获得,而商标的美誉度则需通过商标附随于商品之上的使用不断积累而成。因此,商标的使用是商品声誉产生的源泉。鉴于上述理由,笔者建议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明确驰名商标的定义,可借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03年发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将驰名商标界定为“中国境内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同时在驰名商标认定应考虑的因素中,将商标附着于商品上实际使用的时间作为认定因素之一,此外还应将商品的质量状况作为一个评价指标。
(三)以商誉损害作为商标侵权的赔偿计算依据
商标的价值体现于商誉。已经申请注册的商标相当于一个“器皿”,可以在未来的使用中装载商誉。12小野昌延著:《商标法概说》第十一章第六节,1999年。一个没有装载商誉的商标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因此,在商标侵权中应树立一种认识,即商标侵权是对商标权人商誉的侵害而不是对商标本身的侵害。在损害赔偿上,有商誉损害则应赔偿,无商誉损害则无赔偿。如在“中农”商标侵权案中,法院对于原告损害的认定有较强的参考意义。13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4)海民初字第 821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尽管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销的化肥上使用与原告注册的“中农及图”商标相近似的“中农及图”商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但在赔偿计算上,法院认为,由于原告连续三年没有使用过其注册商标,说明被告侵权行为未对原告造成实际经营上的损失,故对原告经济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