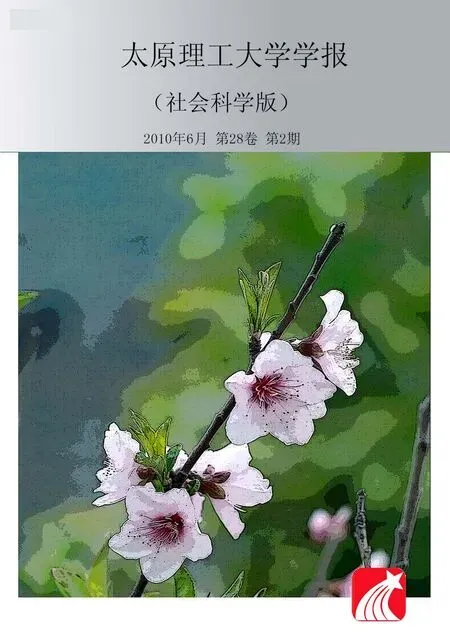迈克·费瑟斯通与赛博空间的后现代性
张飞龙,蒋 挺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8)
迈克·费瑟斯通有关赛博空间的论点彻底颠覆了哈贝马斯的空间概念。哈贝马斯讨论的重点在于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现实空间,比如咖啡馆、酒吧等公共空间。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空间首先可以理解成一个由私人空间集合而成的空间;但他们随即要求这一受社会上层的公权机关控制的公共空间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但是,他的理论似乎有一个前提:“面对面的交流” 是行为交往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判断对方的诚信度”[2],即判断交流的对象是否展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
一、赛博空间的行为交往
赛博空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一空间的存在形式,它是完全虚拟的空间和开放的空间。酒吧或者咖啡馆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是参与对话的群体则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然而赛博空间,比如BBS、QQ、BLOG等,连一丁点儿的封闭性都不存在,游客或者版主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随意涂鸦文字,还可以任意编辑网页、添加内容,所以,赛博空间的交往本身就是对传统交往行为的发展。就目前赛博空间的发展来讲,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恐怕就是人们交往方式的变化。
首先,交往阈限改变。当我们浏览BBS、QQ、MS等公共空间的时候会发现绝大多数发言者是以游客的身份匿名发言的,尽管大多数网游者有一个诸如“虹”、“人在江湖”等等的代号,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只凭借语言来确定他们的身份,更遑论他们的年龄和性别、衣着等更加具体的细节,所以费瑟斯通认为,赛博空间的交往行为更具欺骗性,这是交往阈限改变的结果。[2]当然这不是说,咖啡馆和酒吧等公共空间内的交往行为就比赛博空间内的更加真实可靠,但是至少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它可以获得更多的参考信息来进行综合分析。
其次,诚信度的测评方式改变。交往阈限的改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交往主体的个人诚信度如何测定的问题。诚信是传统公共空间人际交往所必需的个人品质,也是一个基本的伦理要求。在传统公共空间内,个人的诚信是可以根据多种信息来判定的,比如眼神、说话的流利程度、身体语言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展示性自我的重要方面。[2]当然,展示性自我同样具有欺骗性,现实中骗子的种种表现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个人的诚信往往是靠多种交往手段和长期在场交流综合展示给对方的,而赛博空间内的个人诚信问题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它主要依靠技术手段来测评,比如IP地址是否一致,登录信息是否前后一致,等等。总之,个人的诚信度是由位于特定位置的特定的计算机决定的,这就大大区别于传统公共空间内的个人诚信度的测评方法。相对于传统公共空间,赛博空间内展示性自我都普遍具有欺骗性,它经常为人提供虚假信息。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说,这种欺骗是与缺乏严肃性的狂欢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文明社会里对文明人的欺骗。[2]
再次,公民拥有了多重身份。赛博空间内网民是以多重身份来展示自我的。现代网络技术鼓励公民多重身份的实现,一个网民同一时间内可以以多个身份同时出现在赛博空间内。比如,在聊天室多方谈话时,与A可以以医生的身份谈话,与B可以用专家的身份谈话……迄今为止,这种多重身份是赛博空间特有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实的公共空间内,尽管一个人可能有多种身份,可以扮演多重角色,但是很难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展示自己所有的身份。在酒吧,你就是一个分享别人快乐和痛苦的临时朋友(抑或终生不渝的挚友);在教堂,你只能是一位需要忏悔的信徒或者其他某一种身份,如此而已。这是因为传统公共空间里,现实中个人的形象和身体展示了一个人的全部信息,比如健康状况、职业、民族、国籍、性别等等。但是赛博空间内,网民总是以拟像化的木偶身体出现,个人的当前状况完全被隐匿。当前他可能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艾滋病患者,而出现在赛博空间内的却是一个活泼的男孩;现实中他可能是一位只懂得一点上网知识的白痴,出现在赛博空间内的却是一位侃侃而谈的文化专家……这里,网络技术建构了多重公民身份,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公民 “身份”的伸缩性和多种可能性也受到极大程度地考验。[2]
这些都是技术时代带来的重大变化。费瑟斯通认为,赛博空间的行为交往所体现的正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它彻底颠覆了传统学术的基础——生产高于消费,城市优于乡村,阳性优于阴性,权威优于大众,真实优于欲望,言语优于影像,印刷文本优于音像等等”[2]。诚然,从根本上说,赛博空间是一个消费的空间,是一个集合了不同影像风格和语言风格的空间。不论一般网民还是版主,都在追逐极端的个人化风格,更有甚者将个人私密的照片拼贴在网页上,以展示极端自我的一面。
这就涉及到赛博空间的交往行为合理性的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合理的交往行为必须接受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道德或者文化规范的批判和检验,以确定其合理性的真实性。尽管行为主体诉诸价值判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相同的文化规范足可以确定其合理与否。[3]按照这种观点推论,赛博空间的大多数行为,比如电子信件交流、skype电话、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等,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少数的交往行为,如上传私密照片、暴露身体等行为是不具有合理性的。然而,越来越多的网络交往行为却很难用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标准来衡量。最具典型的例子是网民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的方式。2008年,中国赛博空间内发生了多起人肉搜索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作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王菲赔偿案”。起初,这只是一起个人家庭情感问题,姜某死前的日记被姐姐公布在网上,大家一起跟贴,这起事件最后直接演化成了网络暴力。这个事件正符合了谷歌的一贯主张——“在最短时间内揭露某某门背后的真相,为某三某七找到大众认可的道德定位”[4]。
二、赛博空间中的意识形态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会直接联想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赛博空间内网民似乎可以比传统公共空间内的人或者其他人群获得更多的自由。谈到意识形态,我们就无法避免“自由、民主”这两个概念。自由这个字眼,在英文里是“free”,它基本包含了“免费”和“自由”两个意思。在消费文化语境下,考察赛博空间的意识形态问题,离不开“free”这个字眼,这是因为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自由的来源有两个:市场和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赛博空间的自由逐渐从“政府赋予”而转向了“市场供应”。但是有些网络资源仍然是受控的,网民必须付费或者登陆成为会员并免费为该团体义务服务某些内容后才能享受其中某些资源,这个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经济上的资源控制状态。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一个人使用某种资源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或者所需许可的授予是中立的,那么,这种资源就是自由的。以此来理解,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不是应当由市场还是政府来控制资源的问题,而是资源是否应当保持自由的问题”[5]。
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从资源的自由和人的自由两个方面来理解赛博空间的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感到迷惑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自由”,那就是网络资源是否应该不受任何控制地自由发展。这个问题的倡导者,不论是A&MT的设计师还是劳伦斯·莱斯格教授,都还没有注意到赛博空间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裸体聊天、淫秽视频、裸体照片等对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毒害。
就赛博空间内人的自由问题而论,费瑟斯通的态度就显得乐观多了。他认为,“人们能够逃避掉现实中紧密的相互依赖和权力平衡,也可以逃避那些重要的他者(他们了解我们的思想),从而觉得言论自由,说自己敢说的。那些曾经压制没有权力的人的现实暴力和符号暴力很难再发挥作用了”[2]。这和雷音歌尔德(Rheingold)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在虚拟社区里公民身份会更加趋于民主。[6]对于他们二人来说,随着现实空间的丧失,虚拟空间反而得以重构,从而履行着现实空间的功能,人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挚友、自由地发表言论,这其实就是公民身份的再构[6];而且按照他们的逻辑,虚拟空间只能使得人们享受的民主和自由越来越多。但是这种考察比较容易陷入总体性论断的误区,仅仅因为虽然赛博空间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空间,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在多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下重构观念的场所,这些意识形态既包括强势的,也包括弱势的;既包括官方的,也包括社会底层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交互影响的结果或许会是自由的增殖;但是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便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会变得更加强势。韦伯就曾经这样认为,自由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在经济上采用“功利主义”;在政治上采用民选制,让国家机器屈从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意志。这样一来,统治越多的地方,自由也就越来越多。[3]这种研究范式是从结论到结论的研究方法,它过多地强调了赛博空间的一般属性,却忽视了赛博空间的特殊性。因此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设想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的设想,理由如下。
首先,工具理性设计下的赛博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个性可以随意张扬的场所。费瑟斯通之所以这么乐观,是因为他认为工具理性不能够控制赛博空间,因此赛博空间是一个随意张扬个性的地方。诚然,在赛博空间个体可以享受比现实空间更大的自由度。网民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自我发展人际关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法律、道德等暴力范畴的价值理性对自我的束缚;现实中的种种限制诸如道德、使命感、责任感等等都可以暂时得到摆脱。但事实上,赛博空间本身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张扬的一种产物。最初,万维网和因特网的设计者并不是为了建立虚拟社区和发展民主与自由,而是为了军事和医疗等管理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加强控制,既包括管理层面的控制,也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当然,在某一个特定的赛博空间里,各种意识形态总是交杂在一起的,但是从这些意识形态交汇的赛博空间的内容以及交往行为来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价值理性,而非理性的网络交往行为则较为稀少。所以,个性的张扬基本上是一个神话。
其次,赛博空间内的控制并不是减弱了,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强化了。赛博空间内代码无处不在,它主要执行过滤功能,对不符合要求的语言、图片和视频进行过滤和屏蔽,这将严重地影响到言论自由问题。桑斯坦就曾指出,一个允许言论自由的完善机制必须符合两个要件:第一,任何信息对人们都应该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该被筛选,未经计划的、无法预期的信息接触对于民主至关重要……民主之所以为民主,就是人们常常无意间在一些没有筛选过的题材里找到观点和话题;第二,大部分公民应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如果无法分享彼此的经验,一个异质的社会将很难处理社会问题,人和人之间也不容易了解。共同经验,特别是由媒体所塑造的共同经验,提供了某种社会粘性。一个消除这种共同经验的传播体制将带来一连串的问题,也会带来社会分裂。在网络上人们谈论的主题往往更加局限,越来越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而这样的情形比分裂还糟糕。消费者们各自在封闭的情况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7]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中得出一个带有悖论色彩的结论:自由表达得越多,社会控制的也就越多;而且社会控制都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着的。
这时,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费瑟斯通的自由观了。在赛博空间,社会上层和下层的权力平衡固然比较容易打破[8],但是这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尽管按照米尔的自由观,自由属于伦理的范畴,它体现在社会关系之中,但是经过强势社会阶层“过滤”之后而得到的自由,它就是另外一种“自由”了。所以说,赛博空间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言说讲坛,另一方面又限制着人们的自我表达。我们公认理想化的言语情境是理解任何说出的话的必要条件,然而一旦 “言说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达到理想化言语情境的标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不能与他人交往,而是意味着社会压迫,最终便是阶级斗争”[9]。
三、结 论
赛博空间属于新型的第三交往空间,其行为交往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第三空间内主体在交往过程中诉诸了更多的感性,但又受到技术、强势意识形态的控制。如果说传统空间内强势意识形态是以显性的方式影响着行为交往的方式的话,赛博空间内行为交往则受到强势意识形态的隐形控制,但是控制的程度则更加严格。因此,用哈贝马斯的行为交往理论阐释这种交往行为,似乎已经不可能,建构新的行为交往理论,已成必然。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7.
[2] 费瑟斯通.公民与赛博空间[J].海奇豪格评论,1999,(Fall):65,65-67,66,67,67-68.
[3] 哈贝马斯.行为交往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1-22,344.
[4] Google人肉搜索[EB/OL].http://www.google.cn/intl/zh-CN/renrou/,2010-01-12.
[5] 劳伦斯·莱斯格.思想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3.
[6] 霍华德·雷音格尔.虚拟社区:电子时代之回归家园[M].马萨诸塞:安迪勋·卫斯理出版社,1993.75,65.
[7]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00.
[8]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6-70.
[9]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