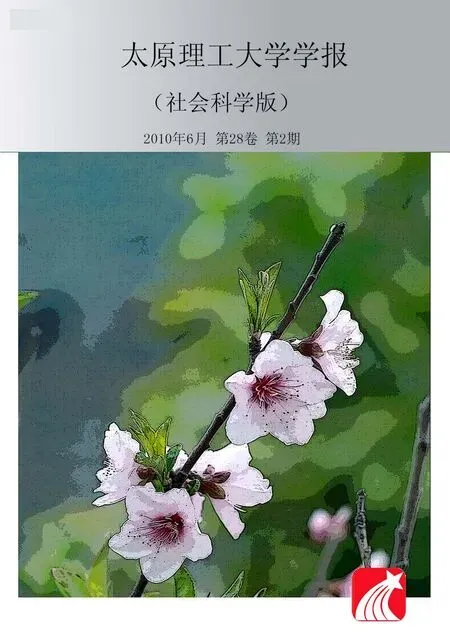失落与救赎
——论石评梅小说基督教思想的驳杂性
邱诗越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早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有一批开明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之道,到了“五四”时期,在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作为与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基督教思想与文化也输入了中国,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本身就包括了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从太平天国时起,《圣经》中文译本就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圣经》既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周作人在他的《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就曾指出:“《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从这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圣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中也常常采用基督教观念和话语,并由此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意蕴与内容,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与题材。
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人,一位活跃在“五四”时期且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她的创作几乎涉及各种文学体裁,其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她的作品量因生命的短暂而显得不够丰厚,但作为一位独具风格魅力的作家,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依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为此,我们不能也不该遗忘。
石评梅与同期的冰心、庐隐等作家一样,作品中呈现出浓郁的基督教色彩。石评梅本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她接受的主要是观念化的基督,即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她的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直接引用的《圣经》原文,更看不到多少宗教教义,但她的作品蕴含着基督教的内涵和精神。细读石评梅的小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她被耶稣的伟大人格所感化,折服于基督教文化的博爱宽恕、牺牲拯救和昂扬奋进之精神,将其视为拯救社会和个人精神寄托的一种途径;但当她面临现实的艰辛与困苦时,又会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在信与不信间游移彷徨。
一、失落——对“上帝”的绝望
石评梅对宗教的信仰与当时的许多作家有相同之处,更多的是汲取基督教的世俗意义与现实价值。宗教信仰对石评梅来说是一种生活需求,亦是一种精神追求,这是一种与鲁迅不同的精神追求。石评梅生活在一个乱离的时代,她在现实中看到的是眼泪、仇恨、欺骗、罪恶、战争……到处充塞着困顿和不平,这一切在她看来是那么的不宁静、不和谐,她为当时的现实所束缚,希望上帝拯救苦难中的芸芸众生,希求追寻新的精神力量,藉以凝聚民族灵魂,以便促进民族的新生。因此宗教对于石评梅来说既是一种形而下的需要,又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不同于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形而上追求。
石评梅对当时特定时代的感受、体验与基督教精神的内涵是相融相通的。在仔细研读石评梅的小说后,会发现在她的作品里频繁地出现祈祷、祷告、忏悔、上帝等基督教意象,并且她的小说《祷告》和《忏悔》就是直接以基督教话语为题目。[注]本文所引作品均出自柯灵主编,石评梅著:《石评梅小说:只有梅花知此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从她的代表作《董二嫂》、《弃妇》、《一夜》等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这些小说表达了她对旧家庭或旧社会妇女悲剧命运的同情,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关爱。
“上帝”在石评梅的笔下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上帝”曾是基督教所崇信的至善万能的神,“他”能够操控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但她作品中的“上帝”一词已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本意,在文本里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文学意象。在石评梅看来,“上帝”是“人身以外”的一个支点与一份精神安慰,并作为一种爱和献身的人格被推崇。马林诺夫斯基在《巫术、科学和宗教》一文中谈到宗教的情感功能时也曾说:“人类在现实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即使作出了极大地努力也仍然战胜不了的困难,在这种时候,宗教就为这些失败的人提供一种信心和安抚,消除人们由于遭遇不可避免地挫折而产生的焦虑,”[1](p228)但面对在场的艰难与迷茫,上帝并未给人们支起一份希望与勇气。石评梅看到的是人们在灵魂深处的挣扎和痛苦,如《余辉》里的苏斐内心有着一份对现实认识的清醒与觉悟,曾经胸怀大志“投笔从戎”,如今面对学生的天真欢快也透露出她对未来的期待,而身陷“只是无穷罪恶黑暗的渊薮”的生存困境却让她感到了希望的茫然;《归来》里的子凌亦是如此,曾因拯救大众而声名大震,内心却依旧因没有找到依凭而感到无比的孤独和痛苦。这些小说袒露了人物在人生追求过程中的苦闷和彷徨。
面对人生的迷惘与现实的困窘,石评梅希望在信仰上寻找到一种情感寄托与精神慰藉,但吴天放的情感欺骗、高君宇的早逝离去让她倍感失落与辛酸,她曾经的希望在此岸世界里破灭了,名誉、幸福、爱情、理想等都化为了泡影,于是将自己的灵魂、精神寄托于“上帝”。然而,孜孜以求的理想无法实现,追求而无所得,作家常常见到现实残酷与冷漠的一幕幕:贫穷、饥饿、离乱、死亡……巴特在《受难》中指出:“耶稣的生活不是胜利,而是屈辱,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不是欢乐,而是苦难。”[2](p258)外在的社会现实与经历体验反映在了石评梅的创作中,小说人物也有如基督耶稣一样的受难者形象。比照石评梅的小说《流浪的歌者》,流浪歌手与耶稣在精神上不谋而合,也有一腔报国热情和宏图大略却不为世人所了解,后因被昔日的友人出卖而入狱,这与当年耶稣因身边的门徒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相似之处;流浪歌手最终未唤醒被拯救者而落陌的走向死亡,与耶稣救世而未被世人理解而死去的命运是一样的。石评梅小说里的许多人物陷进罪恶、仇恨、虚伪的深渊里,最后依旧未能蒙恩而获救,虽在期盼中,但“信仰”与“爱”变成了扁平的符号,上帝的神性在人物的心中早已失重了。
二、救赎——对“上帝”的期待
石评梅关注现实、感时忧民,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她在作品里反映民生疾苦,揭露黑暗现实,并对民族前途、未来命运作了理性的思考。石评梅在她的小说里鼓舞人们积极救世、昂扬奋起,凸显了基督耶稣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等精神。石评梅的宗教情怀和宗教精神是入世的、现实的,而沈从文虽然也信仰宗教,但与石评梅不同的是,他陷入了宗教的虚无和迷茫。
宗教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给人以精神寄托与安慰。面对此在的困厄与迷茫,作家深感疲惫困顿,希冀得到“上帝”的护佑,祈求“上帝”能拯救现实。小说《祷告——婉婉的日记》里的婉婉是位精心照料病人的护士,自幼在福婴堂长大,对生活倍感孤寂,困惑于自己的身世,平时常常读《圣经》,做祷告,诵读《圣经》是为了帮助他人解脱和超越现实的痛苦与孤独。宗教仪式上的祈祷,往往能给人带来慰藉,因为“人们在祈祷中最常祈求物质或精神的惠赐,如本人的健康或康复、他人的痊愈或长寿,获得某些物品,实现某种预期结果等。”[3](p63)宗教信仰既给他人也给自己以精神慰安,使处在苦闷、不幸中的人得到精神寄托与救助,得到“爱”,一如宗教专家詹姆士·里德在《基督的人生观》里所说的,“……只有通过上帝的爱,才能把我们从冷酷中拯救出来。”[4](p54)弗兰克也曾在《爱的宗教》里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基督教的宗旨,即宗教的宗旨,就是爱的宗旨”,[2](p366)宗教的“爱”往往能给人以力量与勇气。
耶稣曾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圣经·马太福音》)。耶稣牺牲自己意在拯救世人,具有执著于苦难而殉道的精神。石评梅在她的小说里就塑造了这样的基督徒形象,如《红鬃马》里的郝梦雄、《匹马嘶风录》里的何雪樵、《归来》里的子凌等都具有献身救世精神。基督教认为,“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是意味着我们聚集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力量,能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4](p70)宗教能唤醒人不断的进取向上,《白云庵》里的蕙就表示:“要另找一个新生命、新生活来做我以后的事业。因之,我想替沉没浸淹在苦海中的民众,出一锄一犁的小气力,做点能拯救他们的工作……”《红鬃马》里的郝梦雄走出一己的痛苦与困惑,献身于革命事业,他的遗嘱就是叫妻子好好教养儿子,对儿子的期待,也即是他对明天的坚信,对未来的期盼。
石评梅小说里另一个高频意象就是“忏悔”。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忏悔时,祈求在耶稣宽恕中得到慰藉,“宽恕之爱是一种对待他人的精神,其中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4](p174)从而使人的精神得以洗涤,唤醒灵魂,“这种宽恕将我们的自我尊严归还给我们,或者说,能够使我们保持我们做人的信心。”[4](p57)石评梅小说《忏悔》里人物的忏悔意识,正表现在以忏悔唤起人的良知,解脱良心的痛苦,并获得一种灵魂的净化与超脱,亦即精神人格的觉醒。作品里的素兰为了表哥翔所表现出的牺牲自我、舍己为人、包容忍耐的精神,就恰如保罗所说的,“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这里体现的就是一种基督徒的忍让和宽容,“忏悔”使人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救赎。
三、疑与信——宗教信仰的徘徊
石评梅对宗教的信仰是驳杂的,有时相信神性存在的巨大力量,但有时又会怀疑其存在价值,因此她对基督教的体验和感受也是多义的,既对“上帝”充满了希望与信心,又对“上帝”感到悲观与绝望,倍感消极颓唐。这样使她的基督教信仰有时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笔下的基督教相似,带有失望悲观的情绪,有时又与冰心、巴金等的信仰相同,对“上帝”充满信心和希望。
因现实世界的污浊、颓然让石评梅对“上帝”的万能与崇高产生了动摇,此时她对基督的信仰与李金发有相似之处,质疑“上帝”的存在及其神性的力量。其实,石评梅对“上帝”的质疑和否定,是源于她对现实关怀的执著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这种信仰的怀疑批判精神,是着眼于此在世界的,但也有对彼岸世界的期待。如小说《蕙娟的一封信》里的蕙娟因事业失败,深感自己无法掌控命运之舵,因而对人生前途感到心灰意冷,打算离开亲朋好友去远方漂泊。这里个人的生存与体验介入了对基督的理解,呈现了作家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理性思考,这种精神痛苦正凸显了寻找的艰辛与彷徨。
宗教的意义在于为人类的灵魂提供一方净土与精神支撑。梁启超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里就认为:“只有通过精神的新生才能获得民族的生存与强大,而宗教对这种精神新生是必不可少的,宗教能促进民族的凝聚力;宗教给人们生活带来希望;把人们从世俗的利害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把精力集中在高尚的努力上;宗教引起人们道德上的顾虑和约束;宗教增强人生存的勇气和勇敢精神。”[5](p44-50)“进入现代世俗社会,宗教作为一种崇拜,一种力量,一种使人至死不渝的忠诚信仰不存在了,但作为一种情感,宗教仍然存在,可能还会继续存在。”[3](p402-403)在石评梅看来,宗教信仰有时能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因此,在《林楠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楠嫂坚毅的生活意志,她对自己的处境与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了信念就不再惧怕黑暗与不幸,对未来与此在就有了憧憬与希冀。这就如同鲁迅先生看到的宗教力量:“他(鲁迅)从《圣经》里看到了一个弱小、受难民族的命运和信仰,有了这样的‘信仰’,一个民族就会有新生的力量,……”[6](p29)
综上所述,基督教文化和宗教思想对石评梅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比较驳杂的,有时她相信“上帝”的存在,觉得宗教信仰能给人以精神启示与慰藉;但当她身处现实的困境与人生的迷惘时,又感到了神祗的远离与无助,进而对“上帝”的存在深感疑惑。总之,石评梅的宗教信仰在信奉与疑惑间徘徊,这是她的作品价值、特色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她作品里的宗教思想具有了复杂性与多义性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周 蔚,徐克谦,译著.人类文化启示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 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M].杨德友,董 友,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3] 梁 工,主编.基督教文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4] [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M].蒋 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第十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6.
[6]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