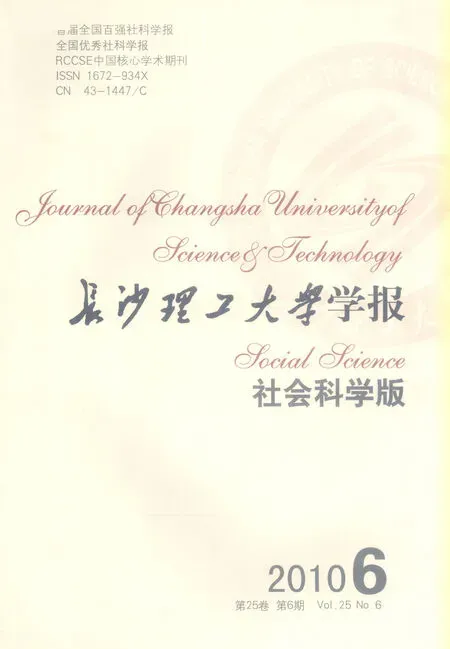论传统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理性
綦保国
(仙桃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仙桃 433000)
论传统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理性
綦保国
(仙桃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仙桃 433000)
孝亲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法制之一。它是特定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其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基础。从经济功能上看,孝亲法律制度主要是激励了父母的生育欲望,从而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繁衍和增长创造了制度性保障。
孝亲;法制;经济分析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孝亲。“孝”虽起源于宗教和道德的约束,但最终却转化为我国古代法制的重要部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出于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孝亲制度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甚至被认为是家庭与国家专制的罪恶之源。有关孝亲及孝道的研究和著述甚丰,牵涉到伦理、宗教、教育、法律等各个领域。本文尝试以经济理性的视角,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以期探析并理解中国古代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属性及其历史意义。
一、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内核
在现代社会,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家庭为什么能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保持下来?为什么人们要结婚组织家庭?著名的法律经济分析大师波斯纳认为:“它必然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1]是规模经济(资源共享)?是专业化分工的收益(男女的家庭劳动分工)?这些或许是家庭制度的经济理由,但更重要的经济学理由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商品——孩子”,这是现代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最主要收益。当然,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家庭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子女”的生产组织,还是农业生产组织——农、副产品的生产工厂。
子女作为父母组建家庭的主要产品,也是家庭的最主要收益,是以父母的大量投入为前提的。父母要想把子女培育成为一件合格的产成品,父母必须投入的资源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生育的痛苦、失去的美色、保守贞节所失去的快乐、当然还有食品、衣服、药品以及教育资源,最重要的还有时间和劳苦等等。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述的一切成本或者投入都是需要收益作保障的。“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依此定义,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探究以下假设的含义: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我们将称他为‘自利的’”,[1]这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作者波斯纳先生一开篇就提出的基本概念。根据这一基本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人类生育子女这一“经济理性”行为:其一,子女作为一种社会收益要大于生育他(或她)所投入的社会资源之成本,青出于蓝必要胜于蓝,这样才有投资价值。其二、父母生育子女的收益要大于父母生育子女的投入,这样父母才有投资意愿。而且,显而易见,“其二”是“其一”的基础。也就是说,父母不会作出经济上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也不应该在子女身上浪费人类有限的资源。因此,古代斯巴达人将不健康的孩子抛入深渊,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直截了当地指出:“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能将子女看作是一种最终“产品”,他们不是父母投资行为的终极“目的”。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认识,孩子可在以下情况下为父母提供收益:“(1)作为性行为的无意识的副产品;(2)作为一种产生收入的投资;(3)作为向父母提供其他服务的一种来源;(4)出于一种保存种姓或使父母的遗传特性、姓名或死后名声永远存在的一种天性或者愿望”。[1]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上述的各种收益?或者说如何保障上述收益的实现?除第(1)点外,(1)从来就不是重要的,中国古代早就知道了中药堕胎技术,而且人们可以选择生而不育。其它各方面收益都需要子女行为的配合。没有子女的特定义务,父母的收益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人们不得不设置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以确立父母权和子职,从而保障父母生育子女这一投资行为收益的实现。
在笔者看来,孝亲法律制度的确立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性选择。就象人类走进农业社会,就不得不确立财产私有制度。假设没有财产法律制度,农民开垦荒地、播种、施肥、除草,但结果却是别人收了庄稼,那么人们只得放弃种地,退回到渔牧生活中去。正如柳诒徵先生在论及家族及私有制度之起源所说的:“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后世以私为厶,而稼字从禾,家声;穑字从禾,啬声。可见农业之人,各私其家,务为吝啬,胜于他业矣。”[3]此言甚是。然父母之于子女,比之农民之于庄稼,其耕种、培育之艰辛而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之于庄稼有财产权法律制度,父母之于子女岂能没有孝亲法律制度。事实上,在古代社会,父母之于子女的父母权十分类似于财产权。
二、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合理性标准
孝亲法律制度有其存在的经济合理内核,然而子女的孝亲义务有没有止境?孝亲义务存不存在一个经济学的理性标准?如果孝亲义务是没有边界的,对父母来说,由于孝亲收益存在人为的超额利润,其结果必然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的结果正如韩非子所言:“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 ,事力劳而供养薄。”[2]对于子女来说,必然要求不计成本地“至孝”或者“愚孝”,在《二十四孝》中存在一些如为母埋儿、卧冰求鲤等令人震憾的“至孝”行为,甚至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非理性伦理要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过度投资还是不计成本的“愚孝”都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
过度的孝亲要求的确是一种专制,那么孝与愚孝的经济学标准是什么呢?时下有一种观点:老年人对社会来说,已经没有经济价值,对其任何的资源投入都是一种浪费。这种议论显然是谎谬的:其一,人是目的,而不应仅仅看作是手段。其二,从经济学上来说,“沉淀”成本的确是归于零,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的研究总是事前研究而非事后研究。因此,对孝亲制度的研究不是将重点放在子女成人之后,而是在父母子女关系还没有产生之前。如果允许一个契约当事人在产生不良后果时修改契约条款,那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契约。
在当今社会,我们的法院在审理父母子女的孝亲纠纷时,常常要求子女给予父母最低生活标准的粮食或金钱,也就是父母生存下来的最低要求的必需品。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指出了这种孝亲观念的浅薄:“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从经济学上说,我们可以假定父母子女在事前自愿签订一份市场契约。契约规定的父母权高于其投入的成本,而低于子女从父母处得到的收益。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份契约,不仅仅因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双边垄断关系,而且事前子女还不存在,父母就开始投资了。至于子女从父母处得到的收益,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了生命,生命是无价的,理性的人都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来保存自己的生命,那么是不是只要父母不要子女的命,父母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呢?显然,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市场,子女完全可以用低得多的价格从别的父母处得到自己的生命。尽管事实上这种契约不可能存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假设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父母可能将资源投资去生育子女,也可能去做其它投资行为。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竞争的结果是产出与投入之差应该是平均利润。因此,父母的孝亲利益应该等于其投资成本+平均利润+利息收入+风险收益。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符合经济学原理,理论上也十分完美,但在实践中却难以“算计”。
根据经济学原理,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孝亲标准,那就是子女的每一孝亲行为其投入的成本(指机会成本)不得高于其父母从这一行为中获得的孝亲收益。或者,反过来说,子女孝亲行为投入的成本低于或者等于其父母的孝亲收益,子女的孝亲行为就是理性的,也是应该的。这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资源总应该向最能创造价值的使用方式流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父母的生育成本或者投入,是为了从孩子那里购买到子女对自己的孝亲收益,而孝亲收益又是子女资源被消费的结果。如果子女的资源本来可以用于其它地方产生更大的产出,而父母强买过来用于自己的更低效率的消费,则是不理性的,也是对人类有限资源的浪费。假设,子女的某一资源,如1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其它地方,只能创造100元的财富;但是,子女用来陪伴自己的父母,却可以给父母带来120元的孝亲收益,他就应该陪伴自己的父母。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陪伴父母的第1个小时是最珍贵的,给父母带来的收益也是最大的,之后每1小时,其价值都会递减。因此,常回家看看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要求子女总陪着父母,或者子女从来不陪伴父母都是不合理的。再例如:卧冰求鲤。卧冰伤身,甚至有性命之忧,行孝成本极大,而只求一鲤,母之收益甚微,这就是“愚孝“了!
三、中国古代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合理性评析
中国古代孝观点的起源甚早。《尔雅·释训》的“孝”解释是“善事父母”,《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据柳诒徵先生考证:“孝”字始见于《虞书》。《尚书·尧典》:“克谐以孝,丞丞父,不格奸。”他并且指出:虞、夏同道。夏道尚忠,复尚孝。[3]与此同时,孝亲法律制度也在夏朝得以确立。著名学者章炳麟先生曾著有《孝经本夏法说》之考证。
孝亲法律制度一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法制之一。历代律令有关于孝亲的规定非常多。笔者将以《唐律疏议》的记载为中心进行讨论,其孝亲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倡孝养父母
赡养父母,这是子女孝亲的最基本义务,也是父母生育子女最基本的孝亲收益。因此,《唐律疏议》将“供养有缺”纳入“十恶”之“不孝”行为。同时,《唐律疏议》又规定:“若供养有阙,疏议曰: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4]从犯罪构成上来看,疏议特别规定了二点:其一,“堪供而阙”;其二,“告乃坐”。由是可见法律规定得十分理性,其一,法律考虑了供养能力,并非要求子女无条件不计成本地赡养父母,“家实贫穷,无由取给,如此之类,不合有罪”。从经济理性上看,我们可以认为,法律将“子女的孝亲成本大于父母的孝亲收益”的孝养义务排除在强制履行之外。其二,法律坚持“不告不理”原则,这不仅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法律实质上坚持了“自愿交易”的市场交易原则。只有父母认为子女“违约”,司法才有权介入。
2.禁止亲在别籍、异财
《唐律疏议》将“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也纳入了“十恶”之“不孝”行为。唐律的这一条规定在今天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是不是一条对子女自由权与财产权进行家庭专制的条款呢?从经济学上看,财产权的共有关系既不利于财产使用价值最大化,也不利于财产的交换;而且,由于家庭成员的利益与其生产活动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子女有可能缺乏积极性,消极怠工。禁止子女别籍,从今天的法律上讲,实质上是限制子女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是禁止子女取得民事法律上的“人格”。这样的规定,不仅不符合经济理性,而且确有家庭经济专制之嫌。
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这样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什么?《疏议》曰:“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 。”[4]从《疏议》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禁止亲在别籍、异财的立法目的在于为孝养父母提供物质保证。在古代社会,劳动生产率低,必要劳动时间多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较少,孝养父母是一个相对较重的家庭负担。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制度性保障,孝养父母的法律规定可能成为具文。《大元通制条格》就有相关记载 :“今照得土民之家 ,往往祖父母、父母在日 ,明有支析文字 ,或未曾支析者 ,其父母疾笃及亡殁之后 ,不以求医侍疾丧葬为事 ,止以相争财产为务 。”[5]“伏见随路居民有父母在堂 ,兄弟往往异居者 ,分居之际 ,置父母另处一室 ,其兄弟诸人分供日用 ,父母年高自行拾薪 ,取水执爨为食。或一日所供不至 ,使之诣门求索。或分定日数 ,令父母巡门就食,日数才满,父母自出 ,其男与妇亦不恳留。”[5]从这些记载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考虑到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的法律规定实属必要。从法律的经济分析角度说,根据波斯纳定理:(1)如果一项权利的价值是当事人财富的一大部分,那么,权利在何处结束将取决于其初始分配。(2)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社会,孝亲资源无论对于父母还是子女,都是一笔不少的财富;同时,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进行市场交易实属不可能。因此,财产权以及其它权利的归属应取决于谁最需要它们。显然,年老的父母更需要财产权作为养老的制度性保障。
3.禁止殴打、虐待父母
《唐律疏议》将“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纳入“十恶”之“恶逆”;将“诅詈祖父母、父母”纳入“十恶”之“不孝”。这样的“恶逆”“不孝”行为,今天在刑法上仍然是一种犯罪行为。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对父母的人身伤害比之凡人来说处罚要严厉得多。其实,这一点从刑法的经济分析角度来说,是很好理解的。犯罪所侵害的利益越大,保护这种利益的法律措施就会越严厉,刑事处罚也会越重。对父母的人身侵害行为,侵害的客体不仅是父母的人身利益,还有孝亲利益,对父母的伤害比之凡人更甚。
4.赋予父母教令权
《唐律疏议》禁止子女违反父母教令:“诸子孙违犯教令,徒二年。谓可从而违。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同时,又禁止父母教令权的滥用,《唐律疏议》规定:“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以刃杀者,徒二年;故杀者,各加一等。即嫡、继、慈、养杀者,又加一等。过失杀者,各勿论。”[5]中国古代法律赋予父母权限极大的教令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人身伤害,包括违犯教令的殴杀与无违教令的故杀,法律规定的处罚比之凡人轻得多,过失杀更是不予处罚。
这些规定引起了现代法学家们强烈的批评。如果仅仅从孝亲角度思考,父母为了保障其孝亲利益,动辄使用家庭暴力,甚至有权对子女进行极大的人身伤害,导致孝亲收益与孝亲成本之间的严重失衡,这样的法律规定是完全不符合经济理性的。
然而,中国古代法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有必要对教令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事实上,古代父母的教令权,其权利属性是十分复杂的,其权利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父母孝亲利益的自助性强制保护权。在中国古代,父母的孝亲利益如果受到子女的损害,国家公权力一般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先由父母凭借其在家庭或者家族中的优势地位,进行自助性的强制保护。
(2)父母对子女的强制教育权。父母为了自己与子女自身的利益,在伦理和法律上也有教育子女的义务,在“望子成龙”的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由于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不足,为了花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教育效果,“体罚教育”成了教育子女的必要的而且被当时普遍认为是高效率的教育手段。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强制教育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教令权的名称就源于此。
(3)父母代行国家的部分司法惩处权。在古代社会,父母对子女的犯罪等不法行为有“同居相为隐”的伦理与法律权利,但父母在不告官的情况下,却可以私自行使家庭教令权,代替国家司法惩处权,对子女犯罪等不法行为进行家法惩戒,例如对在外实施杀人、强奸的子女进行家法处死,并且这种权利经常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
(4)父母对子女的劳动生产控制权。在中国古代,家庭还是一个农业生产组织,为了保证劳动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控制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家法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的企业等生产经营组织往往通过罚款、开除等劳动处分来解决生产经营的控制问题,但在古代社会,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赋予父母教令权。
总之,教令权的设置有其深刻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且牵涉到的法律关系是多方面的,父母行使教令权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孝亲利益。从总体上说,教令权的设置在当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也是有其经济理性的依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今天再提倡教令权,那就明显地不合时宜了。
5.维护父母对子女的主婚权。
中国古代强调婚姻成立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教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不遵父母之命的婚约或者婚姻在法律上无效,在社会上也不被人们认可。
中国古代婚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买卖。如妃字本义为帛匹,帑字本义为库藏;婚礼中的纳采、纳吉就是纳钱财买卖妇女之俗;《唐律疏议》规定:“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买卖婚姻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古代社会,“妻子嫁到夫家去,这几乎是各地的通例”,[6]女儿一旦嫁入夫家,则几乎完全与娘家脱离了经济关系,甚至没有赡养父母的职责。因此,父母生育女孩的成本如果没有买卖婚姻的制度保障,几乎是“血本无归”。尽管买卖婚姻成了父母生育女儿的激励机制,但由于买卖婚姻的市场竞争事实上存在,父母无法取得超额的,有时甚至是本应该获得的孝亲收益,因此,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在此可以找到很好的经济学上的注脚。
尽管买卖婚姻是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激励父母生育女儿的法律机制,但还是遭到了批评家们的普遍指责。从经济学上看,一项不能交易的权利的初始分配应该取决于谁最珍视它。从这个角度考察,主婚权的法律归属取决于父母的孝亲收益与女儿的婚姻幸福之间孰重孰轻。在古代中国,思想家和立法者选择了前者,这是非常遗憾的。但要求他们当时将婚姻幸福的价值与孝亲价值进行现在看来“正确”的选择,也是不现实的。由于女子成婚后,与娘家几乎完全脱离了关系,主婚权这样的制度设置,有时会对女子的婚姻幸福造成致命的伤害。由于父母受自利性的经济理性的驱使,他们往往不考虑女子的婚姻利益,一味地在市场上追求卖一个好“价钱”,有时甚至将女儿嫁给“老、幼、疾、残、养、庶之类”。因此,当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时候,父母对女子的主婚权首当其冲,这是必然的。
至于父母对儿子的主婚权,其造成的对儿子婚姻幸福的伤害相对要轻得多,这是因为女子嫁入夫家,成为夫家的一员,儿子的婚姻幸福与父母孝亲利益的冲突远没有“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那么激烈。考虑到一个新成员加入一个家庭对父母利益的影响,比之儿子的婚姻幸福,父母的主婚权有更多的经济正当性。
四、结论
中国古代孝亲法律制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经济功能上看,孝亲制度主要是激励了父母的生育欲望,从而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繁衍和增长创造了制度性保障。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著称的柳诒征先生曾经认为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者,有三种特殊之现象:第一,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第二,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第三,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3]事实上,这三种特殊之现象都与孝亲制度这种人口增长的激励机制有着非常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反面例子,那就是古罗马。罗马法没有强烈的孝亲色彩,而是企图从另一个方面解决人口增长问题,那就是国家通过羞辱与刑罚的手段,使人们结婚并生育孩子。据孟德斯鸠记载,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这项强制和鼓励生育的法律,人们称它为《茹利安法》。他在颁布这项法律时,曾经说道:“疾病和战役夺走了我们这么多公民,如果人们不再结婚的话,这个城市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城市并不是由房屋、廊点和公共场所,而是由居民所组成的。……我惟一的目的,就是共和国的永世绵延。我增加了对那些不服从的人们的惩罚。至于所给奖赏,我不知道任何品德曾经接受过比这些还多的奖赏。”孟德斯鸠这样评价:“这项法律是一个真正的法典;它把关于这方面一切可能制定的法规都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它们的范围很广泛,影响所及的事物又很多,因此成为罗马民法最优美的部分。”[6]但结果并不理想,人们宁愿舍弃生命,也不娶妻育子。罗马人征服了世界,但却毁灭了自己。也许正是有了孝道文化和孝亲法律制度,中华民族没有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烦恼,也没有古罗马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命运,它虽然历经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灾难,但却真正做到了生生不息、永世绵延!
[1][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林毅夫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邵增桦.韩非子今注今释[M].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年.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大元通制条格(郭成伟点校)[R].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On the Economic Reason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Legal System
QI Bao-guo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Xiantao Vocational College,Xiantao,Hubei,433000,China)
Filial Piety legal syste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legal systems in ancient China.It is the product of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 in a specific time.The existence of it has its reasonable economic foundation.In terms of economic func-tion,filial piety legal system encouraged parentsπdesires of procreation,and create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labor,in another words,the breeding and increasing of population.
Filial Piety;legal system;economic analysis
D909.92
A
1672-934X(2010)06-0059-05
2010-08-18
綦保国(1974-),男,湖南衡阳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仙桃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责任编辑 刘范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