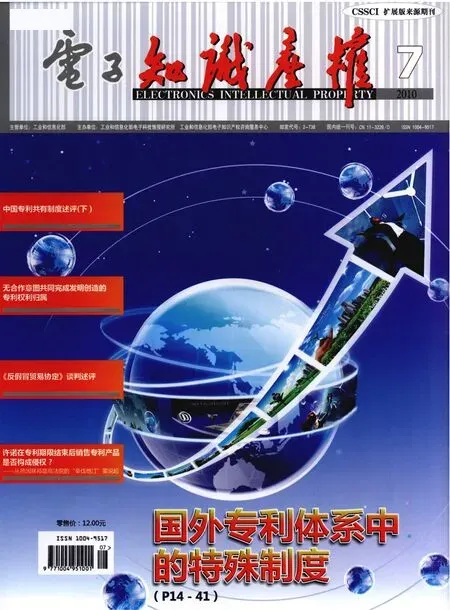中国专利共有制度述评(下)
崔国斌/文
五、共有专利的实施与许可
依据《专利法》第15条,专利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共有专利。联系上下文,共有人无需同其它共有人分享单独实施所获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专利法》的这一规定与过去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是一致的。最高法院2001年在一份名为 《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的文件中指出,共有专利的专利权人在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专利权人自己可以自行实施该专利,由此所获得的利益归实施人,该文件实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1.《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第50条。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取代了上述会议纪要,但并没有重复共有人自行实施权的规定。不过,这应该并不意味着法院立场有实质性改变。
与共有专利实施有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共有人是否可以单独许可第三方实施该专利。在中国民法的传统观念中,单个共有人所享有的权益并非一个完整的所有权,认为“如果按份共有人的份额形成单个的完整的所有权,将会使共有形成为多重所有。”[1]因此,《专利法》没有接受美国法的激进观念:每个共有人享有完整的实施权利,可以让被许可人‘踩着自己的脚印’获得相同的权利,从而支持共有人无限制地向第三方发放许可[2]。中国《专利法》第15条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
《专利法》第15条的规定实际上抛弃了中国过去法律实践中的做法。中国原先的《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规定,当事人就共有专利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征得共有专利权人的同意,2.《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1989,已废止)第67条。由此获得的利益由各方等额分享。3.《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1989,已废止)第50条。后来,统一《合同法》出台,《技术合同实施条例》被废止。上述规定并没有被收入统一《合同法》。不过,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还是依据《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则。对此,最高法院原法官蒋志培指出:“对共有专利的实施,应当经过所有共有人同意并协商收益等问题,是法律的本意,并被我国民法等多部法律所肯定,是基本的法律常识问题。”[3]科技部在2006年的行政规章中持相同立场。4.科技部《关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知识产权管理的暂行规定》(2006)第14条:“……6.合作方中任何一方同第三方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事先征得其他各方的同意,并由合作各方共同确定专利使用费标准。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合作各方应当根据协议规定,合理分享……”2006年《专利法》征求意见稿中,也规定对外发放许可须经过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5.《专利法》(征求意见稿,2006.08)第A1条。在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如果专利共有人未经其它共有人的同意而许可他人实施专利,则该共有人和被许可方甚至可能构成共同侵权。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地域管辖问题的通知》[已废止](1987)第4条规定:“专利权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由许可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许可方实施了专利,从而双方构成共同侵权,则由被许可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是一个关于程序问题的司法解释,但基本反映了法院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本篇法规已被法释〔2001〕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代替,但针对这一问题却没有明确规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会议讨论稿2003.10,此为2004年司法解释的前身)第34条明确规定:“共有专利的专利权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专利的,构成专利共同侵权。”但是,后来这一条并没有被公布的司法解释所接受。
正因为禁止共有人单独发放许可被视为一般规则,最高法院还特意为这一规则创设了一个例外:在共有人自己有实施专利的权利,而又没有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以一个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或者使用”。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第21条;此《解释》之前的《纪要》第50条所规定的例外中还将专利共有人“与一个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合作实施该专利或者通过技术入股与之联营实施该专利”的方式视为共有人自己实施。后来的《解释》中没有重复这一例外,陶鑫良教授等的报告认为,可能是觉得涉及出资行为导致所有权的转移,所以不能由单个共有人进行[4]897。最高法院从宽解释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开发市场中确有一些当事人虽享有实施权却不具备自己独立实施的条件,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也影响到技术的转化、应用和推广,故将发放一个普通实施许可证视为当事人自己实施。”[5]这一类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共有人通常是中国的大学或者科研院所,它们一方面没有对技术进行商业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缺乏技术转让和许可的实际经验,容易陷入“共有却无法获利”的困境。
《专利法》第15条在共有人许可第三方实施问题上背离传统做法的原因,可能是立法者觉得这样会促进专利的实施。比如,比较权威的意见认为:“发明创造价值的体现有赖于其实施应用,《专利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立法宗旨之一在于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因此,尽可能为合法实施专利创造有利条件,是《专利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在专利权共有的情况下,如果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共有人之一实施该专利都必须获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就会阻碍专利的实施。”[6]不过,如果《专利法》规定共有人在发放许可后无需和其他共有人分享许可费,似乎更能促进该专利的实施。
作为对比,中国法对共有技术秘密许可的处理,与共有专利权的许可显著不同。《合同法》第341条规定,“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依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意味着技术秘密的共有人“均有不经对方同意而自己使用或者以普通使用许可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技术秘密,并独占由此所获利益的权利。”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第20条。这一规定或许考虑到技术秘密本身的特殊性,在共有人没有明确约定禁止共有人未经同意对外披露或许可的情况下,通常意味着共有人没有共同采取切实的保密措施,因此每个共有人不承担所谓的默示保密义务,可以自由对外披露或许可。两相对照,本文倾向于认为《专利法》和《合同法》采用不同的规则,人为地增加了混乱,却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政策利益。
六、相关的行政与诉讼程序
(一)行政程序
《专利法》对专利申请共有人对共有事项的决策程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操作层面,主要依据是专利局的《审查指南》。《审查指南》中明确指出:“凡办理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如:提出专利申请、委托专利代理、转让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撤回专利申请和放弃专利权等)时,均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在文件上签字和盖章,并由全体共有人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专利局将视情况分别作出视为未提出该手续或者通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之内补正的处理。”9.专利局《关于办理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的规定》(1990)。如果共同申请人“对涉及共有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应当由共有人共同提出复议申请。”10.《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规程》(2002)第8条。显然,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共同申请人通常需要共同对相关事项做出一致决定。
在海关保护方面,过去的规则是“共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中任何一个权利人已向海关总署提出备案申请后,其他权利人无须再提出申请。”11.《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1995)第6条(本条例在2004年失效,为新修订条例所取代)。这似乎意味着单个的共有人就可以启动海关程序禁止第三方的进口侵权产品。不过,修订后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删除了这一规定,背后具体的考虑不得而知。
(二)诉讼程序
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之前,专利共有人对第三方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是否需要经过全体共有人的一致同意并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共有专利权人典型的诉讼的请求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停止侵害;其二是损害赔偿。这两类诉讼请求对诉讼主体的资格要求有所不同,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首先,关于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在传统的民法领域,当共有物受到第三方妨害时,各共有人的权利及于整个共有物,各个共有人可以为共有人全体的利益而行使物上请求权[7]。一般认可共有人的任何一人代表全体共有者可以提起物上请求权的诉讼以排除妨害[8]。依这一立法精神与法理旨意,“对于专利侵权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和诉前证据保全等与行使诉权密切相关的程序性权利,任何一方都可以单独提出请求。 ”[4]904,[9]
其次,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学术界对于共有人单独是否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存在争议。另外,即便支持单独提起诉讼的学者对于共有人是否只能对个人的份额提起诉讼,也存在争议[8]。但是,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争议,形成固定的程序规则。比如,北京高院对于合作作品采用下列规则:“涉及争议作品是合作作品的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合作作品的作者均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合作作品作者没有参加诉讼的,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作者下落不明,或者利用直接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公告送达。”1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02年12月27日)第7条[10]。从这一规定看,某个共有人单独发动诉讼并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只不过需要将其它共有人列为共同原告,即使其它共有人不同意参加诉讼。实践中已经出现共有人不参加诉讼、法院依职权追加其为共同原告的著作权侵权案例。法院甚至可以在共有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缺席判决,判决被告向包括缺席原告在内的所有共有人支付损害赔偿。13.参见王大良诉王岳红著作权侵权案,北京二中院(2003)二中民初字第722号。对此,也有权威法官持不同意见,认为共有人在法院正式通知后不愿意参加诉讼的,应作为放弃专利诉讼权利处理,其应当得到的侵权损害赔偿也应属于其他共有人[9]。不论赔偿的对象范围确切如何,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法院虽然要求共有人都要参加诉讼,但并不会出现因为个别共有人拒绝参加诉讼而导致其它共有人无法追究第三方侵权责任的情形。在美国法上,这倒是可能的。14.参见Ethicon Inc.v.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135 F.3d 1456(1998)。在美国,单个的共有人不能通过事后的许可协议赦免第三方事前的专利侵权责任,但是可以通过拒绝参加诉讼而事实上达到类似的结果。
当然,将合作作品的规则直接套用在共有专利上,未必可靠。因为共有著作权人发动诉讼,通常不会对合作作品的法律效力构成威胁,其它共有人一般不用担心著作权被宣告无效。但是,共有专利则不一样。单个共有人发动侵权诉讼,会导致被告对专利权效力提出挑战,从而威胁其它共有人的利益。其它共有人为了维护专利权的效力,可能要支付相当的诉讼成本。
《专利法》第15条并没有对共有专利侵权诉讼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如果我们将提起诉讼视为行使共有专利权的情形之一,则依据该条第2款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诚如此,则共有人似乎可以通过拒绝参加诉讼的方式来阻止其他共有人追究第三方的专利侵权责任。这也就否定了司法实践中法院的上述做法。立法者在制定第15条时,是否真的已经预见到这一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不清楚。
七、结论
中国《专利法》的历史还比较短,共有专利所衍生的法律纠纷没有机会充分展现。因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是很高,立法者也没有将完善专利共有制度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利权共有制度中的很多环节一直处在模糊状态。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时,立法者在《专利法》第15条中勾勒出专利共有制度的框架。不过,《专利法》第15条并没有充分考虑并谨慎对待中国法的现有实践,人为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同时,该条的规定依然很笼统,还有很大的改进和充实的空间。
将来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专利共有制度与技术秘密共有制度的协调问题,尽可能地使二者保持一致。其次,需要在《专利法》中进一步明确下列问题:专利共有的属性、共有权益或份额的确定、共有人转让共有权益的程序、共有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角色等等。本文旨在介绍现状、揭示问题,因而没有在制度设计层面对上述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希望能够为有兴趣了解中国专利共有制度的后来者提供一个入门的问题清单。EIP
[1]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29.
[2]Harrington A.Lackey.Problems in Joint Ownership of Patents[J].Vanderbilt Law Review, 1957,11:714.
[3]蒋志培.关于共有专利权实施许可的法律规定如何理解的答复[EB/OL].[2010-01-05].http:// www.chinaiprlaw.cn/file/200203131524.html.
[4]陶鑫良,袁真富等.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归属及职务发明创造完成人奖酬制度[M].//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5]陈永辉.正确处理技术合同纠纷,努力促进科技进步创新――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蒋志培就《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EB/OL].[2010-01-05].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144013.
[6]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导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4.
[7]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49.
[8]姚欢庆.大连音像出版社诉北京市海淀区音像艺术服务社侵害录音带专有出版权纠纷案[EB/OL].[2010-01-05].http://www.civillaw.com. cn/article/default.asp?id=10005.
[9]程永顺.中国专利诉讼[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72.
[1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审判工作规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31.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