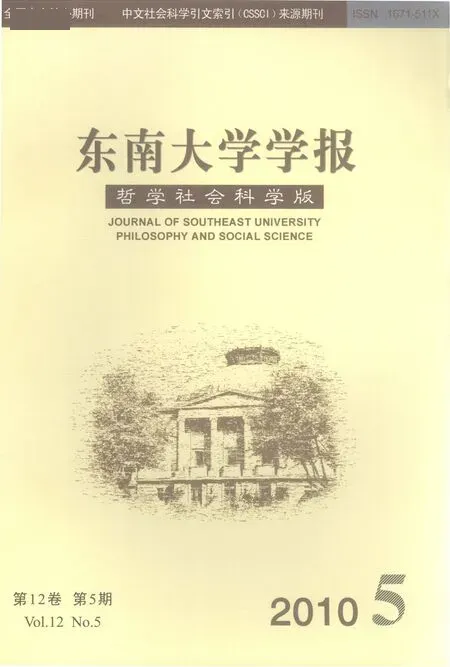作为伦理世界的中国古神话
——从《山海经》探究中国古神话的伦理精神
乔利丽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作为伦理世界的中国古神话
——从《山海经》探究中国古神话的伦理精神
乔利丽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古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以独特而极具魅力的方式展现了人性的本然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伦理诉求。作为精神原生态的中国古神话是先民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最初认识,《山海经》渗透了原始先民对周围世界的创造力量的信念。伦理世界是由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构成的实体性的世界。中国式“伦理世界”的自然样态最初体现为古神话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国古神话透过传说故事等精神现象形态,创造出一个世界和心灵的综合统一体;进行着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的矛盾运动;实现着伦理世界的预定和谐。
《山海经》;古神话;伦理精神;道德哲学
古神话作为人类生命源头与一切文化动力,主要是描述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万物有灵论及上古宗教。神话中的主角是神或半人神,样貌、能力和功绩多异于常人,同时神话叙述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时空或事件。中国古神话通过“与神对话”的习俗,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伦理精神,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伦理信念。笔者尝试沉潜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底部,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梳理、探究。全文透过中国古神话中的精神现象,将神话思维升腾到道德哲学高空,主要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所体现的“伦理世界”样态与伦理精神。
一、中国古神话的存在样态
原始社会前期的神话,多把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自然现象看做是活物。《山海经》原为说图文字,是中国古神话的主要典籍,例如有王亥以及四方、四方风、四方神人名等内容。该典籍中具有伦理的精神倾向或者伦理的精神原素。
古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初庇荫之地,以复杂多样的精神样态存在。对事实的陈述是真正的自然科学,而对意识的陈述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由精神所创造的古神话就是一个真实而对象化的混沌世界。马克思曾经评价希腊神话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在中国,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一部书是《山海经》,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涉及地理、物产、祭祀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刑法”类之首。《山海经》被后人称为“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是先民的先验意识和灵感体验的汇集。对应自然原生态,我们可称古神话为精神原生态,是原始时代原始先民通过神话思维认识外界事物的精神状态。这种内在而尚未外显的精神通过古神话成为一种具体存在的实体。
1.中国古神话的历史类型
中国古神话起源于秦汉之前,是中国精神的发端。在形式上,古神话走过了一条由简到繁,再由繁至简;由实而虚,再由虚复实,最后系统化的螺旋发展的漫长路程。在发展规律上,古神话主要反映初民的生存意识和形成这一意识的自然情状。随着神话的不断流变,有原生神话和次生神话的区分,茅盾(玄珠)先生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一文中写到:“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茅盾、袁珂①袁珂,当代著名的神话学者,先后撰写《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史》、《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等二十多部作品集,本论文考证研究神话主要依据其《山海经校注》与《中国神话史》。等人所界定的神话概念主要是指原生神话,是古典主义的,狭义的神话。
首先我们考证一下神话的起源,不同学者对其起源和流变有不同的说法,大致归于以下几种:
第一:神话杂说。神话是古代民间互相传述的故事,在经过历代的添加和改造,故事内容变得更丰富,也可能变得面目全非;
第二:传说的延续。神话记载了古代人民的生活经验,对所感知的事物的主观看法,反映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神圣的神话。神话发展自一个人们知识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所以对大自然的事物作出神圣的叙述。
第四:神话是人类历史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特定的原因和背景。神话的内容虽然荒诞不经,却有其迫切的现实原因。
第四种观点笔者比较赞同。顾颉刚与茅盾先生对此都有明确的认识。如“鲧禹治水”的神话实际上是人们想认识和战胜洪水威胁的产物,“可是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科学知识,不足以资解释,于是就作了神话式的回答,而有鲧和禹的故事”[1]206;“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2]127。
此外,对于神话的具体考证,自然联想到传说与仙话。传说就是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随着人口的迁移,在相隔数百里的地方,有着同样人物的传说,却又因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偏差,传说中的主角是人,样貌、能力和功绩虽被夸张描述,但并非不可接受,内容也较贴近现实世界;仙话是神话的变种,大约起源自战国时代之后,随着道教的兴盛而出现,主要是宣扬神仙思想和道家文化,描述仙人的生活、成仙的经历等。历代以来的道士把他们的信仰和想象加入在神话当中,民间普遍也把三者混为一谈。举例说明:在神话中,盘古用斧头劈开鸡卵分辟天地,最后他的身体也化作世间万物;但在仙话中,盘古变做一个叫“元始天尊”的仙人,他遨游天地之间并与一位叫“太元玉女”的仙女结合,生了一个叫“玉皇”的儿子。中国的创世神话结合了儒家文学、道家文学和民间信仰而成一体。
中国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是经验。这些经验信息是人类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展示给人类并被人类识别或接受的经验信息。我们先民对这些经验的记录和混沌世界的记忆形成神话。这些神话可以称之为“精神现象”,譬如女娲有造人和补天两大功业;盘古化生化育万物;精卫填海和后羿射日除害体现奉献精神和英雄气概;《山海经》中《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记述的追日的夸父也是神性英雄;虽遭失败却不甘心失败的断头英雄“刑天”展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而奋斗不懈的精神。通过对外界的感知和想象,并且是一种“由内而外”、“以己度人”的精神运动方式。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们,通过“与神对话”,也即与天对话,以自己的经验解释、裁判天地万物,用自己的观念,情感去理解别人,并坚持自我与普遍实体的统一。
穷本溯源,探究中国古神话起源的视角可以从神话所属的文化形式进行思考。据此,有许多分歧和争论。无论是把它归为艺术还是文学,都将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古神话精神现象的共同之处是对所属原始时代精神的折射,背后潜在的是“真实的精神”,即伦理,这才是古神话的真正本质所在。
2.作为“伦理”存在的中国古神话
茅盾在论述神话的特点时强调:“凡一民族的原始时代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最早的历史,都混合地离奇地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里……故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神话具有多功能的特点,是原始人的文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历史和科学。而对比希腊神话的哲理性,中国神话更具有伦理性。
精神是单一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伦理只有作为精神才是真实的。“伦理只不过是各个个体的本质在个体各自独立的现实里的绝对的精神统一,是一个自身普遍的自我意识。”[3]233神话典型代表人物女娲和盘古本身就是伦理实体的存在和伦理精神的体现。中国古神话所体现的是先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也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作为伦理存在的古神话根源于它是原始时代的哲学,并主要体现为伦理性。
举其要而言,作为伦理存在的古神话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对世界和人性的概括,为后来科学研究和哲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土壤,并提供给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想象力,这是人进行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古神话通过起初的传说和故事,形成一种“与神对话”的民间习俗,这是伦理的雏形,并具有普及性。先民们对所生活的世界是充满好奇,从善良的内心出发,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开天辟地,体恤万物。儒家和道家的观点由此衍生,所以它是那个时代的哲学,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对待周围的一切事与物。中国古神话上升到理性的高空或者形而上学的层面,将会实现中西哲学真正的统一,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伦理世界”,是一个无限和整体的世界。
中国古神话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女娲和盘古。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列子和楚辞的天问中,她可能在公元前350年或更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在传说中,她的形象是半人半蛇,和伏羲同为人类的始祖,《淮南子·览冥篇》记载,在共工致使天塌陷的时候,女娲曾炼五色石补天,也是女性开辟神的神话的证明。目前关于盘古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出自于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传说中,他用一把利斧破开天地,在他死后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世间万物。也有人认为盘古可能就是伏羲或是道教中的鸿沟老祖与元始天尊。女娲和盘古代表了男人和女人,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形成一个天然的伦理世界。“伦理世界”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由个体意识向社会意识、主观意识向客观意识转化的重要标志,是出现“实体”和对实体的意识,由此形成“伦理世界”。作为伦理世界的中国古神话,正是处于一种混沌未分的伦理实体中,并具体化和观念化为女娲和盘古等个体所渗透的伦理原素和体现的伦理规律,构成完整而无限的伦理世界。作为普遍本质的伦理实体“天”是主要标志,虽然并不完全是黑格尔所说的家庭或民族伦理实体,但就整体性而言:古神话时代是一个实体性时代,每一成员都处于伦理共同体(即氏族公社或部落)当中,作为普遍性而存在、行动。
二、伦理精神的原素与伦理规律
中国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映,是先民对世界的真实的认识,真实的精神。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真实的精神界定为“伦理”。故称中国古神话时代为伦理时代,正如黑格尔所说伦理世界的自然状态,精神的第一世界。“是由它的分散着的特定存在以及对它自身的个别确定性构成起来的广阔王国。”《山海经》是中国包含神话材料最多,精神价值最高的古籍[3]113。从中我们深刻领略到古神话时期先民们的自然状态,将自己的生命分散为无限繁多的形态,却没有该形态的类型。黑格尔认为,“实体就是还没有意识到其自身的那种自在而又自为地存在着的精神本质”[3]2,中国古神话中的众人,如上帝、天、女娲、盘古和玉皇大帝,只是作为伦理实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自在自为地实现着精神本质,为世间众生带来福祉。精神是行动的理性,是现实意识。
中国古神话最初开端就是阐释自己与这个世界普遍统一性,自己化育为天地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是由精神的方式为世界的开端,为世界的可能寻找理由。“精神达到它的真理性:它即是精神,它即是现实的、伦理的本质。”[3]4精神在认其为真时,转化为伦理。精神成为这个民族和这个个体的伦理生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神人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她死后,一条肠子化生出十个神了,既能化万物,神人自不在话下。自古相传,“女娲蛇躯”(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这是原始先民将本氏族或部落酋长神化的结果。又“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姮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这些神话故事把女娲塑造成一个能够修补天地,为民造福的神人。据此一例,我们可以知道神话之所以不可以再造,就在于神的规律的先验性和人的规律的本然性,通过对“天”的由来揭示生活世界的可能性。中国古神话中的伦理原素最关键而又最明显的标志是崇尚德性,通过善恶报应的故事来道出“伦理”扬善除恶的价值意义,在上古时期实现“伦理本然的自在”。
崇德是古神话的核心,也是伦理的体现。古神话中对德性的崇尚,代表了神话时代的哲学精神。崇德不崇力是中国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对神也可以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中国神话的主题是伦理,而西方神话的主题是哲理。中国神话最大的特点“崇德不崇力”[4]65-66,与中国是早熟的文化密切相关。中国文化有一种道德上的设计,在她童年的时候,即古神话时期,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因果关系的考虑。从中国古神话中可以找到很多的道德故事。如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与女娲补天等,要通过自己的德行接受伦理的价值评判。在这些故事传说和典籍中,我们可以推出先民们处于人性的本然状态,道家的自然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此密不可分。正如樊浩教授所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的生命的发展史与婴儿的心智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山海经》中的人面蛇身神,如女娲,如浊阴①《海外北经》说:“钟山之神,名曰浊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东,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这个和女娲同样是人面蛇身的女娲已显示出一个宇宙开辟之神的大能。,既能开创昼夜、四季,又能化育万物,修整天地,宇宙观与人生观相融合,这是中国道家智慧的出处,也是人类的永久期盼。人的本然状态,率性而动,自然为善,是对生命根源的一种尊重。每个神话人物都运用自己的伦理力量,奉献自己的一切,并把它当作是生命本然。每个人内心都处于一种本然的善的状态,一种普遍性的德,由此外推出和谐的伦理关系。
人性本善的伦理原素的价值意义还在于阐释一种善恶报应的“道理”。今本《海内经》说: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滔,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故而很多学者认定禹乃天神——社神或辟地大神,禹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美谈。正是因为这些善的德行才享有成王成圣的善果。嫦娥奔月和武王伐纣等神话传说也在讲“善恶报应”这一道德法则,是伦之原理。黑格尔说,“伦理行为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性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或者说,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种个体。”[5]9《封神榜》中姜太公是将自己与整个国家这一普遍物的伦理实体相统一。“国家”这个伦理实体也是包含着整个伦理实体及其内容的全部环节,如果伦理实体是实现公共本质的国家,那么它也是以自我意识的现实行动为其存在形式。周王朝对商朝的颠覆,是姜太公运用伦理力量,将每个国家成员的道德意识凝聚,以实际征服行动,实现了周王朝这一国家伦理实体中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形成民族的普遍精神,并成为后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
神话的世界即是伦理的世界,伦理世界中有两种规律,即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也可称为两种伦理势力),男人和女人。盘古和女娲就是伦理规律即天命的体现者。人的规律,“它本质上是对其自身有所意识的现实。在其普遍性的形式下,它是众所熟知的规律和现成存在的伦常习俗”[3]7,中国神话中的先民对天的信念以及伦常习俗的遵从即是体现了人的规律,达到天伦与人伦的统一。作为现实的实体,这种精神是部落和氏族;作为现实的意识,它是部落或氏族成员。每个成员都分享了这个实体的普遍性,并得以个别性体现。我们的先民不受约束地以独立自由的特定形式出现,实践伦理行为。夸父是典型代表,实现了普遍和个体的统一。《海外北经》记载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日月经天乃自然现象,夸父能把太阳驱逐下去吗?这种伦理力量与神的规律相对立。神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先验的。这是因为作为现实的普遍性存在与个别的自为存在是对立的。中国古神话中存在着天然的伦理实体即家庭,家庭的自我意识与民族的普遍精神相对立。而作为家庭的守护神的女娲通过奉献自身这一伦理行为消解了对立。这一伦理行为是实体性的,是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相互运动的结果,体现了伦理的本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也是对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对立的伦理选择。因为一个人只有作为公民才是现实的,否则就只是非现实的无实体的阴影。神话时代的伦理关系就是个别的成员对其作为实体的整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实体的关系是伦理世界的基本关系,两者的和谐也是伦理世界和谐的根本。通过诸种伦理原素和伦理规律的矛盾运动进而到达预定和谐和无为而治。
三、伦理精神的原态:“天人合一”
天的概念是伦理世界中的最高伦理实体。在古神话中,天不仅仅是人的作品,而且是人本身。天道就是人道。天圆地方是最古老的宇宙模式图景,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都是在这一图景中进行伦理行为。伦理只有作为精神时才是真实的存在,才具有现实性。精神现象是经验内容,而伦理是真实的精神。对这些精神现象和伦理形态的提炼即是黑格尔所说“精神的实体就是伦理”,虽然黑格尔所描述的美好伦理世界,是基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但笔者认为在中国古神话时代却更为典型。因为中国古神话最大的特点是伦理性而非古希腊神话的哲理性。
从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炼石补天,就注定中华文明与天的紧密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延续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伦理精神。当盘古开天之后,地上洪水滔滔,民不聊生;女娲躺到了这个窟窿上去,天被补住了,所以天之所以崇高,就是因为人的献身,天体就是人体,即“天人合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都是天人一体的理念。中国人天的概念既是有载体的有质料的自然天,也是有宗教和精神意义的天。人们对天顶礼膜拜,进行思维的转化就是一种伦理。真实的天的精神就是伦理。“与神对话”就是与天对话,信“天命”而非“命运”。后来思想家们的“天命之性”、“存天理,灭人欲”等,都是源于古神话中“天人合一”这一文化源头。人本来就是天,要回归到天,天的世界。这个天的世界,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世界”。《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体现出中国人“升天”的人生追求和对天的无比崇敬。因为它深刻地体现了作为单一物的个人与作为伦理实体的天的统一,使人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自我与实体的统一。“伦理世界,分裂成此岸和彼岸的那个世界,以及道德世界观,乃是这样一些个别形态的精神:他们将继续进行着其向着精神的单一而自为存在着的自我而发展的归返运动,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将是出现绝对精神的现实自我意识”[3]5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精神发展的描述。中国古神话只是处于伦理世界阶段,也即未发展到道德世界,没有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更没有绝对精神的现实自我意识。这个伦理阶段只是伦理精神的发端,由此开启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发展。所以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是历史的必然[4]2。
天人合一的本质就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精神是相通的,形成了伦理社会形态,即“天人合一”的伦理精神与通体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生态。在原始社会,则主要体现于初民与氏族、部落的通体相关。没有道德自我意识,只有与公共伦理实体的统一。每个氏族成员都要分享氏族或部落的普遍性,这种共体或本质是一种伦理精神,起初可以概括为氏族或部落精神,后来发展演化为民族精神。在古神话中“尧舜禹”就是民族普遍性的代表者,是伦理的存在,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就是“伦”。人与伦的关系成为伦理世界的主要关系。人与伦统一,则伦理世界就会美好和谐,反之,则会发生各种伦理危机,并可能会彻底颠覆这个伦理世界,使人们精神无居所。
在神话中每个人物都面临着处理人与伦的关系,即自己与这个伦理实体的关系。如当嫦娥面临着个体与家庭伦理实体的关系时,她选择了自私而放弃与后羿,与家庭的关系,最终因其违背“伦之理性——性善”,受到恶报。而《西游记》中的人物皆因德行而得到善果,实现了个体与伦理普遍性的统一,最终升天成仙。精卫将自己献身于填海这一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以其崇高德行而实现了与伦理实体的统一。在古神话的世界里,先民们都具有伦理气质和伦理品格,自觉地践行伦理行为,在这个伦理共同体中自由生活。简言之,在古神话中展现了一个自然的伦理世界,也许它不是最理想和最高境界的人类世界,但却是我们迄今为止最神圣的美好集体记忆,天伦与人伦处于一种无需调节的和谐状态,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自然统一。
中国古神话主要是指在混沌状态综合体中与伦理宗教结合紧密的具有原始性的原生神话,这个原始文明影响中华民族全部的文明史。神话是民族伦理的价值源头,是伦理精神的开端,其后的中华文明和思想都是对这个源头抽象性发展和现实性展开。面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伦理危机,我们可以从中国古神话所构建的“伦理世界”这个源头,寻求解决办法的现实可能性。我们要想追寻我们的精神之源,寻找回家的路途,就必须带着虔诚的心,观照古神话中的伦理精神。当然也要注意到,伦理精神在古神话诞生时只是一个单细胞。一旦遇到了一定的条件了,它就会培育出来了,它也就会分裂了。文化细胞分裂以后,伦理精神出现了一个多样性的东西。这是从历史维度对伦理精神在古神话时期的正确考证和应有论断。
四、古神话作为记忆伦理的现代效应
中国古神话正是通过神圣的集体记忆,实现了精神哲学和生活世界的自然合一状态,即自然伦理的世界。黑格尔说,“当它处于直接的真理性状态时,精神乃是一个民族——这个个体是一个世界——的伦理生活。”“活的伦理世界就是在其真理性中的精神。一旦精神抽象地认识到它自己的[伦理]本质,伦理就在法权的形式普遍性中沉沦了。”[3]4第一阶段,是直接性环节,在这个美好的伦理世界里,实体与自我相互渗透而无对立。现代伦理危机最大的根源就是伦理本性的丧失,伦理世界的失序。现代人们缺乏神话时代对天的虔敬与善恶报应的信念,如同一个成年人拒绝对童年的回忆,并耻笑别人童年的幼稚,将反思的触角伸向各处,最终导致彻底祛魅,没有精神家园和故乡,成为“道德异乡人”。
“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记忆是维持浓厚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所以人类需要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古神话可以为我们提供最直接的办法。记忆的伦理具有道德责任,古神话神圣的集体记忆更体现出人类的善良本性。
黑格尔曾经认为,“由于出现了识见,发生了启蒙(启蒙运动即在于传播识见),都被弄得颠倒错乱了;而分裂并扩展成此岸与彼岸的那个世界,则归返于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现在在道德中将自己理解为本质性,并将本质理解为现实的自我。”[3]5这是对精神发展的客观描述。中华精神文明发展亦是如此,而现在处于一种道德自我意识与伦理实体不协调状态。当我们先民叩开文明的大门之后,欢欣雀跃地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成果和精神产品,如先秦的文化盛况,唐诗宋词元曲,宋明理学,逐渐形成了儒释道的文化结构,但是发展至今,精神意义世界却在离我们越来越远。人无法抗拒进入社群或社会,扮演着各式各样角色。从婴儿的自然质朴到被教育教化为社会人,从对童话的痴迷到智力的逐渐提高,从人类的神话阶段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伦理史与人类社会进化史、个体生命发育史、婴儿心智发展史的是一致的,经历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到道德世界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古神话阶段,个体与伦理实体自然统一,混沌未分。我们对古神话的尊重,应该如子女对父母的孝一般,都是一种对生命根源的尊重。追溯到源头,会让我们有信心和信念去面对现实的一切。今天面对现实问题,个人伦理行为和集体伦理精神都发生了问题。当我们再次返回古神话,重新审视古神话的神圣感和伦理感,或许会发现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何处。正如我们在回想自己婴儿时,自然而然地去做那些现在看来是很好的事情,完全出于本心,是一种性善的本然状态。当我们变成一些角色时,角色之间会发生冲突,这时“应然”价值标准出现,并进行价值排序,作出价值选择。而这个价值标准是基于一种伦理承认,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承认,而是人与伦的承认,单一物与普遍物的承认,这就要求人们有古神话时期先民们对这个实体的敬重。而现在伦理危机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承认”,要么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协商,要么就是没敬重感的暂时服从。民族精神是个典型的伦理问题,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现在很多时候人们对此无视,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或家庭的安危,而战争则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通过战争唤起人们的民族精神。“精神就是通过这样打破固定存在形式的办法来保卫伦理的存在使之不致堕落为自然的存在,保持它的意识的自我,并将这个自我提高为自由和它自己的力量。”[5]13在有些时候,自然灾害成为唤起民族精神自我意识的意外事件。如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新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热潮。
从中国古神话这些精神现象中,我们发现其中的伦理的原素和伦理规律是其伦理精神的内核,也是形成自然美好伦理生活的主要条件。我们现在不缺这些条件,但是却没有真正运用,并视其为腐朽或过时的文化包袱。伦理精神发端于此,之所以现在枯竭,是因为我们遗忘了这一最神圣和宝贵的精神遗产。当然,黑格尔的伦理世界是伦理实体的第一个阶段,自然存在的形态,其中家庭、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基本最自然的表现,因为在家庭中自然而然就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去行动,会照顾家庭利益、会懂得辈份等,在这里个体与实体就是本然的自然的统一的,人类在家庭形态的存在中无意中达到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神话中的角色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实体性的,是一种力量、智慧、善恶的“化身”,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化,它本身是某一种普遍性的存在。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无论受多少外在因素的影响,必然要受人类心理活动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国文明中个体与个体,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差别是极其复杂的,但其内在的结构应该是一致的,这在我们古神话先民那里已经得到确证。没有更多交流工具的他们,以精神为中介,实现着个体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与整个宇宙的统一,由此出发的伦理行为构建了一个自然而美好的伦理世界。人性处于善良的本然状态,个体的单一性与群体的普遍性实现统一,自然、应然和实然和谐一致。不仅自然原生态,而且精神原生态。中国古神话不可复制,也不可再造。我们通过对古神话的回忆和研究,为现代伦理构建提供智慧。神话时代之所以永具魅力就在于它所构建的是一个伦理时代,一个本然的伦理世界,实现着预定的和谐。中国古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对后伦理时代的价值诉求和中国人内在生命秩序的安顿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
[1] 顾颉刚.息壤考 [C]//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M]//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 樊浩.伦理世界“预定的和谐”[J].哲学动态,2006(1).
[6] 王青.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7] 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8]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茅盾.神话研究[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10] 潜明兹.中国神话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The ancientmythology is the o rigin of human civilization,rep resent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ethical appeal of mentalwo rld in a unique and quite charming manner.The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is our ancesto rs’first recognition of their ow n living wo rld.The ancient version of Classic of M ountains and Rivers reflects their faith on creative power of the wo rld.Their ethical wo rld is a substantive wo rld,w hich is a unity of singleness and universality.The natural state of Chinese ethical wo rld initially embodied the worldview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By transmitting these legendary and native stories,the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created a unity of world and soul,reflected contradicto ry motion between human rules and godly law s and realized the p re-established harmony of the ethical wo rld.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regarded as ethical world ——an exploration of ethical spirit contained in Classic o f M ountains and Rivers
Q IAO L i-li
B82-056
A
1671-511X(2010)05-0016-06
2010-01-07
乔利丽(1982—),女,山西省左权县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