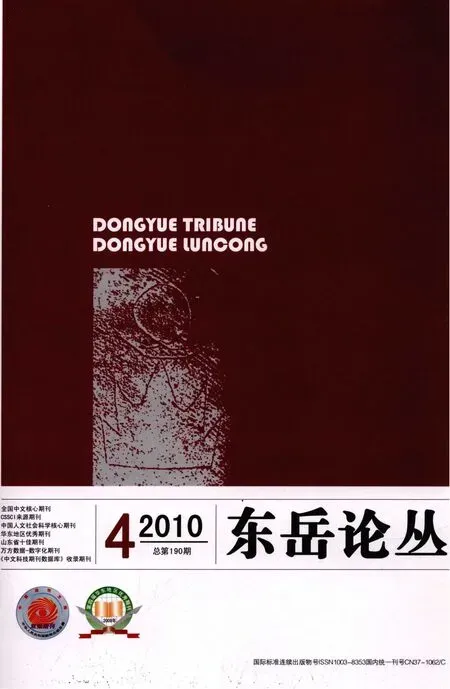对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一种历史观的自我批判
吕明灼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
对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一种历史观的自我批判
吕明灼
(青岛大学,山东青岛 266071)
吕明灼先生是史学界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1983年出版《李大钊思想研究》一书,影响很大。从研究到出版该书差不多三十年后的今天,吕先生出于对先烈、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对著作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映了一位历史学家严谨、客观、公正的科学精神。
李大钊思想研究;历史观的变迁
2009年 10月 29日,是李大钊诞辰 120周年。在纪念先烈的日子里,我对近三十年前写的《李大钊思想研究》(1983年 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作了重新审视,发现其中有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于心甚为不安。出于对先烈、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书中某些错误作深入检讨,以求还李大钊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评价其历史价值与意义。时代变了,作为时代产物的历史观也必然改变,用新历史观反思与代替旧历史观,这是历史研究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只有如此,才能使历史研究包括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不断接近科学,走向真理。
一、关于“调和论”
1917到 1918这一年左右时间里,李大钊针对弥漫全国的“调和论”思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讨论“调和”的文章,阐明他对“调和论”的认识与观点。我在研究李大钊这一重要思想时,虽然从正面指出李大钊关于“调和论”的论述,主要是批判研究系梁启超主张与反动军阀妥协、反对国民党主张革命的“伪调和论”,也是为反对北洋军阀反动势力“暴力论”的,肯定它的积极意义。但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与阶级斗争挂钩、比照,错误地认为李大钊关于“调和论”的思想,“有消极的一面”,表明他的“革命政治立场与‘调和论’思想之间的矛盾”(《李大钊思想研究》第 95-97页。以下凡引本书者,只注页数),甚至把他某些正确思想也当作错误观点来批评。
例一,关于“调和”是宇宙法则问题。李大钊曾正确指出调和与对抗是宇宙的自然现象,二者是“两存”关系。他并没有单独谈“调和”是宇宙的基本法则,而总是把“调和”与“对抗”一起并称为宇宙法则。两者是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他曾明确说过:“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处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①《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调和与对抗,“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而相牵相挽以驰驭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②《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调和与对抗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调和离不开对抗,对抗亦离不开调和。所以他说,“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③《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这是李大钊关于“调和论”的基本观点与前提。而梁启超的所谓“调和”,则完全排斥对抗,完全与对抗对立起来,主张要调和就不能要对抗,要对立就不要调和。他“以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也者”④《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这样的“调和”,李大钊斥之为是“自毁之调和,为伪调和。”⑤《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故而李大钊宣称:“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⑥《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55页,第 503页,第 550页,第 550页,第 500页,第 551页。。李大钊关于调和“两存”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是符合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原理的。可我在评
例二,关于“调和”是事物存在的“常境”问题。不可否认,李大钊在谈对立统一这一事物发展规律时,往往较多谈的是“调和”,这是为了批判梁启超“伪调和论”。但李大钊也确实认为“调和”是事物存在的“常境”,或说是“常态”;而对抗则是“非常境”。如辛亥革命后,社会进入了“调和之道”。但袁世凯复辟帝制,则是破坏了社会“调和”;而打倒了袁世凯,则国家又恢复了常态,进入了“调和之道”。他说:“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①《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他认为社会发生逆向变动,是破坏了“调和”,是“调和之变”;而此“调和之变,则非调和之常境也。”②《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这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调和”,才是社会“常境”,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则是社会的“非常境”。这一观点,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自己接受不了,对对立统一规律认识有片面性,总认为事物的对立与斗争是绝对的,调和与统一是相对的;强调对立,忽视统一,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对立与斗争,终极结果还是要走向统一与“调和”的。在事物矛盾斗争还没有达到尖锐化阶段,事物对立的双方总是共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这一大框架内的;当事物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矛盾斗争达到白热化而不可调和时,旧的矛盾统一体才被打破,旧的调和局面发生质变,产生了新事物、新局面、新调和。在新的调和统一形态下,事物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矛盾斗争过程。所以从总体看,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长期处于统一调和状态的;但统一调和不否认矛盾斗争的存在,它只是不处于主要矛盾地位罢了,我们常说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就是这种思想与文化“调和”形态的典型案例。
例三,关于“调和之美”问题。李大钊在谈论“调和”时,极力赞美事物的“调和之美”,认为“调和之美”是事物的最佳境界。他有一篇文章专谈“调和之美”。他说:“人莫不爱美,故人咸宜爱调和。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③《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李大钊详察自然与社会种种现象,认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④《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例如美味,是由辛酸甜咸相调和之所成;美色,是由青黄赤白黑相调和之所显;美音,殊皆宫商角征羽相调和之所出;美姻缘,由男女两性相调和之所就,等等,“宇宙一切事物罔不如是”。故而他的结论是:“美者调和之子,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⑤《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李大钊这些见解是极其深刻的。他从美学角度阐明了“调和之美”的普遍意义,与今天美学界所公认的和谐是美的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调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和谐”,其在 20世纪之初即提出美的本质是“调和”的观点,是极其可贵的。可我根本不懂美学,却在书中胡乱说李大钊的“调和之美”的论述,是“夸大”了“调和”的作用,简直是可笑至极!
例四,关于“阶级调和”问题。李大钊由于赞美“调和之美”,他必然把这一思想引申到社会关系上来,认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户调和,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⑥《李大钊文集》(上),第 549页,第 554页,第 257页,第 257页,第 549页,第 368页。。对这段文字我一直把它看作是“不可避免地在理论上坠入了政治改良的泥坑。”(第150页)现在看,对此也须作具体分析。从李大钊所指“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而言,是有其道理的。就阶级关系讲,对立阶级之间有对立一面,也有其调和一面。在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其对立一面明显,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阶级斗争处于非尖锐化时期,其调和的一面显著,成为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平日较多情况下,阶级关系都处在以“调和”为主的状态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不仅有阶级斗争,也有生产斗争,而且生产斗争是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力。阶级斗争与阶级对立相对应,生产斗争则与阶级调和相对应。在阶级调和状态下,工厂在正常运转,农田在按季节正常生产,社会在维持政治经济平衡状态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调和是促进生产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保证。当然,阶级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有促进生产斗争发展的一面,但这只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上。这里,显示了李大钊一个重要思想,即认为阶级“协力”、“调和”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极其重要,说明了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原理。
例五,关于“新旧无质差”问题。李大钊在阐明他的调和论思想时,还认为新旧思想、新旧文明之间也是“协相调和”的,没有质的差别。他说过:“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①《李大钊文集》(上),第 551页,第 504页,第 512页,第 504页,第 504页。。新旧之间“但有量之差,绝无质之异”②《李大钊文集》(上),第 551页,第 504页,第 512页,第 504页,第 504页。。这种说法就一般来说是不很“精当”的。但就当时社会上新旧情况而言,却是很有道理的。李大钊特别针对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局指出,当时社会新旧真假难分,多种势力摇身一变都戴上了“新”的帽子以饰其“旧”。“全国之内,无上无下,无新无旧,无北无南,无朝无野,鲜不怀挟数副假面。共和则饰共和,帝制则饰帝制,驯至凡事难得实象,举国无一真人”③《李大钊文集》(上),第 551页,第 504页,第 512页,第 504页,第 504页。。这种无“实象”、无“真人”,多戴着“假面”的社会,怎么区分真正的新与旧?这样的“新”与“旧”,有什么本质不同?如“缓进派”的梁启超,“虽恒自居于新,其实当隶属于旧;虽恒自跻于进步,其实当归纳于保守”④《李大钊文集》(上),第 551页,第 504页,第 512页,第 504页,第 504页。。所以“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属旧者亦未必无新也”⑤《李大钊文集》(上),第 551页,第 504页,第 512页,第 504页,第 504页。。李大钊还认为从事物的发展、传承与更新过程看,新旧事物在由旧变新的过程中,总是新旧交织在一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昨日是新,今日可能是旧。反之亦然。如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代,人人都嫌他太新;可辛亥革命后,他又转向保守,成了旧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李大钊所说新旧无质差别的话,是专有所指的。过去,我们对新旧事物关系有一种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认为新就是新,旧就是旧,把两者绝对化;并只强调质的区别,忽视量的变化,以致一碰到李大钊说新旧无质的差别时,就予以否认,并把它与“调和论”一起打入“在理论上坠入了社会进化与政治改良的泥坑”的冷宫,结果犯错误的是自己。
二、关于“互助论”
五四运动前后,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与主张物种进化不是靠竞争而是靠互助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社会广泛流传起来,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五四”前,生物进化论在思想界占上风;“五四”后,生物“互助论”则强劲传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已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于 1919年 7月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阐述了他关于“互助论”的思想。对这一思想,我在书中总把它归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予以较多否定,并认为“这种‘互助论’思想成为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沉重负担,影响了他迅速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261页)这种说法是极不妥当的。首先应肯定社会互助思想有其积极意义。李大钊关于“互助”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机”、“依互助而进化”的观点是科学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生物的生存与发展中,竞争很重要,没有竞争就没有物种选择,就不能保证物种有力的发展。但生物的互助更为重要,如果没有互助,种群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既有竞争又有互助,物种才能获得发展的平衡。竞争与互助是生物进化的两个基因,缺一不可。这是物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李大钊批判了那种生物进化只有竞争没有互助或只有互助没有竞争的片面观点,并特别强调“互助”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过去,我们总是认为这种互助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中国先进分子把这种思想拿来用于爱国运动中,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很多“五四”青年,就是在“互助”的旗帜下,发动起来,团结起来,建社团,办刊物,搞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小的社会进步潮流。李大钊的“互助论”思想,是与这股进步社会潮流一致、并汇流在一起前进的。可我在书中却把李大钊这种总强调“互助”对生物与人类的重要意义的思想,看成是“流露”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第268页)。
1.关于“互助”、“协合”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对“互助”思想的界定非常明确。他是把它规范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与道德范畴中的。他提出要把“互助”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中去,并要建立一个“互助的理想”社会,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⑥《李大钊文集》(下),第 16-17页,第 16-17页。。在李大钊心目中,“互助的理想”社会、“互助生存的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⑦《李大钊文集》(下),第 16-17页,第 16-17页。。在这里,李大钊明确把“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看做社会主义的“基础”、“根萌”、“法则”、“精神”,这就揭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李大钊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协合”的社会主义、“友谊”的社会主义、“互助”的社会主义、“博爱”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认识虽然把社会主义限于伦理道德方面,但却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对这一可贵思想,我却把它也归之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所致。
2.关于“人类之爱”思想。与“协合”“互助”社会主义思想相联系,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经常提到人类之爱,强调“爱”的意义与重要性。他认为“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能爱人,人必爱我”。“人间共同生产的关系……即是以爱为基础的”①《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他把这种“博爱”思想作为他要建立的“互助”社会的思想基础,并认为“爱人”就是社会主义道德。1918年 7月,他在《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②《李大钊文集》(上),第 573页。。他确认“爱人”是社会主义精神与道德。他又把“爱人”与“互助”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③《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互助”就要“爱人”;“爱人”才能“互助”。在这里,李大钊又把“爱人”与“互助”一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特征,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认识的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也是与我们今日所提倡的“爱人”精神相一致的。可是,我在书中却把这一“爱人”思想与资产阶级“博爱”观联系起来,反说李大钊把这种“爱人思想与资产阶级博爱观相联系”,“在客观上只能起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消极作用。”(第269页)而忽视了李大钊关于“爱人”、“互助”道德的论证,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④《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相对立的。
3.关于“互助”与阶级斗争。过去在我的潜意识里,似乎一提“互助”就是“只能起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第269页)。其实这是绝大的误会,是强加在李大钊身上的“欲加之罪”。实际上李大钊是把“互助”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谈的。他的《阶级斗争与互助》一文,就是阐明两者之间关系的。他在阐述“互助”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同时指出,“互助”理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才会真正实现互助。他说“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失,不过因它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⑤《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李大钊在这里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现在革命的“大变化”、“大洪水”,就是要“把从前的阶级竞争的世界洗的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觉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免的”。所以他在上述文章的最后高呼:“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⑥《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可见,李大钊在谈他的“互助”思想时,他的阶级斗争观念是非常明确的,绝不是像我所说的是“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
三、关于“物心两面改造论”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⑦《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对这一思想观点,过去我在书中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这贬低了阶级斗争对改造人类精神的作用,似乎“阶级斗争只能用来改造社会物质,而不能用来改造人类精神”;“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对精神改造的作用,具有唯心论成分”(第276页)。
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的“物”与“心”是互相联系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更没有贬低阶级斗争的作用与夸大“互助”精神作用的意思。在李大钊思想中,“物”“心”“两面”,是密不可分、互相配合的。1919年 5月,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物心两面改造论”又做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⑧《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物”的改造是社会主义——组织改造论——社会革命;“心”的改造是人道主义——人心改造论——道德革命。这两种革命,即物质的和精神的革命,既有区别,也是“一致”的。“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⑨《李大钊文集》(下),第 96页,第 67页,第 152页,第 67-68页,第 18-19页,第 18-19页,第 49页,第 68页。。所以李大钊反复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中的“两面”也决不是地位平等的,而是“物”决定“心”,“心”随“物”变。李大钊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解释说,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构造,都是社会“表面”的构造。在它的下面,有经济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①《李大钊文集》(下),第 37页,第 43页,第 68页,第 43页。。大量事实证明,“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它永远不能实现”②《李大钊文集》(下),第 37页,第 43页,第 68页,第 43页。。随后,李大钊发表了有名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系统地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一步强调了物质构造的决定作用。
但是,李大钊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精神构造的作用。相反,他还极为重视精神改造的重要意义,认为物质构造的变动不能完全解决精神构造的改造。他说:“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动”③《李大钊文集》(下),第 37页,第 43页,第 68页,第 43页。。他又指出,精神改造运动就是要“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得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时期,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变动,人心内部的恶,若不铲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④《李大钊文集》(下),第 37页,第 43页,第 68页,第 43页。。
李大钊以上关于“物心两面改造论”的论述,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精神对物质又起反作用的原理。李大钊在强调物质改造的同时,重视精神改造、人心改造、道德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五四时期很有意义,就是在今天仍有其历史价值。今天经济上去了,但人们的道德滑坡了。所以我们不断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与李大钊当年强调的“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思想是一致的。
四、后语
在作了上述反思后,我也并不否然李大钊思想确实受过某些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其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过程。但我的问题是,对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中某些旧思想的残留,是戴着黑眼镜,专挑毛病,夸大其词,上纲上线,实在是对革命先烈大为不敬!今谈及此,实感惭愧。
一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往往会带上时代的烙印;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时代的历史观。我开始研究李大钊思想,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 1977年。出于对“四人帮”污蔑李大钊是什么“民主派”的义愤,要发掘李大钊思想的革命精华,并让其发扬广大。但那时,“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其思想流毒还没来得及清除,充斥社会的仍是猖獗一时的极左思潮。这时,我满脑子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形成了“阶级斗争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阶级斗争”的错误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包括我自己)一直把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念,当做神圣教条,并把它绝对化,排除其他社会元素的历史作用,逐渐把“阶级斗争观”嬗变为“唯阶级斗争观”,在这一历史观统制下,中国历史成了一部革命史、一部“阶级斗争教科书”。“言必谈阶级,书必写革命”,“见封建就批,见地主就骂”,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潜规则。在这里,历史主义不见了,封建阶级即使处在历史上升时期也是反动的,新王朝建立初期实行的所谓“让步政策”,是比赤裸裸的残暴统治还要坏的政治欺骗。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更是恨之入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等,统统在排斥之列;引进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被骂为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以致出现“见洋就骂,见洋就批”的怪象。这些被称为“唯革命论”的论调,最大的理论错误,是把革命性与科学性、把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割裂,只要革命性不要科学性,只要阶级斗争不要历史主义。我长期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用这些错误观点去认识李大钊的“调和论”、“互助论”、“物心两面论”,焉能不犯错误?
长期以来,我也深受“两个彻底决裂”思想影响较深,把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作绝对化理解,认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与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就是要“一刀两断”,不“拖泥带水”;如果在思想深处还残留一些旧思想的痕迹,就是没有与传统观念作“最彻底决裂”。由此观察李大钊的“调和论“、“互助论”、“物心两面论”思想,就认为是没有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所致。这种认识是极其片面的。所谓一个共产主义者要与私有制观念、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那是从意识形态,从世界观讲的,是从立场、观点、方法讲的。也就是说,一个民主主义者要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他必须抛弃原来的民主主义观念与立场,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不是指要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等“彻底”抛弃。这里所谓的“最彻底的决裂”,我理解就是作“基本上决裂”。而实际上,从现实生活看,历史与传统、新与旧,总是连结在一起的,其内在联系是很难“彻底”割断的,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等,近代中国的革命者毫无例外地都是从这一传统文化中走过来的。当他们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后,他们并没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们血液里仍然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这种母文化基因是不可能与之“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出发,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如他们总是用传统“大同”思想来解释共产主义,从儒家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传统“中和”思想来加深理解与倡导今日的和谐社会建设,等等。他们总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传承下来,加以创新,为创建革命的新文化服务。再从事物发展规律看,旧变新,总有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完成。往往是旧中孕育新,新中必带旧。任何社会事物都没有绝对纯粹的。一方面,新的要求与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另一方面又不能割断历史,割断事物的内在联系。新与旧往往要在一定时间内同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中华文明的“和”文化,就是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一体”,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所以主张共生共存,和谐发展。这与西方主张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文化体系是不同的。再从我们今天的现实看,对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不一定要求他“同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也就是说,有私有制观念甚至拥有相当财富的人,并不一定会影响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心中装的是“大我”,用此财富为共产主义服务。所以,不能教条式地理解某些共产主义教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和当今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当今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于现实社会实践中。由此看来,在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中,要求他思想中不带有旧的杂质,是既不合理又不现实的。
在自己的治学思想上,也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例如,历史研究的一个原则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条件去苛求前人,甚至求全责备。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往往容易忽视这一条。如李大钊关于“调和论”思想,是他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时候的一些见解。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这些观点可算是很高的了。但我在评论他这一思想时,却往往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不分档,甚至以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谈论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似乎要求他在民主主义者时期就得懂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李大钊关于“互助论”的思想,那时他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他明确把“互助”思想放在阶级消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大框架中来认识。而我评价他这一思想时,却又不自觉地把它放在民主主义者时期的思想来看,认为这一思想不利于阶级斗争理论。这两种脱离历史的评价,都贬低了李大钊思想的高度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在运用过程中,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反而把它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就很容易使其走向反面,成为非马克思主义,或伪马克思主义。极左思潮严重时,人们被禁锢在伪马克思主义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搞的是伪马克思主义,还自认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悲剧往往就在这里发生。这是必须牢牢汲取的历史教训。
K25
A
1003-8353(2010)04-0129-06
吕明灼,男,青岛大学教授。论这一思想时,却错误地认为这是“片面夸大调和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与事物的发展规律”(第104页),似乎李大钊只强调“调和”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与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排斥事物的另一面—对立与矛盾,而这恰恰是被李大钊痛批的梁启超“伪调和论”的观点。
[责任编辑:翁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