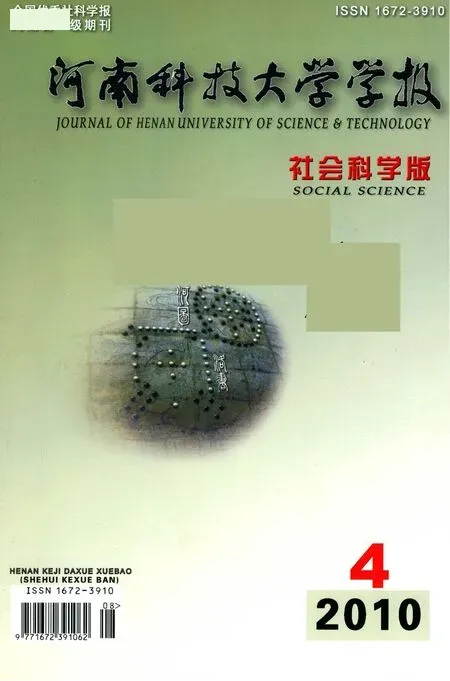还乡:延宕的心灵抵达
——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题材小说《中士还乡》
丁一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还乡:延宕的心灵抵达
——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题材小说《中士还乡》
丁一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从“还乡”维度考察阎连科的早期小说《中士还乡》,主人公“农民军人”的复合身份所暗含的角色冲突使其面临两难选择,企图以归根完成身份重拾却使得灵肉分离。这种还乡造成的心灵延宕不仅折射出作者早期创作中心态的矛盾与困惑,也预示了“还乡”精神线索在其后来作品中演变与转折的轨迹。
阎连科;《中士还乡》;当代小说
“还乡”主题自“五四”以来便常常出现在乡土作家笔下。鲁迅的《故乡》、沈从文《湘行散记》和师陀《果园城记》,都借“还乡”这一形式表达了不同的精神诉求。到了阎连科的小说中,“还乡”则更多地关注并暗示个体承受精神压抑乃至灵肉分离的矛盾与困惑。阎连科的早期小说多是基于生活体验的写实创作,其中农民军人题材小说又是颇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农民军人身份的复合与冲突、抉择与茫然以及灵肉分离式还乡的悖谬,在每一个侧面都透露出个体在精神压抑下的存在状态——而这正是阎连科“还乡”主题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中篇小说《中士还乡》作为农民军人系列的发端之作,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
一、背弃或皈依:农民军人身份之悖论
《中士还乡》发表于《时代文学》1991年第 2期,在阎连科作品体系中通常归入军旅小说系列。继以亲身生活体验为原型创作出的瑶沟系列小说之后,《中士还乡》可说是作者农民军人题材小说的发端。《中士还乡》同《瑶沟人的梦》等小说一样,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与反省。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逃离土地之后的主动还乡 (皈依土地)。主人公是个逃离土地参军的“农民军人”,这个双重身份中暗含了农民和军人两种角色的矛盾。当代的军营“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做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1]事实上,这样的复合特征注定了其中一种身份的渐渐消弭和另一种身份的加强,通常是“农民”这一自然身份被“军人”身份拥有的政治身份渐渐征服。换句话说,农民的土地根性被悄然吞噬。然而逃离土地的青年农民很少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残酷性,小说暗示了这一问题,仅从篇名就可以看出作家有意对自然意义上的土地之子身份的复归,它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指向对土地及其精神意义的回归。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人物回归土地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不是坚守的决绝,而是“延宕”的困惑。
农民出身的中士田旗旗厌恶了平淡得“像一碗水”的军营生活,放弃了入党和受奖的机会决然还乡。回到土地之后觉得依旧是“日子如水”,无聊到想帮邻家奶奶在村头追下蛋的鸡却被生生拒绝:回到乡村的他竟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多余人”。过分寂寞之后他觉得该找点事情做了,于是去妹妹家和入伍前换过亲的媳妇见面。一路上,作家以意识流手法呈现他的路上所见、对三年前与妹妹相依为命时的情景和对离开不久的营房生活的回忆,并运用倒叙及插叙手法在现实与回忆的场景间频繁切换。土地总在冷静下隐藏着残酷,三年前他父母“说死就死了,如出门赶集一般简单”,从此他既当爹又当娘。某天他在庄稼地里异常“口渴”时,看到远方有什么移来:
土道上移来一个绿点、绿圈、绿团儿。他以为那移动来的是一袋绿水,就呆呆瞅着不动,后见那绿袋儿上方有两片红光,心中一愣,跨到路上迎着,待那红绿靠近,他认出来了,那红绿是
一个人:他初中同学,十六岁当兵,回家休假。
老兵了,天哟![2]
这段叙述极富隐喻意味。旗旗在田地里辛苦劳作又要承担爹妈的角色照顾妹,辛苦乃至厌烦自不待言。“口渴”是一种极需要的状态,不仅指生理上的身体需要补充水分,更隐喻他内心迫切的需要。恰恰是渴极时,“一袋绿水”到来。他需“解渴”,“当兵”正好来救急,助他逃离土地,逃离庄稼地上劳苦。“农民”的身份转为“军人”,意味着受苦受累的命运得到改变,这对前者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于是“有点心动”、“心活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对旗旗而言,要离家 (土地)就要舍弃妹妹;要照顾妹妹就只能留在土地,“土地”与“妹妹”二者间画上了一个隐喻的等号,因而他对“逃离土地”或“坚守土地”的抉择,又关涉到对乡村传统价值观的坚守或背弃,选择“坚守土地”既是维护传统家庭的“长兄如父”的伦常道德、相依为命的亲情和土地上辛勤劳苦的品性。他抵挡不住“逃离土地”的魅惑,背弃了土地及其传统价值观。而作家设置中士“还乡”,可以断定是对土地和传统价值观的背弃之后的一次反省与皈依。
二、归根:身份的重拾
中士皈依土地的心理过程绝非顺水行舟般流畅,那是他朝向土地的一次延宕的心灵抵达。旗旗逃离土地后,他天然的农民身份被政治化、纪律化和符号化的军人身份侵蚀,军营中他的农民身份将退居幕后乃至渐渐消隐。中士去当兵原指望能立功入党有出息,他在部队表现勤快,人缘又好,“本来是可以立个功的”,但恰恰难得的一次立功机会他错过了。那是一个晚上,中士抓到了盗窃部队铁丝网的一对父子贼,正要去报告排长,老汉拉住他的手求情:“敢问小兄弟,你也是、农村人吧?”并乞求他“是农村人就该知道庄稼人活在世上的艰难,就不该把他们关在这”。中士疑惑自己的农民身份如何被发现,老汉一语道明——“庄稼人的指头都又粗又短,关节老宽”。于是,他放了他们。
农民身份从他并不拢的五指缝泄露无余。军人中士因这场意外重新发现并确认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土地根性,他为自己并不拢的五指,更为“庄稼人活在世上的艰难”而“悲哀”。他本以为对庄稼人活在世上艰难的同情可以被“一个排的兵都是从农村来”的军营谅解,老老实实向排长汇报后,却被一句“你真他妈农民”骂了个懵懂,只好以自己的农民出身来央求排长“你下过乡……该知道庄稼人的苦”。排长的回答却进一步强化“军人”身份对“农民”身份的绝对压迫和威严:“我是军人,你他妈的也是军人”。至此中士第一次感到两个身份在他身上水火不相容般无法调和。参加演讲团这一情节出现后,他两个身份的裂隙开始渐渐扩大。作家决意要在情节的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让中士剥离“军人”身份而皈依土地,小说中多次出现中士对土地的憧憬和迷恋便是例证。中士在立功入党的节骨眼上突然决定退伍,面对指导员晓之以理的挽留他无动于衷,脑中只是闪过这样一幅诗样美丽的乡村画面:“远处风光清爽,落日恋着山坡,碧绿的玉蜀黍苗挂在田里,锄地的男女,在苗间横着。”[2]返乡后“拔草”的场景则是中士与久别后的土地来了次亲密接触。泥土飞溅到脸上,且看他的反应:
有粒黄土粘着嘴唇不肯落下,他就用舌头勾进嘴里,嚼了,胶着他的上下牙齿,品出一股很鲜很鲜、有很香很香的泥味,他就猛然僵着不动,用舌尖去牙缝挑着化开的泥土。[2]
此时的中士震惊地发现了土地之美,泥土的香甜让他陶醉。在这猛然的发现中,他意识到了根之所在。高高在上的叙述者也忍不住要跳出来替他发言:“眼下,中士想成为一个庄稼汉子。”
三、灵肉分离式的还乡
“妹妹”成为土地的隐喻之后,当主人公以“中士”身份返乡去妹妹家将换过亲的媳妇娶回家时,也昭示着他重新拾回并确认自己的农民身份的意味。中士憧憬着成为庄稼汉子,彻底甩掉“农民”之外的身份压迫,但这一切努力都在作者的笔下被证明为虚无,而土地上的纯美的气象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回忆里。三年前,中士妹妹十七岁,正是水灵灵的年龄。三年后,中士返乡再见到妹妹时发现她老了许多:
她的腰脊真弯了,些微地,隔着她的单布衫,能觉摸出她的腰脊节,一凸凸、一凸凸,如胡同路上的泥峰。[2]
日子可以将一个人打磨,土地又何尝不是?已经很难说土地还是三年前庄稼地上的农民旗旗眼中的土地了。从他与妹夫陈饼子见面的场景中,我们更近距离地看到中士“农民军人”身份与陈饼子纯粹“农民”身份之间的裂隙:
闲谈几句,彼此就没更多话讲。中士初见陈饼子,着实吓了一跳,三年不见,他忽然苍老了许多,算来长中士两岁半,无非二十六岁,可似乎已三十有五,脸上的纹路、肉色都如是一个黄土世界。看着那张脸,仿佛能看见人的晚年,很叫人感到岁月凄哀,光景难熬。[2]
然而,断裂还不仅仅来自身体上的巨大差异。土地上积累三年的劳苦可以将人脸写成一个“黄土世界”,照出“岁月凄凉”,更可以将有着两个不同身份经历的个体生生隔断在一堵无形的精神墙壁两侧。中士与陈饼子之间的交流屏障仅当说起“庄稼、土地、气候”这些庄稼人话题时才被打破,两个人这才有了交流共同点,问问答答很能谈到一块。这,对于执意选择剥离军人身份回归土地当农民的中士,是喜还是忧呢?土地上的凄凉难熬,还有当年与中士订婚的那个自始至终没有在小说中出现的陈饼子的妹妹,已跟随了一个有钱有权的人家不愿再回来,此时此地他又无依无着。离去时正是落日时分,中士心想“又过了一天,若还在弹药库,该是吹哨吃面条的时候了”。“还乡”居然又回到了原点,如同一次无意义的徒劳之举。他对根的皈依、对身份被吞噬的反抗,既显得无力又被证明为荒谬。联想到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要推着一块大石到达陡坡顶端,然后眼看着它滚落到山脚下,再重新开始向上推——难道作家有意向我们暗示西西弗斯的大石才刚刚被推上陡坡的顶端?
也许这一结局投射了作家本人亲历过的无奈。考察阎连科经历可发现,他塑造的中士形象,背负着作家本人因从军而离乡弃土带来的心灵挣扎和切身感受着的漂浮感,真正意义上的“还乡”又何尝不是一个时时折磨他的泡影。在一部小说的后记中,阎连科透露了他多年的心迹:“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漂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距离,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3]于是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总表现出心灵无处安放的漂浮感,他们对土地有执拗的眷恋,对曾经的逃离行为报有深深愧疚,一朝还乡却又被深深的虚无感笼罩,沦为在土地上徘徊的“多余人”。
身已抵达,心却无归。“农民军人”灵肉分离式的还乡造成延宕的心灵抵达,即心灵的徘徊无着迟迟难归。有根的写作者常常经历这样的痛苦:“诗人那里有两个家,一个家在故乡,叫‘出生地’,一个家在心里,叫‘异乡’,诗人的写作,是在这两个家之间的奔跑和追索,不可能离开,也不可能回去。”[4]阎连科与有根的诗人一样执着的是,心永远在两个家之间奔跑与追索。还乡,是从“异乡”逃离奔向他遥远的土地,心灵在这场劳顿的奔波中难免疲惫,难免徘徊、迷失。《中士还乡》深深烙上这一象征困惑与矛盾的精神印记,成为阎连科前期作品的一块里程碑,及至后来创作出《寻找土地》等一批小说,个体与乡土之间关系的转折方才揭开序幕。作家开始寻找能够安放心灵的一方土地,最终发现心灵的路标径直指向那一片广袤的耙耧山脉。
[1]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J].文学评论,1994(5):42-51.
[2]阎连科.中士还乡[J].时代文学,1991(2):52-191.
[3]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28.
[4]谢有顺.文学的常道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9.
Return ing Hom e:A Delay ing A rr iva l of the Hear t:Yan L ianke’s Novel“The Sergean t’s Return ing Hom e”
D ING Yi
(L itera ture Schoo l of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123,China)
To study Yan L ianke’s early novel,“The sergeant’s returning hom e”,from the dim ension of returning hom e,ro le conflictswhich imp licated in peasant soldiers’composite identity m ake the p rotagonist face the dilemm a of choice,but the attemp t to comp lete identity restoration by returning hom e has lead him to the separation betw een his body and sou l.The m ental delay w hich caused by returning hom e no t on ly reflects the m entalit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usion in Yan L ianke’s early wo rks,but also indicates the trace that the sp irit c lue of returning hom ewou ld evo lution and change in his subsequent creation.
Yan L ianke;“the sergeant’s returning hom e”;contemporary novel
I206.7
A
1672-3910(2010)04-0044-03
2010-04-12
丁一 (1987-),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