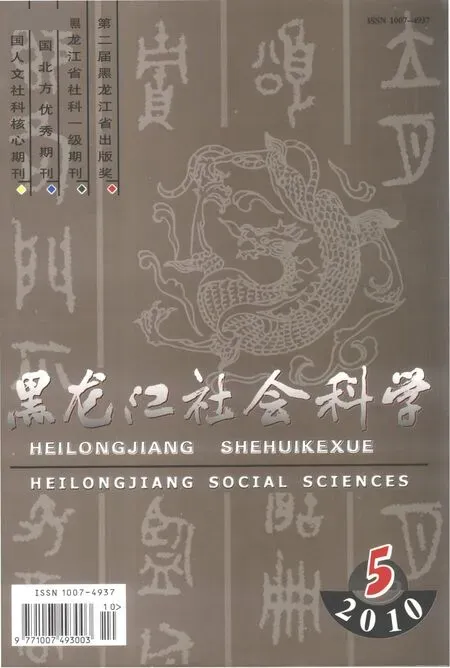徐陵的佛教活动考述
黄 颖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徐陵的佛教活动考述
黄 颖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徐陵,梁、陈著名文士。他奉佛受梁陈之时代风气与其家学风尚的共同影响。入陈后,徐陵更以士林领袖和文坛宗匠的影响力推动和促进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徐陵的日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都体现了他对佛教的精神信仰,以及不俗的佛学修为。
徐陵;梁陈佛教;佛学造诣;精神信仰
徐陵 (507—583),字孝穆,祖籍东海郯县,西晋末年举族迁移至江左京口。作为文学家,徐陵在文学史的纵横坐标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其诗文不但泽被其时之南北文坛,对隋唐以后的文学亦有影响。徐陵由梁入陈后居于士林领袖地位,在陈朝政坛和士族中有不小的影响力。徐陵对佛教的信仰早始于梁朝,并贯穿其一生。入陈后,徐陵以其一代文宗的影响力、开国重臣的地位和声望,促进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变化,表达其对佛教的支持和信仰。
一、徐陵崇佛之时代背景
徐陵生活的梁、陈两代,佛教大行于世。上至君王贵戚,下至贩夫走卒,崇佛之风盛兴一时。受时风淫浸,东海徐氏也表现出崇佛之家学风尚。
徐陵奉佛首先为时代风尚使然。佛教于中国之传播、兴盛,魏晋世族可谓居功至伟。魏晋之际,儒学式微,老庄兴起,佛教遂乘此中华学风转变之机挟其精深广博之义理,于士林中扩大其影响。其时名僧支道林、支孝龙、康僧渊等“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1]163,遂为琅琊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等膏腴之家群加激扬。南朝之世,玄学与佛学合流,名士与名僧交往仍为阀阅之家所奉行。南朝君主或起自布衣,或为寒族,虽掌握国家政治、军事大权,但在文化学术上仍唯世族马首是瞻。南朝历代统治者及王室大倡佛教、结纳高僧、修习佛典,既为融入士族文化之需,亦是利用佛教巩固统治。于南朝佛教发展最有力者当属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朝诸帝和陈朝诸帝。萧子良盛集高僧于官邸,遂有审音考文之盛事。梁武帝萧衍之佞佛已为世人熟知,其在位四十八年,建佛寺,度僧众,开法会,持戒律,亲自注经、讲经、译经,四次舍身同泰寺,可谓君主佞佛之极致。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受其影响,自诸侯起即崇佛有加。陈朝诸帝亦崇信佛教,陈武帝不但多兴佛事,且效仿梁武帝舍身之举。宣帝、后主也多召集名僧开讲佛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时社会风尚可想而知,这点已多有学者论述,此不赘述。
徐陵崇佛,还自有其家学渊源。陵父徐摛对佛教的信仰,及其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于传记中可窥一斑。《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记载:“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2]325宝志禅师、光宅云法师乃梁朝名僧,由“每”字可知徐摛与其时义学名僧多有往来。据《梁书》卷三十《徐摛传》载,梁武帝因徐摛创作宫体而召其责让,“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3]447。徐摛能因祸得福,除了“称职”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佛义的熟悉、精通深合梁武帝心意。徐摛还主持建造灵泉寺,参与佛教类书《法宝联璧》的编纂。
徐陵三弟徐孝克的笃佛行为更为明显,其传附于《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徐孝克梁末侯景之乱时,“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2]337,后还俗。入陈后,徐孝克以居士操行自处,“蔬食长斋,持菩萨戒”[2]337。徐孝克于佛教义理有一定造诣,他在钱塘“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2]337。徐孝克出家、持戒、讲经的诸多行为足以表现其敬佛程度之深与佛学修为之高。而徐陵之子徐份、徐仪亦有焚香礼佛、结遇僧人、研习佛经之举。东海徐氏一族,自徐摛起,至徐陵、徐孝克兄弟,再至陵子徐份、徐仪俱与佛教颇多关联,可谓三世奉佛。东海徐氏之表现可视为梁陈士族世代崇信佛教、精研佛理之典型。
二、徐陵与梁、陈僧徒之交往
徐陵的奉佛行为主要有结交名僧、研讲义理,相关记载多关乎其入陈之后。徐陵与梁、陈两朝僧人多有交往,如慧因、真观、智顗,其中最著名者非天台宗创始人智顗莫属。
1.徐陵与智顗
徐陵日常多与僧侣交游,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与天台智顗大师 (538—597)的交往。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六《智顗传》记载:“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字德安,姓陈氏,世为颍川人。”[4]180梁承圣三年
(554),智顗约十七岁,于湘洲果愿寺出家。后入北,投光州大苏山慧思门下。北齐天统三年,即陈废帝光大元年 (566),智顗奉其师慧思之命前往建邺弘法。陈废帝光大二年 (567)至陈宣帝太建七年 (575),智顗以北地法师的身份在建邺开展活动,徐陵亲见智顗应始于此时。智顗门人释灌顶撰《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对徐陵崇信智顗一事安排了一段奇异的因缘:“仆射徐陵,德优名重,梦其先门曰:‘禅师是吾宿世宗范,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训,资敬尽节,参不失时序,拜不避泥水。若蒙书疏,则洗手烧香,冠带三礼,屏气开封,对文伏读,句句称诺。若非微妙至德,岂使当世文雄屈意如此耶!”[5]191如按灌顶之说,徐陵于智顗的态度缘起于亡父徐摛的梦中教导。这自然是为神异一代文宗与天台祖师的交往附会因缘前定之说。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云:“顗便诣金陵,与法喜等三十余人在瓦官寺,创弘禅法。仆射徐陵、尚书毛喜等明时贵望,学统释儒,并禀禅慧,俱传香法。欣重顶戴,时所荣仰。”[4]564又《佛祖统纪》卷二三言:“四祖顗禅师,于金陵瓦官寺为仪同沈君理、仆射徐陵等开《法华》经题,一夏开释大义,白马敬韶等咸北面受业。”[4]247智顗至金陵,受请驻锡瓦官寺弘法,主要是开讲禅法和《法华经》。徐陵于瓦官寺得受智顗教诲,深感智顗在佛学上的造诣高妙,故生虔敬之心。《佛祖统纪》卷二四即将“仆射徐陵”列于“四祖天台智者大禅师”[4]250世系之下。南宋释宗晓所编《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录北宋李沆《净光法师赞》有言:“徐陵师顗,道以尊贤。”[4]927可见,徐陵出于崇奉对释智顗乃执弟子之礼。
陈宣帝太建七年至陈后主至德元年 (583),智顗隐居天台山。此间,徐陵与智顗交往一要事是徐陵向陈宣帝请诏为智顗建寺,并赐法号。据《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载,太建七年九月,智顗欲离开金陵,入天台静修,“陈宣帝有勅留连,徐仆射泣涕请住”[5]192。徐陵曾极力挽留智顗,智顗也应其所请,勉为淹留一夏,后终成行。智顗入天台之后,身在京城的徐陵请求陈宣帝为其立寺天台山,并赐予法号。释灌顶纂《国清百录》卷一“太建十年宣帝勅给寺名第十”条云:“具左仆射徐陵启,智顗禅师创立天台,宴坐名岳,宜号修禅寺也。五月一日臣景历。”[4]799唐毘陵沙门湛然述《止观辅行传弘决》亦记载此事道:“尔后勅赐寺额云:‘具左仆射徐陵启,知禅师创立天台,宴坐名岳,宜号修禅。’”[4]148智顗隐居天台是为寻求一空间研习义理,并为创立宗派做准备,这也是天台宗创始的重要阶段。智顗能获朝廷为之立寺、赐号,固然是由于其佛学修为之杰出,但徐陵为其在朝野奔走呼吁显然也是一要因。徐陵对天台宗之创立甚有力焉。
陈后主至德元年末至陈后主至德二年 (584),智顗得徐陵力荐重回建业,于光宅寺讲经说法。智顗于太建七年入天台山,远离京城。其再至金陵,又得徐陵之力。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载其事:“陈少主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徐陵对曰:‘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鉴渊海。昔远游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霭,永阳王北面亲承。愿陛下诏之还都弘法,使道俗咸荷。’”[6]193徐陵以智顗为“释门名胜”,对其佛学修为与宗师风范推崇有加。而陈后主因徐陵之言,遂七下诏书,将智顗迎回金陵。智顗复得弘法京城,徐陵也得以重聆其教诲。
徐陵于日常之中,也多与智顗音信相通。灌顶纂《国清百录》卷二收录徐陵致智顗书信四通,题为“陈左仆射徐陵书第十九”,原注言“陵书最多,门人竞持去,追寻止得三纸并愿书”[4]801。徐陵是其时俗众中致信智顗最多的人,后多散佚。正因为与智顗之密切交往,对天台宗创立之贡献,及其以一代文宗、士林领袖身份崇奉智顗而造成的影响力,徐陵被敬奉为天台六祖智威禅师前身。
2.徐陵与其他僧人的交往
梁武帝天监六年 (507)至天监十三年 (514),徐陵与释宝志有交往。据《观音慈林集》卷《感应一·宝志大士传》记载:“宝志大士,俗呼为志公……初金陵东阳民朱氏之妇,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大沙門僧俭出家,专修禅观,至是显迹。”[5]93宝志活跃于齐梁,行事纵诞,出言成谶,相关记载多神异其事。梁武帝对宝志颇为推崇,敕其出入宫廷。天监十三年,宝志于建邺无疾而终。《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载:“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2]325
梁武帝天监六年至中大通元年 (529),徐陵与光宅云法师交往。《续高僧传》卷五《法云传》云:“法云姓周氏,义兴阳羡人。母吴氏,初产坐草,见云气满室,因以名之。七岁出家,更名法云。”[4]463法云在齐代即已擅名,与其时贵胄王融、徐孝嗣、周颙多有交游;入梁后,受梁武帝钦礼,梁天监二年 (503)入主光宅寺。“以大通三年 (529)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4]465。据《法华经义记》所附《法华经义疏序》云:“爰至梁始……开善以《涅槃》腾誉,庄严以《十地》、《胜鬘》擅名,光宅《法华》当时独步。”[4]363云法师为梁代的《法华》巨匠,“法门博赡,道俗所归”[5]128。《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载:“光宅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2]325
陈宣帝太建十年 (578)至陈后主至德元年,徐陵与释真观有往来。释真观 (538—611),为陈、隋时僧人,《续高僧传》卷三十《杂科声德篇》有传。据《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记载,真观为钱塘人,曾在江宁兴皇寺开讲,为兴皇法郎门下,精于三论。真观声名盛于陈代,时人语曰:“钱塘有真观,当天下一半。”[4]701陈宣帝太建十年,始兴王叔陵任扬州刺史,慕名邀真观至金陵,此盖为徐陵亲见真观之始。徐陵与真观的交往,可由真观致书徐陵一事略加推断。陈宣帝太建十年,吴明彻北伐兵败,朝廷兵员损缺,有议从僧人中括兵者。佛门因此扰动,真观致书时为左仆射的徐陵。《续高僧传》本传记载其事曰:“于斯时也,征周失律,朝议括僧无名者休道。观乃伤迷,叹曰:‘夫剎利居士,皆植福富强。黎庶厮小,造罪贫弱。欲茂枝叶,反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则亡身在法。’乃致书仆射徐陵,文见别集。陵封书合奏,帝懔然动容,括僧由寝。”[4]702真观既膺时名,为解法难而毅然致书徐陵。此书具载于《广弘明集》卷二七,题为《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书》。徐陵得书,即上奏朝廷,僧难终得以消解。
至德元年前,徐陵与释慧因交往。慧因 (539—627),《续高僧传》卷一三《义解篇》有传。《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因传》载释慧吴郡海盐人,俗姓于 (或谓姓干),历陈、隋、唐三朝。十二岁出家,后从建初寺琼法师学成实论。复从钟山之慧晓、智瓘学禅定法,继从长干寺智辩学三论。《续高僧传》卷一三《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因传》言其:“穷实相之微言,弘满字之幽旨。写水一器,青更逾蓝。”[4]522足见其高超的佛法修为。本传记载其与徐陵之往来:“陈仆射徐陵,高才通学;尚书毛喜,探幽洞微,时号知仁,咸归导首。”[4]523以慧因之高才硕学,吸引徐陵,使陵归礼可谓夙识相通。然慧因陈朝活动的记载甚少,其与徐陵交往的时间和具体情形已难确考。
徐陵因其父徐摛之故,自幼即与梁代名僧释宝志、光宅云法师结识。此虽非徐陵主动,却实为徐陵与佛教因缘之始。徐陵因天资聪慧颇受宝志、云法师赞赏,名僧对徐陵风神之褒扬极类于名士品题人物。可见,时至梁朝,佛教僧徒与士族子弟之交往仍效名士风流。入陈后,徐陵与其时义学名僧亦多往来,且当陈朝佛教界面临僧难时倾己之力,极力周旋,足见其在陈朝的地位,以及对佛教之崇奉与热忱。
三、徐陵的佛学修为
徐陵于佛典之精熟亦可从其文中窥知一二。许逸民《徐陵集校笺》收录了徐陵所作《四无畏寺刹下铭 》[6]200、《报德寺刹下铭 》[6]191、《东阳双林傅大士碑 》[6]1224、《孝义寺碑 》[6]1190、《长干寺众食碑 》[6]1207,以上所列诸作中除《长干寺众食碑》成于梁代外,皆作于陈。这些公文皆为徐陵代君主立言、润色帝业的应制之作,虽与佛教有关,但实难由此考察徐陵的佛教思想。但徐陵于行文中对佛教理论、佛经典故信手拈来,对朝廷佛事极尽渲染之能,足见其对于佛教典籍之精熟。
从徐陵的日常活动来看,徐陵不仅谙熟佛典,且精通佛义。《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言:“(徐陵)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座莫能与抗。目有青睛,时人以为聪惠之相也。”[2]335《大品般若经》乃鸠摩罗什在姚秦时 (403—404)所译,为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对中国佛教影响至深。六朝佛学之根本特征为玄佛合流,徐陵少而精通《老》、《庄》,亦善《大品般若经》,其在讲论《大品经》时出入于玄佛之间应是必然。佛教讲经例有论辩,徐陵复能于论辩之时独擅其义。由此可知,徐陵既有名士谈玄之风神,亦有高深的佛理修为。汤用彤先生对此亦有论述:“徐陵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后主在东宫,陵为讲《大品经》。义学名僧,群集讲筵……原夫文人与僧徒之投契,当时不只在文字之因缘,而尤在义理上之结合。徐孝穆钦仰天台智顗,江总持尊重兴皇法朗,均于其学问上有所心折。”[1]425-426
既然论及徐陵对智顗学问之折服,义理之契合,就不得不提及梁陈之际南北佛学交流。由于南北政权对立,佛教在中古的发展呈现出地域性差异。汤用彤先生对南北佛教的特征概括为:南统重义理,北统重禅修,这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随着北魏孝文帝汉化,以及梁代开始逐渐频繁的南北文化交流,这一格局被逐渐打破。北朝僧人多有精于义理者,而北方禅定之法也开始南传。《止观辅行传弘诀》评价智顗证得“法华三昧前方便”,列其为“禅定第一”[4]145,可见智顗于北朝禅法之精深造诣。此外,智顗与其师慧思还重视义理之研解,倡导定慧双修[7]。智顗与慧思的观点是对南北佛学的批判与融合,体现了南北佛学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新趋势。据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云,智顗在建邺的主要活动之一为“创弘禅法”[4]564,徐陵与毛喜等“并禀禅慧,俱传香法”[4]564,则徐陵对智顗阐扬之“禅”必有修习。此外,陈宣帝赐智顗天台之寺庙号曰“修禅寺”,可见智顗至南朝后对宣扬禅法用力之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其时统治者与士族的肯定。《妙法莲华经》为后来天台宗所依之根本经典,智顗入陈后数次于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徐陵亦与讲席。由此推测,徐陵一生的佛学修为,经历了从最初的玄释兼通到后来渐趋于定慧双修的改变。这正是南北朝后半期学风交流、思想整合之趋势使然。
徐陵文章中亦不乏敷演佛理,体现其佛学修养的文字。其《与李那书》约作于陈文帝天嘉二年(561),此书是致北周李那,与其交流文章创作的心得。文中大量使用佛教典故,“至如披文相质,意致纵横,才壮风云,义深渊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归,皆逾火宅。宜阳之作,特会幽衿,所睹黄绢之词,弥怀白云之颂。但恨耆门远岳,檀特高峰,开士罗浮,康公悬溜,不获铭兹雅颂,耀彼幽岩”[6]830。“二乘”指声闻乘与缘觉乘。《法华经》有“二乘成佛”之说,此说谓修得二乘也有成佛的可能,为《法华经》前十四品的中心思想,这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8]。“化城”语出《法华经》卷二《譬喻品》,为法华七喻之一。化城,指变化之城邑,比喻二乘涅槃,与“二乘成佛”同义。“火宅”语出《法华经》卷二《譬喻品》,乃喻迷界众生所居住之三界。众生生存于三界中,受各种迷惑之苦,然犹不自知其置身苦中。徐陵用佛教徒之智慧开悟,脱离迷障,得道涅槃来形容自己对“文质相宣”创作宗旨的体悟。徐书中“二乘”、“化城”、“火宅”皆出《法华经》,徐陵对《法华经》之谙熟、精解正符合其与智顗过从甚密、得其衣钵之事实。徐陵在陈废帝光大元年 (567)朝任吏部尚书,整顿选举,他在《答诸求官人书》中道:“若见问尚书何不分判用与不用,许与不许?仆答云:君非屈滞,岂可相期决言应果……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属,门户相似,人才不殊,选家斟酌,无能为尔。若涉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宾用,并是前缘……此则清阶显职,不由选也。自此而论,岂非前业……仆六十之岁,朝思夕计,并愿与诸贤为真善知识,曾无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诉。”[6]914-915“应果”即应,译作阿罗汉果,即应受人天供养的意思。徐陵以此比喻士人所求之官禄。“善知识”指正直而有德行之人,又指善友、亲友、胜友,徐陵文中应用后一说。徐陵此文完全是一副政治家兼佛教徒的口吻,他不仅论述了整顿吏治的切实必要性,还用佛教果报、因缘之说来解释贵贱、清浊之别,以消泯寒族庶人之不平。
徐陵对佛教的信仰,亦出于其俗世精神的寄托。《徐陵集校笺》卷八所录徐陵《五愿上智顗禅师书》曰:“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笼,无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愿力庄严。一愿临终正念成就。二愿不更地狱三途。三愿即还人中,不高不下处托生。四愿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愿不堕流俗之僧。凭此誓心,以策西暮。今书丹欵,仰乞证明。陵和南。”[6]1015这是徐陵向智顗发愿,临死能离别诸邪念,如实忆念诸法之性相;死后不经地狱三途;能轮回为人,得不高不下处托生;转世为人后,能年少出家;作一守戒脱俗的高僧。就此五愿而言,可见两点:其一,从徐陵愿“童真出家”、“不堕流俗之僧”等语来看,徐陵对佛教戒律有所修习,对佛法更是虔心尊崇;其二,徐陵于佛教的寄托主要在于远离诸苦、邪念不侵,以清净心对待浊世人身,则徐陵发愿的终点仍是世俗人世。徐陵此种信仰在其《又与释智顗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难可敷具……弟子二三年来,溘然老至,眼耳聋闇,心气昏塞,故非复在人。兼去岁第六儿夭丧,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适今月中,又有哀故。频岁如此,穷虑转深。自念余生,无复能几。无由礼接,系仰何言。敬重璪公,今还白书不次。弟子徐陵和南。”[6]1003-1004此信应当作于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徐陵此时已年近八旬。历经宦海沉浮,阅尽人世沧桑,且家中频遭变故,这都使徐陵更有人生苦痛、世事无常之感。这也是促使徐陵皈依佛教、崇礼智顗的一大原因。
对于徐陵而言,其崇信佛教、精熟佛教义理是时代氛围造就的,也是其作为士族阶层必备之素质;而对佛教业报、因缘诸说的信仰,则是消释其人生痛苦与忧惧的必要途径,是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与融摄。这在风云变幻、荣辱不定的梁陈之世,也是士子的一种精神常态。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2] 姚思廉.陈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姚思廉.梁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大正一切经编辑委员会.大正藏新修大藏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 藏经书院.续藏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6] 许逸民.徐陵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42.
[8]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01.
K22
A
1007-4937(2010)05-0119-04
2010-05-15
黄颖 (1984-),女,江苏江都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时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