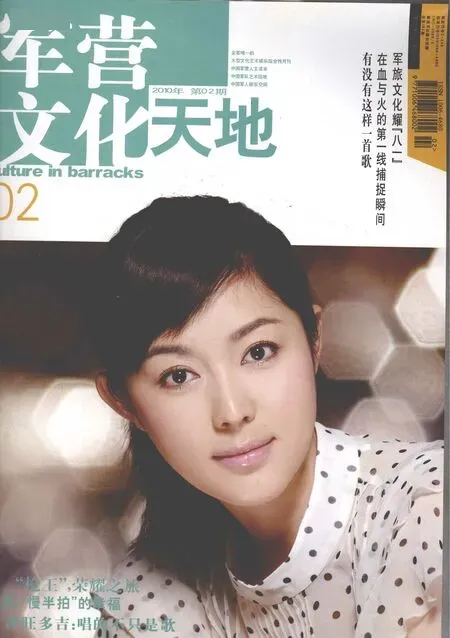在血与火的第一线捕捉瞬间
文/乔天富
《解放军报》的记者既要履行军人的使命,又要捍卫记者的职责。

我在《解放军报》当摄影记者已经32年了。军报记者既是军人又是记者,这个职业要求我履行双重使命。作为军人的使命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军人的生命属于祖国、属于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是军人的本分。记者的责任要求我们敏锐地发现新闻,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新闻事实,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摄影记者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充满挑战性是新闻工作的特色,绝对现场是新闻摄影的特性。经常直面危险是军人和记者的职业特点。30多年来,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践行军人的使命和记者的职责,也做成了一名《解放军报》记者应该做的事。
与水火天灾竞速
突发新闻是本质意义上的新闻,突发新闻摄影难度大,突发性新闻摄影体现着新闻摄影的本质特征。突如其来,难以预知,是它最大的特点,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决定了记者的拍摄难度。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置身于新闻现场,这是拍摄突发新闻照片的前提条件。突发新闻又往往与灾难、战争连在一起。抗震救灾、扑火救灾、抗洪救灾,解放军是主力军、突击队,这些突发新闻的现场,会自然产生鲜活新颖的新闻形象,是新闻摄影的富矿。军队的行动,为我们记者的工作创造了方便,我十分珍惜这种机会和条件。
1987年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1987年5月上旬,祖国北疆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我闻讯立即出发,先后乘坐火车、汽车、直升机,日夜兼程于5月9日到达黑龙江省塔河县第一线火场,成为首都新闻界第一个从北京赶到火灾现场的摄影记者。我不吃不喝不睡觉,拼命工作拼命拍照,冲洗、放大、写说明,快速发稿,成为第一个向北京发回独家新闻照片的摄影记者。5月15日,《解放军报》在首都各大报刊中率先以独家新闻的形式辟栏刊出一组题为《战火海》的新闻照片,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进行了转载。此次采访,我经历了熊熊烈火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头几天,没吃没喝没地方住,而危险也时时伴随我和官兵们,5月14日,我在漠河的原始森林中拍摄森林武警官兵扑火战斗,被大火包围,36小时断水断粮,后来是跟着森警官兵靠着指北针向黑龙江边突围得以脱险。

初上前线的“小”记者
面对熊熊大火,面对漠河县城的一片废墟和一具具烧焦的尸体,耳闻废墟上撕心裂肺的哭喊,灾难是如何造成的?谁应该对灾难负责?一个个问号在我的脑际盘旋。余烬旁,废墟上的灾民纷纷向我诉说5月7日大火洗城的惨状,控诉县长的无能和渎职,更引人注目的是废墟中县长住的那栋红砖房却完好无损。记者的敏感告诉我,当事的领导负有重责,是他们的官僚主义造成了这场灾难,而县长高保兴正是这个事件的头号新闻人物。在拍摄解放军英勇扑火的同时,我也暗暗地留心高县长的举动。5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到漠河灾区视察,在漠河县西林吉火车站桥头临时停机坪,边防团、森警、漠河县领导在等候副总理。9时整,一个精彩的画面出现了:人群中,高县长独自一人向着一边,用手抓着嘴,一副窘态。机不可失,为了不惊动县长,我对着左边的警察对焦后迅速向右甩动镜头,待高县长进入画面后旋即按动快门,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典型神态就凝固在底片上。《渎职者的窘境》这幅照片先后被数十家报刊发表。中央新闻媒体对大兴安岭火灾突发事件的报道,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推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新闻改革。
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雨雪冰冻灾害,我第一时间到达重灾区——湖南郴州。
灾害发生时正值新春佳节来临,大家都准备过年。我正在犹豫是陪妻儿去海南过年还是留在北京清静几天时,南方的灾害发生了。开始也不以为然,中国这么大,灾害年年有,下点雪,几天就过去了。1月31日,我坐不住了。中央政治局开会部署救灾。京广铁路、京珠高速不通。职业敏感告诉我,应该出发!
我搞到了一张2月1日由北京至长沙的机票,边报告领导边直奔机场。此时长沙正降大雪,飞机晚点两小时于19时起飞。快到长沙上空时,机场关闭,转飞桂林。在桂林机场作为灾民挨了一夜冻,终于在次日下午到达长沙。此时的长沙,十万军民上街扫雪除冰,我向报社发回了第一张扫雪的照片。在省军区招待所饱饱吃了一顿晚饭后,晚20时,夜行军,向300多公里外的郴州进发。
这300多公里的路艰难异常,白天化雪,晚上气温下降立马结冰,我们在大雾弥漫、能见度仅10米左右的“玻璃路”上缓缓行进。100公里路上我看见了8起车祸,20多辆车相撞,接下来由于大雾的掩盖,干脆什么都看不清了。2月3日凌晨4时,终于到达郴州地段。在距城区20公里,我们加入了被堵塞的汽车长龙。下车后借着车灯观察,京珠高速路是一个冰的世界:路上是冰,路中央和路两旁的绿化带树上全是冰坨子。郴州冰灾的特殊是我此生首次见到:郴州是一个冰的世界。京珠高速路上结满了5至20厘米厚的一层冰。郴州地方电网高压线电塔全部倒塌,全城停电。成千上万辆各种轿车、载重车把高速公路堵死,京珠高速路郴州地界几十公里路段成了难中之难。部队对这段高速路临时实行了“军管”,机械化加人海战术,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一起上阵,刨的刨,铲的铲,砸的砸……装甲牵引车上了阵,昼夜突击。战至4日中午11时08分,京珠高速公路耒宜路堵塞最严重的这段冰道终于被打通,实现了北上南下双车道通车。我拍下这些感人的画面及时传回报社,传递给心系灾区的读者。

在大兴安岭火灾现场采访

记录下雪灾中的湖南郴州

荣获长江韬奋奖
救灾救到家门口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编发《解放军报》当天的新闻图片稿。惊天噩耗传来,15时31分,收到手机短信:绵竹地震了!绵竹是我的家乡,短信让我心急如焚,然而此刻老家亲人的手机却全都打不通了。打开电脑上网,大吃一惊:四川境内发生特大地震灾害。我当即决定奔赴灾区采访。16时30分,我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救灾部队正在集结,两架伊尔-76待命起飞。下午18时老家才传来消息,却是两位亲人遇难的噩耗——绵竹灾情极重。我强忍泪水,拍摄了工兵团官兵点名、登机的照片。19时许,军机起飞,22时在成都某军用机场着陆。卸载、装载、编队、加油,直奔汶川。
车队行至都江堰市成灌高速公路收费站,接到命令,山体崩塌,都汶路堵塞,部队就地救灾。我随工兵团一部到达聚源镇中学,但见一幢六层教学楼整体垮塌,趁部队下车集结、分工的时机,我快步跑上废墟开始拍摄。此时,天下着雨,废墟上遍布尸体,救援工作已经展开,20分钟不到,我就拍摄到武警成都市消防支队的勇士们从倒塌废墟的缝隙中救出一个学生的照片。一名武警上尉告诉我,废墟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被房梁卡住。此时是13日凌晨2时30分,工兵团官兵接替武警,投入抢救生命的战斗。战士们钻进倒塌废墟横梁的缝隙中,冒着频繁的余震,顶、切、割、钻、锯、拔,经过6小时的艰苦奋战,于13日晨9时10分从废墟中救出幸存女学生高颖……勇士们的一幅幅英雄群像在我的数码相机中定格。记者的职责督促我赶快发稿!此时,都江堰无线、有线电信都不通,我赶到成都西郊,通过长途电话线拨号上网,向解放军报发回了第一批图片稿件。当日,中国军网辟专栏发表了这批最早反映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的勇士们钻进废墟,救出幸存学生的新闻照片。14日,《解放军报》刊出了这批照片。

在祖国最北端漠河边防采访

在四川地震灾区
发完图片,我立即返回聚源镇。工兵团接到上级命令,转战绵竹市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救人。我为部队带路奔向汉旺。13日午夜,救援车队到达绵竹,但见城区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出城区奔汉旺,行车300米就到了我的老家,依然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借着汽车灯的余光,我看见家乡马路两边一片废墟,心如刀绞,泪眼模糊。这时,我多么想停车看看,哪怕两三分钟。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停车,我是记者,更是军人,部队在执行命令,目标是汉旺,时间就是生命,我没有停车的权力,不能耽误一分钟。我强忍悲痛为车队领路直奔汉旺。
15日8时,我乘陆航团长余志荣驾驶的黑鹰机,超气象飞行,抵达地震中心汶川映秀镇采访,成为最早进入汶川的摄影记者之一,摄下了英雄官兵抢救伤员,从映秀小学废墟中救出小春梅的镜头。当天下午,从汶川返回凤凰山机场,发完稿后顾不上吃饭直奔北川县。傍晚,找到正在曲山小学奋战的驻滇某集团军工兵团。在这里救人无异于虎口拔牙:曲山小学地处北川新城陡峭的山边,和被垮塌的山体埋葬的北川中学新址相邻100多米,余震频频,山体随时可能垮塌,时时威胁着官兵们的生命。官兵们冒死夜战9个小时,于16日晨4时39分救出三个学生。我在陡峭的山坡上守候一夜,记录了官兵们的壮举。次日,题为《苦战九小时,救出三女生》的一组5幅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在《解放军报》刊出。
在这次地震中,我的家乡绵竹市东北镇天齐村98%的房屋倒塌,死亡45人,乔家遇难3人。19日下午2时28分,二炮部队官兵在我的家乡天齐村和乡亲们一起在废墟上举行仪式,哀悼死难同胞。我噙着泪水,摄下了军民悲痛悼念和在废墟上宣誓的场景。
我来自四川农村,入伍前是个放牛娃,只读过6年书。23岁就进入了《解放军报》。80年代,靠艰苦自修,用三年的业余时间参加自学高考,获取了中文和党政干部基础科两个大专文凭,为我从业打下了文化基础。
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任《解放军报》记者32年,我们这支英雄军队为我创造了取之不尽的新闻资源。国家和人民养育了我们,面对战争,面对灾难,义无反顾上前线是我们的使命。作为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新闻现场,在血与火的第一线摄取新闻图片是我的工作。危险地区、危急关头、危难时刻,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军人和记者。2003年,我的老领导,军报摄影美术处原处长韩荣志去世,我为他张罗后事,从他火化后的骨灰中拣出了一块弹片。“上战场不能畏缩不前!”这就是他向我交代战场纪律。我的另一位老领导,军报摄影组原组长郝建国在战斗中摄影,眼睛受伤,用一只眼坚持工作几十年,现在已经双目失明。可以告慰老一辈的是,我军战地摄影的优良传统毕竟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得益于当兵时的训练,我养成了个习惯,家中有个平时不动的“战备箱”,“战备箱”中储有出差要用的各种物品,过去是胶卷、暗房袋、冲洗胶片用的化学药品、剪刀、玻璃瓶、温度计、换洗衣物、个人卫生用品之类,现在则是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等等。一有紧急任务,背起摄影包、提起“战备箱”,5分钟之内就能出发。
《解放军报》培养了我。《解放军报》这个业务平台给了我千锤百炼的工作机遇,把我从一名士兵培养成高级记者。我调入军报不久,组织和领导就把我作为摄影记者的主力使用。领导一次次赋予我重要的任务,认真二字,我坚持做到了32年如一日。32年下来,所幸的是我扪心自问,可以心中无愧。
作为军人和记者,我并不希望战争和灾难发生。我愿我们国家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但客观现实难如人意。在我今后的军人和记者生涯中,如果发生战争和灾难,我将一如既往,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