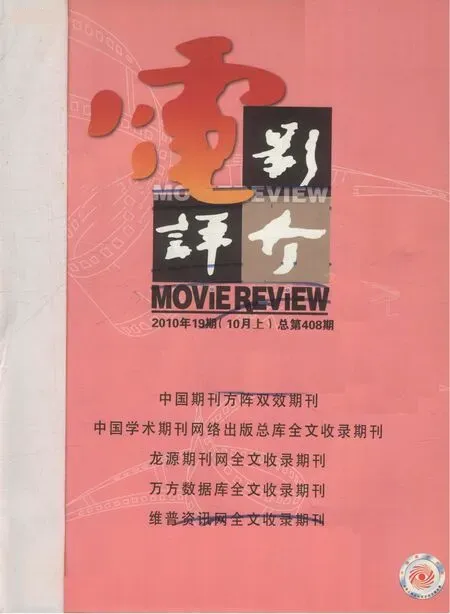由“家”到“国”:论香港电影《刺马》与《投名状》的“兄弟”观
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出现新武侠电影流派,大导演张彻被称为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在他的电影中,“兄弟情仇”和“阳刚美学”一直是两条互为表里的线索。拍摄于1973年的电影《刺马》,是张彻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的英文翻译是blood brothers,比中文题名更加直接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和美学风格。张彻的弟子吴宇森后来曾提及,他对张彻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刺马》,在他自己的作品《喋血街头》和《喋血双雄》里表现了与张彻《刺马》相类似的兄弟情怀。2007年,基于长久以来对《刺马》故事的深刻兴趣,香港新一代著名导演陈可辛重拍了这个关于兄弟情仇的故事,并改名为《投名状》。《投名状》的故事结构和《刺马》极为相似,却体现出和后者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故事由黑白鲜明的善恶果报转而成为对晚清战乱时期个人悲剧命运的灰暗迂回的回想反思,二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出张彻和陈可辛这两位不同时期的香港导演对于中国大历史的态度发生的微妙转化。
73年的《刺马》上映后受到相当高的评价,饰演马新贻的狄龙凭此片获得了第19届亚洲电影节的“表现特出性格男演员奖”和第11届金马奖的“优秀演技特别奖”。《投名状》在获得奖项方面亦绝不逊色,此片在200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夺得8个奖项,并包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李连杰亦凭此剧成为最佳男主角。台湾的2008年第45届金马奖《投名状》再次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及最佳视觉效果等三项奖项。1973年《刺马》问世到2007年陈可辛执导投资3亿人民币的《投名状》,香港和大陆二十余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在这个关于“兄弟”情感的故事之中产生出巨大的裂变。在《刺马》之中,张彻借助电影表达了在“兄弟”情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之间激烈冲突,并对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行为显示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维护兄弟情深的铁三角关系成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指向,在此主题之下,整部电影叙事明快、层次明晰、色彩鲜明,体现出70年代香港武打电影特有的影像风格。而《投名状》则更加着力于宏大的战争场面,片中情节曲折,人物个性复杂,场景设置逼真,在电影的美学追求上具有当下香港电影鲜明的时代特色。两部影片差异极大,而其中对于“兄弟”情谊的解读,马新贻/庞青云之死究竟是代表着“家”的传统情感的维护还是对“国”的利益的夭折之殇,是张彻和陈可辛在影片中发生争论的核心主题。
《刺马》和《投名状》都根据三兄弟结义金兰、情同手足、反目成仇的感情发展节奏作为整部影片的故事主体结构。大哥马新贻《刺马》/庞青云《投名状》的出场是两部影片体现其差异性的开始。在《刺马》里,马新贻的出场颇符合传统少年志士的风格:白袍白马,英姿飒爽。张彻在电影里经常喜欢使用色彩鲜明的服装道具,白/黑、善/恶的搭配给观众以明确的人物个性标签。这一方面可以给整部影片造成简单明快的特色,同时也会引发人物性格缺乏层次感的诟病。然而,在《刺马》里,马新贻并非非黑即白的一个人物,在他耀人眼目的白袍之下,是同样极为抢眼的黑色长裤,人物个性黑白各半的暗示跃然眼前,这是张彻对电影色彩符号作用的一个细节性的然而却是精妙的把握。为描述马新贻的少年英姿,张彻把摄影机摆在较低的位置,以站于马下的黄纵和张汶祥的视角来观看马,仰拍马上背脊挺直、英气逼人的形象。接下来一段关于“长毛”还是“发匪”的对话,显示出张汶祥对于“大丈夫”的人生见识远远高于表情强悍然而懵懂无知的黄纵,仰视/俯视的视角此时则不仅仅显现出双方的站立位置的差异,而更深化为一种对人生态度的高下之分。这段对话,几乎是全片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唯一交代之处,之后的故事基本就架空了与具体历史的必然关系。与之相反,《投名状》庞青云初遇赵二虎正值大战惨败,衣衫褴褛地坐在一群难民中间,颓唐狼狈,神情沮丧。陈可辛在《投名状》里交换了二人的位置,下山抢粮的土匪赵二虎彪悍沧桑,他在马上注意到庞青云,是因为对方脚上的一对官靴,两人四目相交,彼此的精神气场不相高下。对庞、赵之间势均力敌气场的细节渲染,为此后两人由于人生观的差异而产生激烈冲突埋下伏笔——冲突来自于双方同样强大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因为争夺一个女人。
同样,在描述三兄弟情感深化,进入亲密无间阶段的故事发展阶段,张彻仍旧是用一个仰视镜头拍摄三人立于高坡之上,各个表情如沐春风,意气风发,而这情感的蜜月期是与三人共同享受并肩作战之后的荣华富贵密切相连。这种快乐的短暂似乎只是为接下来讲述“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古老箴言而作一转折。与之相反,《投名状》里兄弟情谊达到高峰是在三人深陷重围,庞青云身负重伤时得到两位兄弟舍命相陪的时刻,三兄弟彼此紧紧依靠、赵二虎热泪盈眶的特写为三人的情感做出最引人注目的诠释。此时的赵二虎和姜午阳开始相信兄弟之情经得起血的考验,值得他们去顶礼膜拜。电影接下来继续叙述无休止的厮杀、血腥、阴谋与考验,三兄弟的情感一再受到艰难时世的考验。
用仰视镜头和黑白色彩搭配对人物性格进行诠释与一对官靴的特写,高坡上春风得意的三兄弟与重围中混着泥土和鲜血的脸部特写,两位导演对“相遇”、“兄弟情深”等场景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引出了另外一层含义:在三兄弟情感发展的线索之中,马新贻/庞青云的人格特征究竟如何去判断,该由谁来判断?张彻和陈可辛分别在影片中采用了同一个视角,即刺杀大哥者——三弟张汶祥/姜午阳的事后叙述。在《刺马》里,张汶祥被塑造成一个表面放荡不羁而对兄弟感情发展态势洞若观火的人物。张汶祥是一个颇有独立人格的英雄形象,他头脑清醒,个性独立,在发现二哥黄纵被害之后更能够独立缜密地设计刺杀行动。这让我们联想到70年代香港电影的主要特征之一,即产生了具有“香港人”个性的本土风格,而这个风格是香港终于摆脱了西方/大陆夹缝心态的独立姿态的体现。张彻时期的香港武侠电影并不关心电影所要表现的特定历史背景,《刺马》虽然从影片人物的服装道具来看,观众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故事发生在清朝,然而,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并不一定和清朝(太平天国)有必然紧密的联系。张彻“所讴歌的英雄也不追求救国救民的抱负,纯为一己之好恶,逞一时之快,只求活个痛快,杀个痛快,显得偏激而狂烈。”[1]因此,张彻时期香港电影所表现出的独立看似痛快然而同时却又不免狭隘。
与张彻塑造这种个人英雄相反,《投名状》里的姜午阳被塑造成一个嗜血残暴、目不识丁的武夫。陈可辛一开始就把故事的历史背景清晰显示给观众:太平天国时期的江南战场。庞青云与赵二虎、姜午阳在血腥战场上建立起来的一瞬间的深厚情谊,并不能够在此后不断的杀戮和名利争斗中被继续保持,分歧、谎言、背叛一直参杂在三兄弟的交往之中。与张彻在《刺马》当中极力渲染过的充满阳刚惨烈气氛的著名场面相比,陈可辛把姜午阳行刺庞青云的一场戏的背景设定滂沱大雨,泥泞小巷,使得他的刺杀行为显得拖泥带水、凄厉迷茫。姜午阳刺杀杀兄仇人时的决绝,带给观众的不是快意恩仇的释放感,而是一边倒的对导演塑造的另类英雄庞青云——这个似乎可以挽救朝廷于危亡之中的枭雄之死的怜悯与叹惋。
香港评论家文隽曾写文章谈陈可辛为新拍刺马故事定名为《投名状》时说到,“张彻版产生戏剧矛盾的冲突,主要来自马新贻与黄纵妻的一段奸情……陈可辛其实想透过《投名状》这荒谬的结义形式,去反讽这世上根本就不存真正的兄弟情和义气,这才是电影《投名状》最大的题旨!”[2]由此可见,香港电影中对于“兄弟”情感的演绎,在陈可辛这样的新一代导演这里已经发生的转变。《刺马》把故事的矛盾冲突中心放在“家”的伦理结构之中;距《刺马》34年,陈可辛想要表达的,不是能够超越具体历史桎梏的个人英雄,而是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这样一些在“国家危亡”的宏大的历史压迫下无法翻身喘息的生命个体。对于“独立”于历史背景之外的英雄形象,陈可辛开始发出明确的质疑。这种意识在他后来的电影《十月围城》当中进一步发挥。
因此,从《刺马》到《投名状》,从歌颂“兄弟”到质疑“兄弟”,两部电影的差异正是香港电影三十年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缩影。陈可辛以香港人对本土历史的重新审视的崭新姿态杀人内地市场,并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同度,它体现了现今香港电影发生变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即越来越意识到香港之外的那个本土大历史的具体存在,并试图重新融入到对整个大中国历史的诠释之中,这种融入必将引导香港电影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
[1]《张彻武侠电影指南》,《电影画刊》2003.7
[2]文隽《<刺马>改名<投名状>的考虑》http://ent.sina.com.cn/r/m/2007-11-28/005318102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