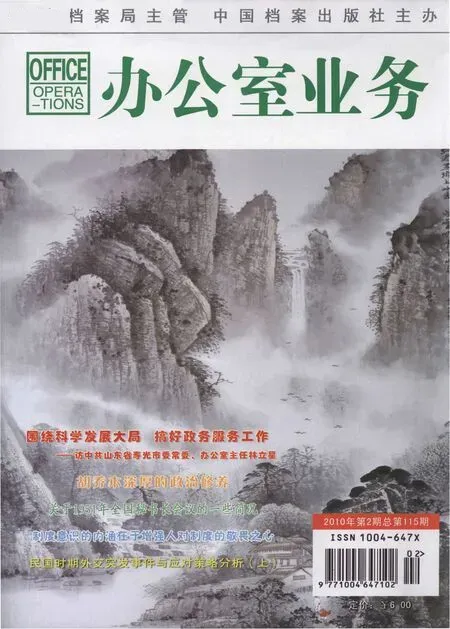胡乔木深厚的政治修养
李 秀 芹
(一)
毛泽东对胡乔木做过多次评价,既有表扬肯定,也有批评规劝。其中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据说是在1959年4月初召开的“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得知胡乔木未将陈云关于公布粮食高产的不同意见向他报告以后,在中央全会这样的庄重场合指责他:“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毛泽东的批评一针见血,既准确概括了胡乔木的角色特征,又指出了他这个“一介书生”与政治家的不同。
邓小平也对胡乔木做过评价。据中共中央批准的《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说,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原谅了胡乔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对他的揭发,既肯定“乔木是我们党内第一枝笔”,也批评“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结论是“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在中共高层论人若称书生气十足,往往是此人并非政治家之谓。
胡乔木逝世后,新华社受命发布的《胡乔木同志生平》称,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这大概是盖棺定论了。但笔者以为即便如此,胡乔木仍不愧为具有深厚政治修养与敏锐政治家视野的一代秘书大家。何况他历来主张秘书要具有政治家的视野,到了晚年尤其如此。他曾一再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人员说:“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对于政治形势,政治转变,就要有政治的观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也要根据政治形势来看。”他认为,“离开政治形势叙述党的决议,就不能正确评判党的决议,就不能评判党的决议的成败”。这是他一生秘书经验的总结。事实上,胡乔木如果缺乏深厚的政治修养,没有政治家的视野,又怎能成为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得心应手的秘书呢?
(二)
胡乔木关于秘书要有政治家视野的思想,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要能正确观察、分析、判断客观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二是依据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和策略思想。三是为实现预定战略目标与策略思想,确定相应的微观政策。这是胡乔木悉心研究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结晶。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最重要,是后两个层次的基础。只有对不断变化的、由相互联系的各种因素起着作用的客观形势迅速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才有可能据以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目标与策略思想,进而确定具体的实施政策。正如胡乔木论及“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问题时指出的:“正确的政策决定于对情况有正确的判断,采取的措施有切实的可行性,能够获得广泛的接受。”反之,如果对政治形势判断有误,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胡乔木举例说,“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
胡乔木认为,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前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这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强化政权建设的一系列政策等等,就是建立在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日本和中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等客观形势做全面分析、正确判断之上的。有了这种对复杂多变的客观形势的正确决断,才有了关于敌、我、友方面的正确战略、策略与政策,这已被实践所证明。
1958年至1978年之所以“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胡乔木认为这是“我们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都认识不足”、对国内国际形势判断有误所致。他说:“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的影子笼罩着很多同志的思想”;“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客观世界跟自己的主观世界发生矛盾,主观上的各种想法成为一种臆想”;“对社会政治力量实际上的对比没有科学的估计,这种情况是最容易犯的一种‘左’倾错误”。总之,不论是总结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还是研究其失败的教训,胡乔木总是能从三个层次着眼,并把能否正确观察、分析与判断客观形势放在第一位。
(三)
胡乔木政治家的视野,在起草《历史决议》时得到充分展示。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他先后与起草小组成员谈话32次,记录稿多达20万字。而且,亲笔撰写了有关“文革”十年的内容。整个起草过程始终体现了他那深厚的政治修养。
首先,是客观、理智地分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足以威胁中共命运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怀疑甚至否定“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阻碍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以及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一种是将建国以后乃至中共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思想并进而怀疑中共能否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无论哪种思潮,若任其发展,都可能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因此,如何写好《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成为中共面临的当务之急。胡乔木说:“现在在党内党外,都存在两种很不相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对毛主席有哪些错误应当讲清楚,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最好是不讲”;“有的同志说,现在要赶快出毛泽东全集,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的所有作品都照原样编出来,以便于大家来批判。”当然还有另外的意见:“毛主席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确实把我们党广大的干部带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胡乔木认为,“我们要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否则,很难用历史来教育党和人民。”胡乔木的这种判断是实事求是的,也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了基调。
其次,是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战略、策略思想。胡乔木说:“要考虑到党内有各种情感,各种要求,要找到这中间的最大公约数,在那个基础上来说话,使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因为各方面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所以写这个稿子就要很好考虑。”他还说:“无论如何不能发表这样一个讲话,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这个问题是个关系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历史决议》“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党里还有很多人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领导人民,把中国带上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点上要很鲜明。”“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中央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贯穿了乔木的这个战略、策略思想。
再次,有了上述对政治形势的理性观察与准确判断,从而产生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以后,就可以制定具体的“拨乱反正”等微观政策,较顺利地促进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总之,胡乔木政治家的视野,反映在《历史决议》的字里行间中。
(四)
胡乔木的政治家视野不是天生的,而是有个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
首先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与熏陶。胡乔木在延安刚做毛泽东的秘书时,就上了一堂“要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的启蒙课。一次,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谈改版问题,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都尖锐地批评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场的胡乔木感到批评得太重了,便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泽东批评他:“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毛泽东的批评对胡乔木而言,影响是深刻的,直到晚年他还常常提起。
1956年12月,胡乔木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次写作实践对其形成政治家的视野产生了质的飞跃。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方面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表明斯大林及苏联党的做法并非都是对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办事;另一方面也捅了娄子,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产生了混乱,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面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如何表态?怎样评价苏共“二十大”?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要做具体分析,他是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明确肯定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同时也要指出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毛泽东的这种抛开个人恩怨,立足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胸襟,使我们理解了二十四年后胡乔木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之所以再三强调“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来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所在,也足以看出他受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当然,这些毕竟还是外因。如果没有胡乔木本人的努力,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对改造世界观的自觉与真诚,那也是很难成就其深厚的政治素养的。胡乔木在《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一文中如数家珍般地点评马、恩、列、斯、毛这些卓越政治家的经典之作,使我们发现了他那政治家视野形成的内因。他在谈及用理智的态度研究历史时说:“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还是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还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这更让我们看到了胡乔木的政治家视野与其百科全书式的学养,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