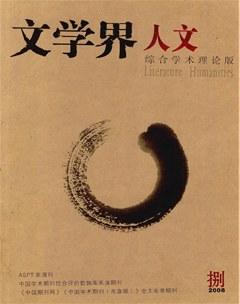臆论《红楼三论》
汪大白
内容摘要:《红楼三论》是一部富有价值的红学专著,所论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前沿性,所用方法具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作者关于版本的探索和结论,还需经受学界的审视和时间的检验。作者否定曹雪芹著作权而指认曹颜著《石头记》的观点则难以确立。
关键词:问题;方法:人物:版本;作者;证据
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07-04
《红楼三论》是徐乃为撰著、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新书。笔者与著名红学家白盾合作《红楼争鸣二百年》时,认真研读了该书,深感该书在近年红学新著中特色鲜明而不容忽视。为此且将我们的看法写下,以就教于学界与作者。
一、关于“人物论”
对照通常可见的形象泛论,徐先生的“人物论,极富特色。
首先,徐先生的“人物论”体现了极强的“问题意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前沿性。他论林黛玉角色地位,是因为读者过多关注林黛玉,总觉其角色表现似乎不及薛宝钗重要,往往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林家为什么不上“护官符”?黛玉为什么没有金饰物?他论薛宝钗的文学形象,就想澄清研究中存在分歧的某些基本问题,比如宝钗与黛玉的思想本质是否构成鲜明对立的问题;宝钗是否处心积虑要取黛玉而代之,千方百计谋夺宝二奶奶宝座的问题。他之所以论述“湘云的婚恋结局与脂砚的性别身份”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借此求正于周汝昌先生”。他之所以研究秦可卿的问题,正是因为问题关系到刘心武“秦学”的是非得失。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强烈的针对性,体现出该书所论的学术前沿性,从而赋予论著选题以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徐先生的“人物论”,根据探索的具体范围、具体需要,得心应手地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方法的运用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他在《袭人晴雯异同论》一篇中用的是作品分析法,他说:“只要我们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把睛雯袭人放在历史的文化层面上,排除个人喜好的偏见,排除先入之见的干扰,我们将会得出与通行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与周汝昌论史湘云,运用的则是探佚法。因为“史湘云结局问题的实质是探佚问题”,于是他预先明确“探佚的依凭”的四个“要点”,然后从角色地位与婚恋设计、图诗曲的婚恋解读、“金麒麟”的“间色”预伏等方面进行论证,结论认为“湘云之醮归宝玉是不成立的”。
还有,对于特别重要的人名、特别稀罕的物名,为了揭示其中内蕴和寓意,例如探索“黛”、“钗”两个人名的内蕴。探索妙玉两个“怪杯”的寓意,徐先生杂取考证、探佚、索隐等等方法交互使用,最终统一于对小说创作设计的体悟和把握。在索求妙玉“怪杯”的综合意蕴之后,他给自己提出“特别要思考的”问题:“是否符合《红楼梦》对妙玉形象的总体设计与具体描写呢?”一作者的总体设计与作品的具体描写,正是其“人物论”两个基本的立足点与着眼点:也正是立足于、着眼于作者的总体设计与作品的具体描写,他的方法运用才能恰如其分、各得其所,人物评论才能实事求是、确有创获。
立足于、着眼于作者的总体设计与作品的具体描写,依据“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上下”的形象定位,把握“钗黛合一,互补兼美”的创作思路,徐先生《宝玉、黛玉、宝钗之人名内蕴揭解》以及《黛玉初名代玉考辨》两文,对三个人名的寓意进行破解,认为三个名字的设计,揭示了黛、钗二人“等同的角色地位”、“互补兼美的形象内涵”;揭示了宝玉与黛钗之间“等距离的婚恋关系,包括等同的婚恋悲剧”;并且认为,“黛”抽取于“粉黛”,“钗”抽取于“裙钗”,“粉黛,,一与“裙钗”均为青年女子的代称,今用于女主角黛玉、宝钗,则视二人为红楼女子的代表,甚至视为中华女性的代表。应该说,除最后一句似有拔高之嫌以外,三个人名寓意的推想都能为我们所接受,因为这些推想符合作者意图和文本实际。一方面,小说叙事中关于黛、钗二人判词与梦曲的设置、关于二人与宝玉等距离亲缘与同方式结缘的设置,以及等距离婚恋与同地位角色的其他细节的描写,都反映出作者相应的总体意图。另一方面,从黛、钗形象的塑造来看,在作者笔下,论貌则二人兼美,论才则二人并秀,论德则二人趋同,同样反映二人在作者的设计意念中是距离相等、地位相同。这些说明作者对于三个主人公的取名的确十分精心,也就说明破解三个人名的内蕴的确不无意义。不过我们并不赞成将这种人名破解看作“析幽探奥的捷径”。假如缺乏对作者意图、作品主题的准确把握,这种破解就与索隐无异,捷径可能变成歧途——因为字词在拆解辨说之中,其意义指向多不确定,完全可能任人所取。回顾以往索隐诸家,多见人名的任意索解。当然,徐先生解释“代玉一因谢世而被替代的“玉”,“宝钗”——因离弃而被分开的“宝”,可说大致不差,对于宝玉与二人等距离婚恋悲剧的理解,比起我们说过的“让路”方式,的确更进一层。
立足于、着眼于作者的总体设计与作品的具体描写,看到了黛、钗二人等同的角色地位、并秀的形象内涵以及她们与宝玉等距的婚恋关系、等同的婚恋悲剧,便会消解历来关于钗、黛二人的优劣褒贬之争,澄清关于宝钗形象的种种误解。徐先生《薛宝钗形象歧见之研究》一文,通过作品情节的具体分析,对误解宝钗形象的论点进行反思,否定了钗、黛之间“卫道叛逆,势若水火”的对立关系,否定了指认宝钗“处心积虑,谋夺宝座”的错误见解;并且在宝钗结局的探讨中。排除“宝钗情缘,另有所归”的可能,同时肯定钗、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同样悲苦深重,“若从现今的悲剧观念去评判,则宝钗之悲更甚于黛玉。”这些论述不仅观点鲜明,而且见解可取。
与钗、黛评论相关的是袭人、晴雯的评论。“袭为钗副,晴有林风”,袭、晴历来被视为钗、黛的影子,在人们心目中,袭人与晴雯也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位置,人们的评判“一般都是褒晴雯而贬袭人”。徐先生在《袭人晴雯异同论》中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睛雯袭人,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质异形。”(第222页)他认为:将当宝玉的侍妾视如人生目标的唯一追求,这是袭人晴雯相同的也是最本质的方面,睛雯在这方面的自觉、迫切和执着比袭人毫不逊色。与此相关,她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婢女头儿自居,有着出“奴”头地的愿望,这一方面睛雯与袭人并无二致。论及二人不同,他通过分析,指出她们个性品格的不同,以及内心欲求的外现方式与追求方式的不同。他的结论是:
袭人与晴雯做宝玉之妾的人生目标是相同的,自视为奴婢头儿的心态也是一致的。但是品性有“媚”与“洁”的高下,出发点有“情”与“礼”的区别,谋取方式更有“曲”与“直”的不同,因此还是给人以鲜明的不同的审美感受。(第243页)
这一评论突破简单的道德评判,更加富有文化内涵;既体现历史的原则,又有着审美的观照;既扣住作品实际,又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所以见解成立而又显得新颖。
同样新颖的还有《赵姨娘形象新论》。赵姨娘是一个内
涵复杂、形象特殊的人物,我们对她无法简单归类,更难以准确评判。她与丈夫、女儿之间不相称,与贾母、风姐之间不合拍,与贾府背景之间不协调,“她分明是一个异类”!人们感到她讨厌,有时又觉得同情;有时觉得她像是“反抗”,但她却明显是在“使坏”。着眼于她的特殊目的与特殊手段,徐先生将她定性为“畸形的反抗”,认为“畸形的反抗”决定于她卑微的身份地位。正是姨娘身份的卑微,经济地位的低下,人格上的屡遭凌辱,导致她性格的特殊性;而她“畸形的反抗”,目标狭隘,手段阴狠,让人觉得可恶、可怕,又感到她的无奈——恐怕这正是小说塑造这个人物的意义所在。就人物评论而言,徐先生看到了赵姨娘形象的特殊性和内涵的复杂性,但是他的观点独特却似乎不甚全面,他的论述简明却似乎尚可深入。
总之,徐先生“人物论”所研究的都是历来争议较多的女性形象,他所作出的人物评析见解新颖、个性鲜明,应当得到肯定、受到欢迎。
二、关于“版本论”
徐先生的“版本论”,论的是一个专题:甲戍本成书的时间及其相应的内涵。他的结论是:
该书不可能成书于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而是成书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曹雪芹未及终稿而死后的菜一年;该书是评批者、整理者圈内人(极大可能是畸笏叟)的最终“集评式”的整理本。胡适先生所赖以命名的唯一依据“至脂砚斋甲戌(原本误为戍)抄阅再评仍用陌头记》”一句中的“甲戌(原本误为戍),是抄胥抄误之词。(第274页)
徐先生分别以“甲戌本”成书时间的逻辑判断,“纂目”、“分回”与“甲戌本”成书时间,脂本的人名演变与“甲戌本”成书时间,语句修润与“甲戌本”成书时间,正文校析与“甲戌本,成书时间,“甲戌本”第一回独多的“四百余字”与成书时间,以及“同评异文”与版本先后等多章考论,证明“甲戌本”其实是个后起的本子,并不具有“甲戍本”的内涵。
在分章论证“甲戌本成书时间的基础上,他推出一个独特的见解,认为“那个脂评圈内人在作整理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重新评批,即留下了大量的新评语——那些未及流传到别的本子上的最后一次新评语”。他称这最后一次评批为“末评”,视之为“综合整理”的一个方面;而且认为这个“末评者与最后整理者”应当是畸笏叟”。(第402、420页)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确是“新红学”的两大核心问题之一。胡适1927年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即“甲戌本”以后,“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并称“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最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胡适的话表明两点意思:一、甲戌本的成书时间早于其他本子;二、甲戌本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关于甲戌本的学术地位与版本价值,红学界一直十分推重。周汝昌近年还强调:“甲戌本《石头记》是国宝。甲戌本是红学的源头。甲戌本的重要价值,远胜于庚辰、己卵之本。只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有人提出“脂评伪托说”,根本否定包括甲戌本在内的脂评本,正如徐先生在《“脂评伪托说”总评批》中指出的,“这是一个完全错谬的结论”,所以在红学界受到广泛的批评。
关于甲戌本的成书早晚,红学界真还存在不少歧见。吴世昌《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一文认为,甲戌本“系从较晚的、不止一个底本过录而来”。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一文认为,甲戌本抄录的时间应该晚于己卵本和庚辰本;赵冈、陈钟毅在《红楼梦新探》中指出,现存甲戌本的底本是晚于庚辰本底本的“新定本”。
但是长期以来潘重规、周绍良等很多学者始终认为甲戌本早于其他各本。直到目前,认甲戌本为最早版本仍是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冯其庸2004年为北京图书馆影印《甲戌本》写的“弁言”指出,现存纪年最早的抄本是甲戊本,只是现存的甲戌本并非甲戌原本而是过录本。蔡义江2004年出版的《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一书,通过对“正文”的考察辨析得出结论:“甲戌本是最早的本子,也是曹雪芹最后的改稿”,同样他认为,目前见到的是这个最早本子的过录本。刘世德先生《红楼梦版本探微》以两项个案研究的结果也已证明甲戌本是最早的本子。
可见红学界关于甲戌本早晚问题的意见,见仁见智难于统一。立足这个学术平台,考察徐先生的版本论,我们觉得其中闪烁着一些思维的火花,传达出一些考论的新意,值得学界重视;尤其是徐先生认为在版本演变过程中存在整理者的“末评”的见解显得新颖而独特,而且关系十分重大。只是我们都很明白,恰也如同徐先生所说的那样,“研究判断古籍版本的先后,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专门的学问”;特别是《石头记》版本源流的考证审辨,更是极其繁重而又艰难的学术工程。
我们认为,研究甲戌本成书时间早晚这一课题所要求的,显然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自圆其说或者见解独到而已;这一课题所要求的,是在繁杂交错而且是动态演变的版本现象背后,必须清晰地、准确地揭示出那个“确曾存在”而且“确属惟一”的事实真相!其艰难何如、其严峻何如,可想而知!正因如此,不言而喻,徐先生的思考与探索,徐先生的见解和结论,都还需要经受红学界的审视与推敲,尤其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和鉴定!
三、关于“作者论”
徐先生“作者论”的基本观点是:《石头记》的原始作者确是曹寅后人,但却不是曹雪芹,而应当是曹寅的养子曹颜。围绕于此他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石头记》的早期流传看,“其始创作时间当在雍正初年的公元1728年之前,其时曹雪芹只是不到十岁的孩童!…因此,《石头记》的原始作者决不可能是曹雪芹而只能是他的父辈!”
(二)、早期脂本版式以及批语表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重评'之前,“有一人已经首批《石头记》……这个人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只能是《石头记》的评批者而不是《石头记》的原作者”。
(三)、“披阅增删”是脂砚斋对曹雪芹与《石头记》关系的“盖棺论定”,“既然他人在曹雪芹逝世之后说他是‘披阅增删者,这‘披阅增删只能是真实的”。
(四)、仔细辨析脂批涉及曹雪芹“写”《石头记》的批语可以断定:“这些批语的本意都不是指‘创作,而是指‘披阅整理。”
(五)、作为自叙性小说《石头记》,“可以清晰地考索出曹氏家族与贾氏家族的平等对应……作为曹颐遗腹子的曹雪芹的对应者只能是贾珠的‘准遗腹子贾兰,《石头记》的男一号主人公贾政的独生子贾宝玉对应的只能是曹寅的儿子!”“根据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一般地就是作者的规律,《石头记》的作者只能是曹寅的儿子,而不可能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
(六)、自传性小说《石头记》,原型事件取材曹寅时代,“而曹寅逝世多年以后才出生的曹雪芹不具备《石头记》作者所应当有的生活经历,自然也不可能是《石头记》的原始
作者。”
(七)、“《石头记》之空前绝后的彻底的悲剧结局……只有曹颜的特殊身份,可以在创作学上获得准确的满意诠释。”(第4-6页)
关于《石头记》作者问题,徐先生所作论述全面而深入,所作探索认真而严肃,决非一般哗众取宠之谈、刻意标新之论可比;而且其中体现出那种学者所注重的“问题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学术胆识,都令人敬佩。然而,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指出,徐先生提供的依据、所作出的论述,大有可商之处,否定曹雪芹著作权而认为曹颜著《石头记》的新观点也难以确立。
所以说他的新观点难以确立,是因为他与历来对曹雪芹著作权持有异议的学者一样,只是涉及现有的己知的材料,未能提供新的有力的证据。所以说他的依据与论述大有可商之处,是因为他所涉及七个方面,完全属于他对现有材料的个人理解,尚难排除其他不同解读。可以看出,所列七个方面不外两种情况,前四个方面是对前人文字资料的理解,后三个方面是对文学创作原理的理解。既然全属个人理解,也就应该保证本课题对“理解”的学术要求:一是正确,二是唯一。我们认为,徐先生的理解不外三种情况,一是正确,一是歧解,一是错误。本文无法就此作出全面而详尽的评议,只能就其比较新颖的第一方面的论述作一具体考察,以求窥豹一斑之效。
徐先生说:“关于《石头记》原始作者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从《石头记》流传的视角去研究,从流传的时代去推测创作的时代,从创作的时代去寻找、去推定《石头记》的原始作者。”(第8页)值得肯定,这是个不错的视角、不错的思路,只是需要不错的证据。他说:“如今我们发现一则关于《石头记》早期流传的史料,其流传远在曹雪芹死年的壬午年之前,竟然提前了二十年!不仅与未成书稿应当在作者死后流传的通则相悖,而且由此推算出的《石头记》始创作年代竟然在曹雪芹的童年!由此而提示曹雪芹决不可能是《石头记》的原始作者,只能是《石头记》的披阅整理者!”这里使用“决不可能是”、“只能是”的措辞,表达出毫无保留的语气。其实“通则,之外是否还有特例,“推算”之中是否存在问题,都不能不令人疑虑——当然这是细微之处。最重要的是,他究竟“发现”什么可靠的史料,能够作为“过硬的证据”,作出这样的论断呢?原来他“发现”的是“曹雪芹同时人周春”的“一则记载”。他引用这篇文字时特将下面一段设为黑体字,认为其中“透露出《石头记》早期流传的时间”:
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1743)、甲子(1744)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记》、《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也。
据徐先生说,周春这段文字似乎有两种歧义的解释:
1、我在癸亥、甲子间私塾读书时,就耳食到父老说《石头记》中贾家的事就是张侯家的事,当时具体讲述已经模糊,只觉得约略与《石头记》相符;当时不敢臆断,如今通过考析,觉得当年父老的判断十分正确。据此可知,周春儿时曾听父老说,《石头记》里的贾家就是历史上的张家。
2、我在癸亥、甲子间私塾读书时,曾耳食父老谈张侯家事,记得不甚清楚,后来读了《石头记》才约略觉得张侯家就是贾家。那么,据此则理解为:听张侯家的故事是儿时的事,对张侯与贾家作比照索隐是后来的事,或者是此刻的事。
即使是在精心设定的两种解释中,我们也会倾向第二种,因为第二种解释比较符合周春本意。相反第一种解释倒是严重曲解了原文。其一、原文说“听父老谈张侯事”,只能理解为“耳食父老谈张侯家事”,怎么能解释成“耳食到父老说《石头记》中贾家的事就是张侯家的事”?“父老谈张侯事”与“父老说《石头记》中贾家的事就是张侯家的事”,完全是两个意思,岂能彼此等同!其二、“觉得当年父老的判断十分正确”一句,根本不符合周春原意。周春说的是,他本人“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之后,初步感觉“父老”当年所“谈张侯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诸书,遂决其无疑义也”,即认定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原文只有“父老谈张侯事”,哪来“当年父老的判断”?真有“当年父老的判断”,那么贾府“张侯家事说”怎能算是周春的观点?可周春又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周春再三强调的是他自己:“余……不敢臆断”,余“再证……”,“余细观之”一他肯定的只能是他本人的判断!
可是徐先生偏却采取并坚持第一种解释,认为:“这第一种解释自然证明了在乾隆癸亥(1743)、甲子(1744)时,《石头记》已经流传到了周春的家乡浙江海宁了!一毫无疑义,他的立论需要这个“最早流传的下限”!所以颠倒过来,他便彻底否定第二种解释。他说:“只要稍作事理辨析,第二种解释是不成立的。”他在“理由”的陈述之中,始终将他的理解认定为周春的“立意”、“本意”:他将周春说的“父老谈张侯事”,当成“当年听说的《石头记》的题材所自”;当成“当年我的父老说《石头记》写的是金陵的张侯家”;当成“周春的父老们阅读《石头记》时作正史证稗史的交流一将自己的理解当作客观的事实,而且如此执着,关键是早已存有一个既定的结论于胸臆之中!既然如此,妨碍既定结论的第二种解释,也就当然遭到否定。
徐先生否定自“理由”之中有一条特别有意思,他说:
假如当年周春的父老只闲谈张侯故事,并未与《石头记》联系。而周春在数十年后接触《石头记》时,才猛然领悟儿时耳食父老讲的“张勇家事”即是此刻所读《石头记》的贾家,作出奇特的联系索隐,完全不合思维的逻辑。而且,细看周春下文的引述,几乎看不出贾家与张家相关的地方:所以要他在数十年后对儿时的耳食作出考索是不可能的。(第11页)
由此可以看出,徐先生对周春其人认识不足。红学历史已经证明,周春正是穿凿附会的“索隐”风气开启者。尽管我们认为贾家与张家并不相关,但是周春却能将儿时耳食的“父老谈张侯事”与晚年所读《石头记》硬生生扯到一起,正是凭借不同寻常的思维逻辑,而“作出奇特的联系索隐”。
由此可以反证,徐先生把“父老谈张侯事”释为“父老说《石头记》中贾家的事就是张侯家的事”是曲解——周春果真写明父老谈的是或者父老谈的不是张家事与贾家事,也都无须徐先生这段“假如”!所以认为周春父老所谈竟是张侯事与贾家事,本来不是周春记载的意思,完全是徐先生按照“思维的逻辑”进行揣测的结果。
由此可以认为,徐先生对周春笔记的曲解,不只是具体词句的理解问题,而在于“思维的逻辑”问题。周春只是将父老谈的张家事扯到《石头记》上来,是以互不相关的“甲证乙”,是对小说作品的误读;徐先生将“父老谈张侯事懈释为父老说的就是贾家事即张家事,这可是无中生有的“甲是乙”,是对周春笔记的误读。原本是周春认为《石头记》是张侯事,竟说成周春父老认为《石头记》是张侯事,不知徐先生是上了周春的当,还是思维上超越了周春,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石头记》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胡适在红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就因为他不仅考证了小说的“本子”,而且考证了小说的作者。如果我们认为《石头记》的作者“这个问题尚未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就不仅需要“新的视角”,而且需要“新的证据”!提供不了新的证据,就确立不了新的观点:没有过硬的新证据,也就难以颠覆胡适的结论。关于作者问题的讨论,我们赞同胡文彬的看法:“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讨论中不管出现怎样大的分歧,都应该视作正常的现象。”同时,面对各种作者新论,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胡适的一句名言:“拿证据来!”
参考文献:
[1]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2]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7页。
[3]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4]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85年,上册第66页。
[5]胡文彬.《(红楼梦作者问题论稿)序》,见《红边漫笔》.华艺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