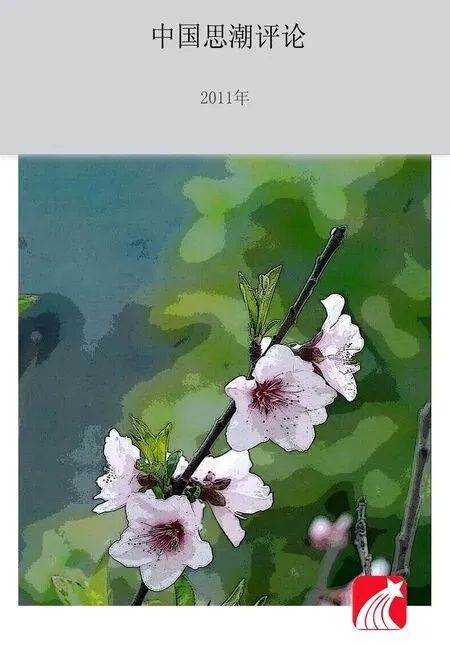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
何爱国 姜义华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可以称为“国粹”思潮,发生在晚清时期,这次思潮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鹄的,以“古学复兴”为旗帜,标揭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国粹学报》(1905—1911)为主要舆论阵地。第二次可以称为“国故”思潮,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4号。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北京大学国学门(1922—1927)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1929)是此次思潮的代表。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方兴未艾。本文拟着重探讨此次国学思潮的概貌及其趋向。
一、流派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兴起了第三次国学思潮。与前两次相比,这次思潮凸显了人文性、大众化与市场化特征:一方面有国学教研机构的大量兴起,如高校与民间的国学院、国学所、国学班、国学课、国学讲座、书院、蒙馆、私塾、淑女堂等;另一方面有国学媒介的大量出现,如国学网、国学博客、国学期刊、电视国学、手机国学、国学丛书、国学读本等,媒体关于国学的激辩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国学话语广泛进入了社会的思想前沿与主流媒体。从对国学的基本认识态度来看,这次国学思潮流派纷纭,论战激烈,其中主要包括重倡派、反对派、缓行派、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等。重倡派以赵吉惠、纪宝成等为代表,主张大力振兴国学。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以国学传承文化,接续文脉。认为国学在近百年实际上处于衰微的过程,这不仅源于西学的冲击,更因为我们在“富国强兵”的现实主义思维下把国学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文化“罪魁”,还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条主义、一元文化史观等思想的干扰,文脉出现了断裂,因此,要延续中国文脉就要“重倡国学”。第二,对国学所代表的传统思想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之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动力。传统与现代化、国学与西学并非二分对立,而是可统一与互补的。中国既需要科学与民主,也需要信仰与道德,而后者是离不开国学的。国学复兴绝不是向适应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的回归,更不是要回归古代的专制主义,而是在适应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复兴,是现代人“寻根”的精神之旅。国学复兴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中国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以中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三,把国学复兴看作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主张以国学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第四,国学能够扩大执政的文化基础,提升执政能力。第五,以国学建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认为国学管理是大智慧,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反对派以舒芜、章立凡等为代表,反对复兴国学,对其予以彻底否认。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国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适合编入现代学科体系。国学的内容都可以纳入现有的学科体系,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在当今社会科学分科越来越细、日益清晰的情况下,“国学”这样的错误概念就根本不应再存在了。第二,国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积淀,国学思潮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注]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国学里“更多的是愚昧,而不是科学;更多的是专制,而不是民主;更多的是禁锢,而不是自由;更多的是守旧,而不是创新”。[注]慕毅飞:《别在国学面前热昏了头》,《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24日。第三,国学精神不是商业思维,而是小农思维,不适合现代中国的发展,“国学”也无法培养出合格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缓行派以刘梦溪、张绪山等为代表,认为国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是“不甚恰当”的名词,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注]刘梦溪:《论“国学”应该缓行》,《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1月6日。儒家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在整体上的发挥作用,要到中国完成现代性改造以后,为中国的长远利益,孔孟之道应该缓行。批评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全面接受的态度,认为孔孟之道中包含大量反现代性的政治伦理思想,而目前处在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改造关键时刻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吸收其有益营养的同时抵制其毒素,复兴国学必然会给处在现代性改造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甚至会使宏伟的中华民族振兴事业出现历史倒退。
谨慎派认同学术范围内的国学研究,但反对具有公共色彩的、以“弘扬国学”为主体的全民国学运动,并提出应警惕“弘扬国学”范围的扩大化与极端化。
补充派认同国学,但反对国学主导论,认为国学对于今天而言应该是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只有其对现代学术能提供补益的部分才是值得发扬的,而其与现代社会和学术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则应该成为记忆。
重估派反对独尊论与复古论,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进行适应时代的重新估定。古代的思想文化资源与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需要经由重新估定、重新构建,融入新文化的创造中,方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上述流派中,重倡派与反对派都有一定的声势,但都有所偏激。前者往往倾向于夸大国学的功用,无视国学的负面因素,甚至走向了国学独尊(特别是“儒学独尊”)与国学救国(特别是“儒教救国”)的复古主义之路;后者往往倾向于完全抹杀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走向了本土文化虚无主义道路。缓行派与谨慎派则从当下国学运动中所存在的反现代化倾向出发,提出了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命题。补充派与重估派则主张结合时代特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重估派尤其强调“重估”与“重构”、“多元”与“一体”、“传承”与“创造”、“主体”与“世界”的结合。
二、特征分析
这次国学思潮所展现的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五大特征:
第一,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与学科创新诉求。在这次国学思潮中,很多学者认为,重振国学有助于提高中国的人文学术创造力,批评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大规模移植西方学术,把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经验的学术和文化类型当作普遍形态,结果使得中国人文学术普遍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由于没有看到作为西方人文学术根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的限度,忽略了中国人文学术自身的经验、问题和语境,从而使中国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依据自己的资源,针对本土经验,不断创生新的文化理论的生命活力。国学倡导者指出,中国的人文学术若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克服普遍面临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问题,解决好学科制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
第二,具有明显的人文素养与伦理精神诉求。认为国学是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基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思考方面,传统人文精神虽然不免具有农业文明与家族本位的特性,但也具有构建现代人文精神所需要的人本与人道属性。国学复兴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伦理规范与精神原理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第三,具有浓厚的功用化、市场化色彩。这次国学思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发生,更加强调走出书斋,经世致用,充满商业气息,并且强化国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强调把国学作为文化产业来经营。各种“老板国学班”应时而生,如“乾元国学教室”强调培育“能够掌握、传习、运用国学的综合思维,并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实现跨学科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话,开启管理人的困惑”。中国国学俱乐部摒弃“训诂”、“读经”等传统国学学习传播路线,尝试将传统国学哲学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进行结合,讲求“经世致用”,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国学中有关“修身”、“养心”、“固意”、“省思”、“慎行”、“乐艺”等六大传统的国学训练和体验系统,从而倡导国学在事业、职业、家庭、健康等方面的生活化应用。
第四,具有公共化、大众化、俗世化、运动化、时尚化与娱乐休闲化等趋向。这次国学思潮声称,国学不应仅仅是书斋式研究,更应当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生活,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使“国故”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现时代新文化的根基和组成部分。于是,国学以时尚的名义走入当下生活,国学经典也从庙堂走进民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出现,国学日益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易中天品历史、于丹解诸子热极一时,“电视国学”、“讲坛国学”、“手机国学”争奇斗艳,采取超女模式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热闹地开展,保安员谭景伟在北大宣讲《论语》心得,苏州某教授推出《新编人文三字经》,“国学辣妹”也不失时机地展露“风采”。对于国学的俗世化、大众化、市场化与“生产力化”,有人表示不安,有人指其浮躁,但也有人表示理解与认同,认为对娱乐化的国学用不着担忧,要流行,要普及,总得寻找最易被大众接受的方式,而娱乐和媒体就是被国学需求力量选中的现代方式;如果一提到“国学”就得诚惶诚恐,把国学搞成一门高高在上的学问,恐怕与发扬光大国学的初衷是南辕北辙的,长此以往,国学也不是没有被“捧杀”甚至“跪杀”的可能。
第五,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国学复兴人士指出,国学是中华文明之根,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和根基,是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因此,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离,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恢复民族与文化自信,增强民族意识的自觉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构建民族精神支柱,激发民族精神,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现代新文化,就必须重振国学、振兴国学。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注]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重建国学“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的标志,是进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开展文化对话的表现”。[注]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年5月26日。
三、背景及根源分析
第三次国学思潮与前两次国学思潮发生的背景具有根本差异,前两次国学思潮发生时,中国还处于农业与小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现代社会,而第三次国学思潮则处于中国工业化的中期与市场化的完善期,中国已不可逆转地踏上现代工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轨道。经过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之后,中国已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与世界文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但中国的文化与人文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不与之对称,人文的自主创新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就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突显期”的经济社会节点上,第三次国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展开的。以下从四个方面探讨其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第一,文化多元、文化认同与文化软实力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剧变,世界秩序在深刻调整。要求警惕全球冲突,呼吁文明对话与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呼声不断高涨,国人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国学热”正是适应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几乎全面覆盖了我们原有的学术话语,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国学这个参照系。
第二,市场经济的人文诉求。中国市场经济历经多年的发展,在21世纪初进入深化完善期,人文主义诉求日益强烈。首先,国学之兴乃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构建精神家园之所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一种持久的精神寄托,而国学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与精神架构,能够满足人们提升精神境界的需求。其次,国学之兴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设与其适配的道德规范之所需。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在道德层面还来不及重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以致诚信缺失、慈善缺位、腐败横行,迫使人们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救偏之策,并在建构新的社会道德体系过程中重整传统资源。
第三,海外儒学与海外华人的文化反哺。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使得全球学者孜孜以求其“奇迹”之因,“儒家资本主义”解释一时风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精神动力被归之于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新儒家由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能与资源,杜维明等新儒家代表人物以接续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较大的反响。其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广为流传,推促着国学思潮的萌发与发展。
第四,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与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挫折。后现代主义反话语霸权、反元叙事、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解构学科本位、呼吁重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与实践,给了中国学术界不同程度的刺激。而苏东剧变所引发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也催促我们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思想与精神资源,我们所提倡的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也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了其源头活水。在这种文化与政治氛围中,国学的崛起成为可能。
四、得失与前瞻
目前,无论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还是从身份标志、文化认同来看,国学的昌盛都是必要的,第三次国学思潮仍将继续发展。但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次国学思潮中也出现了若干误区,若不加以矫正,将不利于其健康发展:一是出现了提倡儒学独尊、儒教救国、读经救世等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一元化和夸大化的错误;二是出现了不加区别地一概诋毁和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复古主义与闭关主义的不良倾向;三是在普及国学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其实用化与大众化而导致了对国学的诸多歪曲。因此,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发展的、自主创新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它。
第一,提倡学术与思想的多元而非一元,鼓励争鸣。复兴国学不等于独尊国学或儒学,把国学或儒学意识形态化与一元化。无论是对于“国学热”思潮还是对那些反对“国学热”的观点,都必须一视同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谨慎、耐心地创造一种学术自由的气氛,使不同的学派与观点,都能够得到平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第二,警惕复古主义与排外主义,提倡现代化与开放的态度。王国维早在《国学丛刊·序》中就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复兴国学不是复古,更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了现在和着眼于未来。国学的形成本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前提下,对传统学术的清理与研究,并不是与外国之学对立起来的唯本国之学。要把国学放到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必须具备国际化、现代化的视野,以及开放、包容、自主的心态。
第三,警惕简单的实用主义态度。目前,对于国学的应用有三种态度:一是完全不赞成国学的市场化、俗世化、大众化,反对“恶搞”、“搏出位”等对国学的“恶俗化”,称之为“颠覆”、“浮躁”或“古人的厄运年”;二是认为国学的春天就在于市场化、俗世化、大众化与多元化;三是认为适当借助商业运作的力量能加快国学走向大众的脚步,但绝不能急功近利和过于商业化,将国学作为牟取名利的工具。前两种态度显然都走向了极端,第一种忽视了国学的人文关怀与公共性,而第二种则忽视了国学的学术性与社会意义。正确的态度应是以分析的、开放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国学,国学的生命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