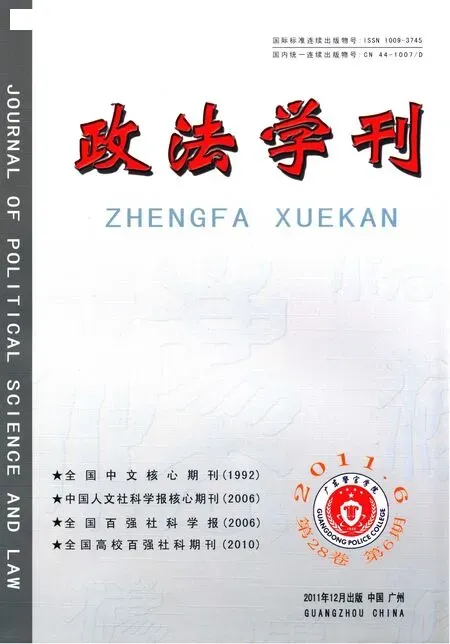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之历史现状及其造法方式
杨长海
(西藏民族学院 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诚如Dinwoodie教授所言,尽管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创建的历史并不算太长,然而这一法律部门自一开始就附有某种国际的量纲。[1]虽然早在19世纪末以多边公约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框架得以确立,但问题远未完全解决。知识产权已构成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商业性开发很少限制在一个国家。一个外来因素的渗透不可避免地涉及潜在的冲突法问题,如管辖法院的建立、准据法乃至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随着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的不断上升,晚近人们尝试创制知识产权冲突法制度。荷兰最高法院于1989年受理涉外商标权一案,开创了知识产权跨境管辖的先河,被誉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来,冲突法的作用致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的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如今人们对此领域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迫切。在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国际化、网络化,跨国知识产权案件层出不穷的今天,如何通过冲突法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对跨国知识产权关系的保护和调整是国际社会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之一。令人鼓舞的是,我国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就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用冲突法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国家层面上的立法,其意义可谓里程碑式的。本文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的历史现状做一简单梳理,并观察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模式的发展趋势,以求方家指教。
一、知识产权冲突法国外研究之历史现状
在历史上,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影响非常小。这部分是由于国际私法学者采用的“地域性”方法。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使得建立于“法之域外效力”基础之上的传统国际私法的制度方法“失去了支点”;另外,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自然属性使得人们对非物质现象很难进行物理的定位。人们难于回答如与知识产权最密切联系、自体法以及政府利益分析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问题。[2]1因此,知识产权被简单地排斥在冲突法的范围之外。
理论终归是要为实践服务的。“无论过去人们如何解释冲突法与知识产权领域问题的实际需要难以相容,但这种需要已变得日益迫切。”[2]2随着欧盟东扩,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与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欧洲一体化需要更多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因此,欧盟更为关注知识产权的统一国际私法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关知识产权国际私法著作应运而生。国际上第一本有关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著作是由Ulmer教授于1970年完成的《知识产权与冲突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该作品最初是用德语写成的,后于1978年被更新并翻译成英语。Ulmer的写作目标是为当时欧共体国际私法草案提出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建议性条款。因此,Ulmer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欧共体成员国知识产权的冲突法作出比较性论述,其中主要明确有关知识产权侵权与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其他问题如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外国法院的判决与执行问题均不涉及。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Ulmer为欧洲知识产权冲突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案掀起了一轮热烈的学术讨论。不过这轮讨论主要发生在德国学者之间,特别是那些与慕尼黑和汉堡马科斯普朗克知识产权法与冲突法研究所有关的学者,而且主要围绕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该轮讨论围绕地域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展开,与此相对应形成冲突法上绝然对立的两种方法,即保护国法 (the lex protectionis)与起源国法 (the lex originis)。①本文中保护国法与起源国法是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下的两个概念。保护国法是指知识产权基于国际公约被保护国家的法律;起源国法是指知识产权最初产生国家的法律。参见《伯尔尼公约》第5条。
在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著名的Huston一案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讨论可谓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接下来讨论的中心议题已不再仅是保护国法与起源国法之争,而是法律选择过程中精神权利的地位问题以及是否应由单一准据法而非保护国法调整知识产权的初始所有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掀起了一股知识产权冲突法的浪潮。随着1968年《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执行公约》 (《布鲁塞尔公约》)的缔结,内国知识产权在外国的实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以往的数年中,人们见证了大量的泛欧范围内知识产权跨国诉讼,其中荷兰最高法院于1989年根据《布鲁塞尔公约》受理涉外商标权一案,开创了知识产权跨境管辖的先河,被誉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的“哥白尼式革命”。[3]欧美学者给予知识产权冲突法以不遗余力的关注,各路学说精彩纷呈。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James J.Fawcett& Paul Torremans,1998);《从板块到网络∶国际知识产权策略》(From Patchwork to Network: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ller,1998);《电子空间下的知识产权冲突法》(Conflict of Law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yberspace)(Dessemontet,2000);《国际私法与知识产权》(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Austin,2001);《专利权的跨国实施:知识产权与冲突法结合之分析》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of Patent Rights:Analysis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arta Perteqas Sender,2002);《版权及其邻接权的法律选择》 (Choice of Law i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van Eechoud,2003)。
国际上有关组织与机构对于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海牙《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以下简称《海牙公约》或DHJC)计划展开的。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因特网通讯的急剧扩张所带来的问题也促成一系列围绕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国际专门会议的召开以及一大批出版物的发行。国际文学和艺术协会 (ALAI)在其1996年阿姆斯特丹以及2002年纽沙特尔 (Neuchatel)研究日选择了这一主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于1998年第一次组织知识产权特别会议,并且自此将该主题纳入其议事日程。2001年,慕尼黑马科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竞争与税法研究所 (MPI)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从事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关系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被纳入《冲突法中的知识产权》中,并于2005年出版。在美国,美国法学会 (ALI)于2002年正式启动了知识产权冲突法项目并被命题为《知识产权:跨国纠纷管辖权、法律选择及法院判决原则》(ALI原则)。为获得国际影响力,ALI委任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共同报告人以及一个全球性顾问团体。除此之外,ALI原则还加强与海外平行项目MPI项目的交流。ALI原则在经过多轮讨论与修订之后已于2007年5月在美国法学会举行的年会上获得最终通过,其正式文本也已公开发行。ALI原则的内容涵括知识产权纠纷管辖权、法律适用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参与专家来源最广、立法技术最为高超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原则。[4]作为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立法咨询机构通过的知识产权原则,其对各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理论与立法实践的影响力不可小视。
二、知识产权冲突法国内研究状况
在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随着中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后,中国学者对知识产权的研究白热化。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一个高潮,产生了若干有代表性的论作,如《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吕岩峰,1996)、《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郑成思,1997)、《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李振纲,1999)、《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微探》(石巍,1999)、《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 (冯文生,2000)、《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与解决问题研究》(朱榄叶,2004)、《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徐伟功、李涛,2004)、《从冲突法角度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姜茹娇,2005)、《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冯术杰,2005)、《欧盟知识产权统一国际私法研究》(屈广清,2006)、《商标国际私法研究》(彭欢燕,2007)。
学者从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与地域性的关系入手,提出通过国内立法、国际条约及相互承诺等方式赋予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从而使冲突法在调整跨国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中发挥有效作用。[5]有的学者从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制度基础入手,通过相关现实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分析,结合我国知识产权的国际地位和相关法律实践,来论证国际私法方法解决跨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基本问题;在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与法律冲突方面对中外理论进行逻辑综合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另有学者对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和评价,并从理论 (法律冲突构成要件)和实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肯定性的结论。此外,还有学者对区域性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研究或从部门国际私法的角度对知识产权冲突法进行了探讨。
但总的来说,我国的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与国外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相比显得落后不少。学者的研究比较分散、零碎,有的观点显得陈旧且片面。笔者认为,我国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我国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知识产权冲突法基本理论的纠缠上,学者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的关系论证上,许多观点都是在知识产权实体国际公约研究的基本理论之上形成的,推理性的结论多于实证。第二,我国缺乏对国际知识产权冲突法理论与立法现实的跟踪研究,研究思路比较封闭,有的研究资料还停留在上世纪末期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成果上。第三,对知识产权管辖权、法律适用等技术性方法问题缺乏充分的研究。有的学者虽有涉及,但大多无充分论证,研究结论过于简单且主观。第四,对新技术特别是国际互联网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影响研究不够,不少研究回避新环境下的新问题,更不能针对新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法,这与当前的国际实践严重脱节。第五,对知识产权冲突法问题缺乏细化的分类研究。
伴随着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的落后是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的滞后。我国《民法通则》、《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规,均未涉及冲突法方面的调整。我国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之中,①参见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以及2004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些规定仅涉及知识产权中某些具体的权利类型,而且在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上,不是适用国际条约就是适用我国法律,没有一条可以援引适用外国实体法的冲突规范,[6]难以适应涉外知识产权关系日益发展的需要。2000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出台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该示范法中专设“知识产权”一节,共8个条文,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的效力、知识产权合同、知识产权侵权等方面的问题。该示范法虽然是学术性的,但其立法技术在国内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为我国知识产权的冲突法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国际国内热于探讨知识产权冲突法保护模式之际,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难能可贵的是,该法中第一次就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做了明确的规定,开辟了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国家正式立法之先河。但毕竟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才刚刚起步。《法律适用法》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条款仍过于简单,立法技术显得粗糙。知识产权一章中只有区区三个条款 (第51-53条),主要涉及知识产权本体法律关系、知识产权合同与侵权问题的法律适用。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此外,我国立法与涉外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现实严重脱节,尤其是忽略了现代科技尤其是互联网语境下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但无论如何,《法律适用法》为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与依据,可以预计,契此我国知识产权冲突法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三、知识产权冲突法之造法方式
在过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国内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了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内容。然而近来,国际冲突法学界的争论转向另一个主题,即这一部门法的创制方式,特别是由于海牙《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 (DHJC)谈判被搁浅,而美国法学会以软法模式启动了其知识产权冲突法项目 (ALI原则),知识产权冲突法的造法方式问题愈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学者谓之体制性(institutional)问题。 “体制问题可以在许多方面对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内容产生重要影响。象知识产权国际公法一样,知识产权冲突法的造法过程中,也必然渗透越来越多参与者的政策诉求。”[1]那么,知识产权冲突法的造法应在何种“体制”下进行呢?是否应继续沿以传统的国别冲突法形式,还是应采取多边条约的路径?是否应通过日渐成为当代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软法”模式来实现,还是通过国际参与者的合作形式 (当事人意思自治)更为可取?国际社会经历国际知识产权公法立法的僵局过后,掉头转向知识产权冲突法保护。伴随这种趋势,是探寻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方式的努力。
如前所述,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上世纪90年代试图依据欧洲《布鲁塞尔公约》的框架创制一个关于管辖与判决的综合性条约。在多边条约路径的支持者看来,知识产权问题应按一般民商事纠纷处理,并希望象10年前将知识产权纳入WTO法律框架一样,将知识产权问题纳入一个多边的管辖与判决公约范围之内。然而,《海牙公约》的谈判经历也许可以说明,通过一个宽泛的管辖与判决公约很难解决棘手的知识产权问题。《海牙公约》没有充分考虑跨国电子交易中知识产权的挑战,这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即使这样一个包含知识产权问题的“大公约”获得通过,然而将知识产权合并在《海牙公约》中与合并在WTO制度中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WTO制度中并入TRIPS协议,其直接利害关系是成员的义务受WTO争端解决制度支配,并通过其贸易强制机构执行。《海牙公约》并没有建立具有监督权的司法机构以确保公约的实施与解释,而是通过要求内国法院根据公约的国际性质、必要的统一性以及其他缔约国的判例法解释公约以达到解释的一致性,没有全球性的司法架构可供私法当事人选择。这是学者怀疑其执行力将大打折扣的原因。
又如前述,美国法学会致力于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创制,ALI原则项目以“软法”的形式出现,“硬法”方法显然不为当前的政治气候所能接受。尽管冲突法向来有属于本地法的悖论,但ALI显然期望其项目获得国际影响力,因此它委任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共同报告人以及一个全球性顾问团体,还加强与海外平行项目的交流,以增添其价值。尽管有这些努力,ALI原则的通过并不一定导致外国法院或者外国立法机关大量的引用与信赖。在这一软法形式下,内国法院很可能借用一些条款用于填补内国法律的空白。然而有选择地采用不同原则是存在一定风险的。现有方法没有厘清冲突法制度中管辖、法律选择以及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者之间固有的关系。这是软法方法不可避免的风险。欧盟委员会的观察不仅强调创制知识产权冲突法不同体制的选择,更强调细节水平以及规则勾勒的无条件性。[1]正如Paul Stephan在他的有关私人立法的著作中所表明那样,“在通往统一标准目标的细节性与为达成协议而调和不同观点的一般性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参加人员的范围越广泛,达成协议的几率就越低。毫无疑问,冲突法的目标理应是达成一些普遍性规则的框架,据此不同的实体法可以共同存在。然而,学者担心一般性框架不足以解决跨国知识产权纠纷,只有绝对统一的冲突法规则才能保障冲突法目标的实现。尽管ALI原则有多方角色的参与可能影响原则的内容,然而,有学者还是认为,一个纯粹的国际协定比ALI项目这样的软法方法更为可取。
一些学者认为解决国际贸易中法律多样性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授权当事人选择法院以及他们希望用于调整其法律关系的标准。[7]私人当事人显然可通过在合同中规定法律适用与法院选择条款的方式来改善对于分散内国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知识产权冲突法的不完善性。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选择法院条款有助于这一策略的实施。ALI原则以及MPI建议案中都包含法院选择条款。实际上,这一方法只不过证明这样一个现实,即通过私人行为创制跨国标准比国家立法更容易实现。然而,依赖当事人意思自治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限。这一方法缺陷之一是,它只规定当事人事前存在合同关系的一小部分案件的解决办法,而大多数跨国知识产权案件并不属于那些种类。况且,如果网上知识产权交易可能由权利持有人通过非协商合同方式创制这样的关系,那么将难免出现海牙谈判中所遭遇的问题。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不考虑消费者参与选择法院或者准据法协商过程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这是海牙国际《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仅限于B2B合同的原因。第二个缺陷是,确认当事人意思自治意味着某些政策目标可能很难实现。知识产权法中有实体的公共政策的成分,国际知识产权是内国与国际标准平衡的产物。不加控制地转向当事人意思自治忽略了这一法律的尺度。
以上几种选择看来都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冲突法制度。近年来,国外有学者主张鼓励国内法院统一不同的国际知识产权的价值及政策,并创制调整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实体标准。这一选择的实质是允许内国法院通过在国内法规定的策略空间中创制一个知识产权冲突法制度。比如Dinwoodie教授建议允许法院通过综合内国与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对侵权诉讼案件进行合并判决,并鼓励内国法院创制调整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的实体标准。Dinwoodie教授建议,创制以供法院援用的这种实体法源可包含国际协定与惯例、内国或区域的法律以及冲突价值。法院从其中提炼出能反映所有法源下面潜在的价值的实体法。[8]195-210Dinwoodie教授的这些建议显然遭到学者质疑,理由之一是这超出了法官的权力能力。确认同一的“核心”知识产权价值是相当困难的,因而创制超国家标准是不切实际的。况且,知识产权法律国际化进程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即使某些特定的知识产权价值可能被认同,然而它们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的。[9]此外,通过内国法院创制实体标准也不是法院所应承担的合适的任务。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规则导向且不承认判例效力的大陆法系国家法院来说,这一方法无任何意义可言。
综上所述,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冲突法的国际立法还将在曲折中演进。这个由国际交往实践提出的问题最终需回到国际交往实践中加以适当的解决。这可能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国际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甚至价值观念的国际整合过程。由此看来,知识产权冲突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很难改变单个国家冲突法架构的现实,知识产权冲突法的主要渊源仍将来自国内立法和司法判例。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行是做法是加强对知识产权冲突法制度的研究,发掘国际或国别的优秀知识产权冲突法研究及立法成果,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冲突法立法提供借鉴。
[1]Graeme B.Dinwoodie.Developing a Privat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Draft Prepared for Northwestern Colloquium [EB/OL].http://www.law.northwestern.edu/colloquium/ip/dinwoodie.pdf,2007 - 12 -26.
[2]J.J.Fawcett & Paul Torremans.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K),1998.
[3]Marta Perteqas Sender.Cross-border Enforcement of Patent Rights:Analysis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杨长海.电子时代知识产权跨国诉讼的示范法 [J].电子知识产权,2007,(12).
[5]吕岩峰.知识产权之冲突法评论 [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6).
[6]何艳.知识产权国际私法保护规则的新发展 [J].法商研究,2009,(1).
[7]Paul B.Stephan.The Futility of Unification and Harmo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J].VA.J.INTL'L.,1999,(39).
[8]Graeme B.Dinwoodie.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itigation: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Norm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Conflict of Laws[M].Tübingen:Paul Mohr Verlag,2005.
[9]Graeme W.Austin.Valuing“Domestic Self-Determination”In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prudence[J].CHI. - KENT L.REV.,200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