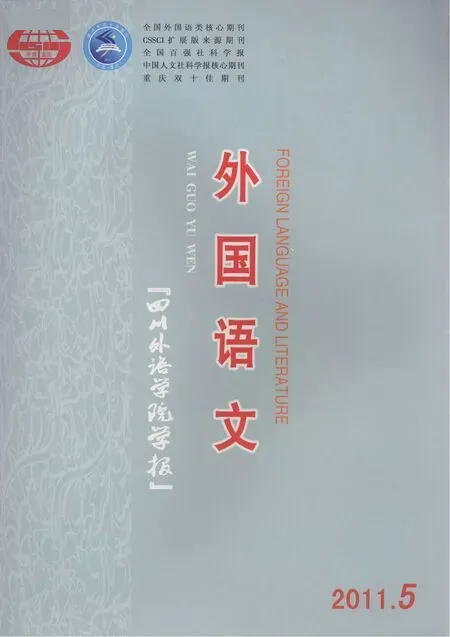刀锋上行走的毛姆与神义论的难题——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视角解读拉里的自我完善之路
董元兴 李 慷
(中国地质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英国小说家威廉·毛姆(William Maugham)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作品《刀锋》(1944)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形象。其中不时游离于故事之外的拉里尤其引人注意:他因为经历了战争中的丑恶而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是丢下了未婚妻和工作,散掉了自己的财产,通过读书和四处游历去寻找人世间为什么会有恶的答案,最后回到美国当了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当前对拉里的人物原型以及所反映的小说主题的研究大都围绕毛姆或者拉里的生活经历。如果能够从作者本人和拉里所阅读的哲学、宗教和文学作品中挖掘其共同主题,就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毛姆所赋予拉里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
一、毛姆与韦伯的共同难题
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毛姆是将自己阅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体会移植给了拉里。比如,毛姆在谈到他自己读哲学的经历时,曾说笛卡尔的文笔使他着迷,感觉就像“在湖泊里游泳,湖水是那么清澈,直见湖底,晶莹的波澜让你心旷神怡”;斯宾诺莎则让他感觉像是在“仰望巍峨的群山”[1]36。小说中拉里也认为读斯宾诺莎“象乘一架飞机降落在巍峨群山中的一片高原上”[2]80;而笛卡尔的文笔是“那样的痛快、文雅、流畅”[1]86。
其实,无论是从毛姆本人还是小说中拉里的读书过程来看,其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要探究人世间为什么会有恶,即神义论(theodicy,也译作“神正论”)的答案。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在他的《神义论》一书中指出神义论的核心含义就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能够容忍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恶呢?”[3]4。为无辜的苦难提供合理的解释一直是东西方思想中面临的共同难题。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探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就是以无辜的苦难为考察核心。他在1919年发表的《以政治为业》这篇演讲稿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治家们能否出于为善的目的而采取道德上有害的手段。他认为政治家往往面临着两种对立伦理的选择: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是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而后者是必须考虑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4]107。问题是政治家为了达到善的目的,很多时候不得不采用道德上有害的手段。韦伯就此提出了关于无辜苦难的问题:上帝既然是全能而仁慈的,怎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让它充满无辜的苦难?[4]110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和毛姆比较推崇的得救之道都是印度教的《奥义书》。为什么小说里感情丰富的美国青年和现实中冷静的德国学者最后都会选择东方古老宗教来解答神义论?这里有必要比较韦伯与毛姆对于西方思想中无辜苦难主题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于印度教的理解。
二、毛姆与韦伯对西方苦难意识的解读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毛姆和韦伯对于基督教中神义论难题的解读。尽管毛姆在《刀锋》中并没有专门提及拉里对于《圣经》的研究,但在小说中有多处显示出拉里对于上帝存在与否以及神义论的困惑。拉里在向伊莎贝尔解释他为什么不回芝加哥,而要留在巴黎的时候,说到他的问题就是“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有,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1]80。而在小说的第六章里,拉里在与小说中的毛姆长谈时,就提到在修道院里对神父们提出的疑问,即“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1]298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最后谈到政治家所面临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种选择时,也指出“世界的无理性”问题是“推动着所有宗教发展的动力”[4]110。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里讨论神义论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约伯记》这个故事的意义的。他认为神是全能的信仰与世界上的无辜苦难构成了难以解答的矛盾。而这个问题会使人们认为“在彼世的神与一再卷入新的过恶的人类之间存在着一道极其巨大的伦理的鸿沟”[5]180-181。所以《约伯记》的故事会使人们认为神的行为是凡人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对于什么是正义的观念是无法用来裁断上帝的行为的。这个解释也正好说明了小说中的拉里为什么会难以相信有这样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上帝存在。
此外,韦伯和毛姆还解读了西方哲学家们对于神义论的解读。作为神义论的提出者,莱布尼茨指出我们的理性常常面临的困惑就是关于恶的产生和起源的问题。[3]20对此,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就必定是全能并且全善的,因此他所创造的世界也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对于恶的产生,莱布尼茨认为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并不表示这个世界没有恶,只是说这个世界善超过恶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可能的世界都高[3]30-31。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已经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了。这就是莱布尼茨所谓的乐观主义。很显然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乐观。那些善良而无辜受苦的人是无法相信为什么应该是他们受到这些苦难的。
除了宗教和哲学作品,韦伯和毛姆还分析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对于无辜苦难的诠释。《刀锋》中的拉里在巴黎时读了几乎全部的法国文学和希腊原版的《奥德修纪》[2]79。到了德国波恩以后,他又开始读德国的文学:歌德、席勒和海涅等[2]295。这些作品中就有探讨神义论的主题。例如,毛姆本人非常推崇的法国文学中就有伏尔泰的《老实人》。毛姆自己在谈到读哲学的乐趣时,就特别强调自己每当要写长篇小说时,就会重读一遍《老实人》,以便希望自己能写得像《老实人》“那样流畅、那样优雅、那样机智”[2]36。而《老实人》恰恰是对莱布尼兹的乐观主义神义论的讽刺。
伏尔泰在该小说里借邦葛罗斯的遭遇讽刺了莱布尼茨的那种盲目乐观的人生哲学。在该书的第一章,邦葛罗斯就试图论证天下事有果必有因,在此最完美的世界上,男爵的宫堡是最美的宫堡,而男爵夫人是最好的男爵夫人[6]9-10。但等到了第三章,这个宫堡教师就变成了一个身上长着脓包、牙齿乌黑的叫化子。他向老实人讲述了男爵城堡和里面的人如何被保加利亚士兵侵占和残杀。[6]18在邦葛罗斯还在宣扬个人的困难造成全体的幸福时,他和老实人乘坐的船遭遇了飓风,刚逃上岸,又遇到了地震,结果邦葛罗斯被当成魔鬼附体而被吊死。[6]25这显然是对莱布尼茨的乐观哲学的嘲弄。
而毛姆和韦伯都讨论过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就是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正是反映了善良的人所遭受的无辜苦难。毛姆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指出它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主题是像孩子那样的无辜者应不应该蒙受苦难的问题。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就指出只要是读过这部小说中的人,都会记得《宗教大法官》那一节中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即目的能不能为手段辩护的问题。[5]109
托斯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其中《叛逆》一节里,伊凡给阿辽沙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土耳其人会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一位有教养的老爷和太太就用树条揍过他们亲生的女儿;一位将军仅仅因为一个农奴的孩子弄伤了他的一只猎狗,就要一群猎犬把这孩子撕成了碎块。[7]266在伊凡看来,即使到了审判日那一天,这些无辜受苦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和那些折磨他们的人在上帝的启示面前拥抱和解。在后面一节《宗教大法官》里,伊凡讲了自己写的一个故事:耶稣重新降临人间,给人类带来祝福。红衣主教认出了他,却把耶稣投进监狱。晚上主教来到狱室对耶稣说,人们所关心的是寻找那可以使大家一齐信仰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会用刀剑互相残杀。[7]285这就揭示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疑问:我们是否会为了自认为是最终的天堂而对别人实施伤害乃至残杀?这正是韦伯所指出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困境。
三、印度教对毛姆和韦伯的启示
相对于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而言,在《刀锋》和《以政治为业》中,毛姆和韦伯着墨较多的就是印度教的奥义书。毛姆在小说的开篇引用了《迦托—奥义书》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1]1可见印度教对于该小说的影响。而在被作者称为可以“跳过”的第六章里,拉里具体谈论到了印度教的奥义书,并且毛姆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这次谈话,我也许认为不值得写这部书”[2]283。可见毛姆想要通过小说传达给读者的对苦难的解答中,重点就是印度教的《奥义书》。韦伯在进行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时,就指出其中能够给神义论提供理性上的满意答案的是以下这三种思想体系:即印度的业报、祠教的二元论、隐身之神的预定说。[5]472
《奥义书》对无辜的苦难是如何解释的呢?印度教的《奥义书》的梵文字面意义即“坐近”、“亲近”。其书名给人的印象就是虔心求学的弟子坐在老师身边,听老师讲道。通过一个婆罗门与死神的对话故事来阐释关于死亡的教义。年轻的婆罗门那启凯也多(Nachiketa,英文译名采用Prabhavananda与Manchester的英译本)因为其父亲一句要将那启凯也多献给琰摩(Death)的气话,而真的去找了琰摩。琰摩被他的诚信感动,答应帮他实现三个愿望。那启凯也多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想知道死亡的秘密。琰摩在给那启凯也多教授大梵(Brahman)之时,就指出大梵是旅途的终点,是最高的目标。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这个大梵,其学习之路就好比“有如利刃锋,难蹈此路危”。而最终只有通过这条像刀锋一样的道路,人们才能够摆脱死亡的束缚。
毛姆在《刀锋》中所要传达的正是这样一层含义,即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都会犹如在刀锋上行走一样,稍不留神就会遭致失败。谈波登最后被欧洲虚伪的上流社会甩了,马图林在经济大萧条中破了产,麦唐纳禁不起酒的诱惑而遭致非命。而拉里自己何尝不是也在刀锋上行走:要追求无辜苦难的答案,就没法和女友结婚;要追求心灵的平静,就要抛弃财产,到煤矿和农场干体力活,并经受精神和肉体的考验。
在《唱赞奥义书》中,则有对轮回报应的解释。该奥义书指出,行善的人有望在来生获得好的命运,行恶之人则正好相反:维在斯世行善行者,有望生于善胎,或生于婆罗门,或生为刹帝利,或生为吠奢。若在斯世行恶行者,其事且将为入乎不善之胎,入乎犬,或野彘,或战陀罗人之胎。可见,在印度教看来,决定来世命运的是在今生的行为是向善、还是向恶。这种轮回导致的结果就是“果又生因,因又生果,业力之流转无穷,生死之轮回不已”。所以,我们今世遭受的苦难是因为前世的过错,而我们想要来生获得幸福,就要在今生行善。
这种因果轮回的理念无疑是想通过一种理性的解释来回答神义论的难题。所以,韦伯在《印度的宗教》中就指出该教的两个基本宗教原理,即灵魂轮回信仰(Samsara)与业报(Karma),使得该教义具有一种彻底的味道,即前世的功德与过恶决定现世的命运,现世的功德与过恶则决定来世的命运。[5]154因此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比较了能够给神义论提供比较满意的几种思想体系之后指出,其中能在形式上给予神义论最完美的解答的就是印度教的教义。[5]183
相对于韦伯的冷静分析而言,毛姆更多的是赋予拉里对印度教的感性认识。例如,拉里认为轮回是对世间存在恶的解释:如果我们知道今生所受的恶报是我们前生造孽的结果,我们就比较容易忍受,并在此世努力行善,使后世少受些苦。[2]251所以拉里最后的观点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和丑恶的东西并存的。毛姆自己也谈到,在他从《古兰经》、《圣经》、佛教,希腊神话一直读到奥义书的过程中发现《奥义书》的精神是属于超然物外的,并且它成了所有生命的源泉。[1]58印度教的轮回信仰对毛姆的影响很大,他在临死前就和他的侄子罗宾·毛姆谈到了对于人世间邪恶的解释。毛姆要他的侄子不要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就消失了,而是进入了涅槃轮回。
四、毛姆和韦伯的选择
虽然毛姆和韦伯都选择了东方的印度教作为神义论的答案,但隐居修行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韦伯认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就要意识到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起来。他在这篇演讲的最后指出:对于政治家来说,即使这个世界愚陋不堪,不值得为之献身,也要能无悔无怨。[4]117而面对二战的残酷,毛姆显然已经没有韦伯那样的自信,认为可以依靠政治家们的自我道德约束来为普通百姓提供幸福。《刀锋》出版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故事中的人物虽然主要生活在一战后和大萧条时期,毛姆也没有提及希特勒的上台,但从拉里的精神探索过程来看,不难看出在二战前的欧洲,西方的思想精华已经无法为现代西方人提供精神的避难所。正如《刀锋》的译者周煦良所指出的:小说中虽然没有涉及纳粹的兴起,但是小说所反映的欧洲的精神空虚已足以说明为什么纳粹主义能够乘虚而入了。[2]10
通过比较韦伯的《以政治为业》和毛姆的《刀锋》,不难看出二人都是通过比较东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关于无辜苦难的主题来为神义论寻找合理的解释,而《奥义书》则从轮回和业报的角度为他们提供了形式上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与韦伯所坚信的政治家应该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起来所不同的是,毛姆为拉里提供的是一条普通人应该担负起自己责任的自我完善之路。
[1]毛姆.毛姆读书随笔[Z].刘文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毛姆.刀锋[Z].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3]莱布尼茨.神义论[M].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4]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韦伯.韦伯作品集宗教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伏尔泰.老实人[Z].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7]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Z].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