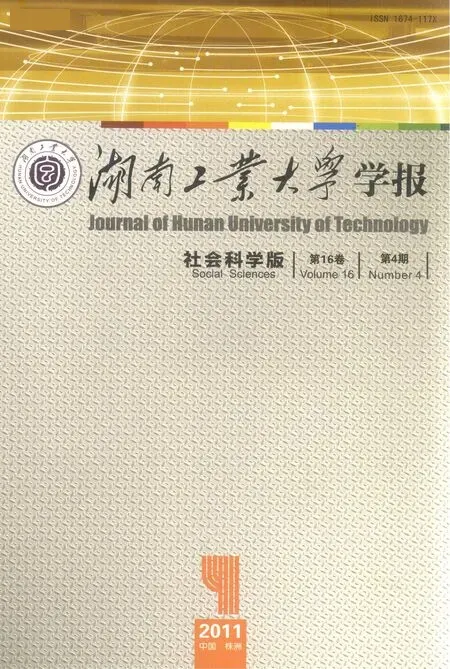个体身份认同与乡村历史叙事
——王青伟《村庄秘史》中的乡村历史叙事探析*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个体身份认同与乡村历史叙事
——王青伟《村庄秘史》中的乡村历史叙事探析*
陈娇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王青伟的《村庄秘史》以不同人物个体身份认同的艰难和失败的故事,呈现了乡村社会的颓败和崩溃,隐喻和折射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失落处境及其所面临的严峻迫切的身份认同问题,体现了作者对乡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以及中国与西方等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
《村庄秘史》;身份认同;乡村历史叙事;寓言写作
以文学形式演绎乡村历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传统。王青伟出版于2010年的《村庄秘史》承续了这一传统,以对个体生命身份认同的艰难和失败经历,呈现了乡村社会的颓败和崩溃。透过这部作品,我们或许可以撩开新世纪乡村历史叙事帷幕的沉重一角,窥探到乡村社会崩溃背后作者的深重文化隐忧,及其对全球化语境中乡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与西方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 个体身份认同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村庄秘史》标题中就含有“秘史”两字,但是与《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秦腔》等乡村历史叙事不同,它不是以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个人之间的欲望纷争及乡村社会的日常场景描写等来直接演绎乡村秘史;而是叙述了乡村——老湾众多个体生命的身份找寻和认同的故事。《村庄秘史》中几乎都是身份可疑的人物,他们或者企图抹去自己暧昧或不光彩的历史,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处,因此无法追溯自己的历史;而在现实社会中,他们也是身份模糊、紊乱之人,不能恰当地在现实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也无法确证自己的身份。作品主要以三组人物故事,从社会政治身份、性属身份及伦理身份等方面,演绎和凸显了个体生命对身份找寻和求证的艰难经历。
首先,是章大和章一回的政治身份的认同与求证。章大也叫章抱槐,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共组织。但在被捕中写了脱离组织的悔过书。抗战期间,加入国民党敢死队,参加淞沪战役。如果那时死了,“他的生命就可以在那个瞬间得以永恒,他留在世界的最后履历就会写着革命连同他以敢死队督战官的身份死于淞沪战场载入史册”。[1]55但他活了下来,作了国民党县长,不久被革职回家。解放后,在一所中学做历史教员。他试图抹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重新开始生活。但弟弟章小说他是“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教历史不合适,应该改教化学。[1]69章大于是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一个不能开口说历史的人”,“只能活在现世”。[1]69而一个人没有历史也就无法确认现在。因此,他决心寻找那些他历史上几次闪光点的当事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至死也没有找到,这是一个永远被排拒在主流历史之外的无身份的人,死亡是其必然的命运归宿。章一回刚好相反。他成功地抹去了自己暧昧的历史,成了极左年代“上面”的化身。“谁也弄不清为什么章一回竟然成了上面的化身。开始本来有人质疑过这件事,后来那几个人分别被章一回找去谈话,被谈了话后他们就一个个沉默了,再也没有了质疑声。”[1]199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有人对章一回的最高法庭表示质疑;更可怕的是,当章一回的脸越来越年轻而内心越来越苍老时,他在恐惧中希望通过忏悔、审判来确认自己身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恰当地放入那段特殊历史中去,才会有国族、身份、村落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这一切都被拒绝。由于恐惧、惶惑无法确证自我政治身份,章一回转向血缘伦理身份认同,希望退回母体子宫确认自己。他甚至“觉得叶子就是他的母亲”,于是退化成婴儿,“缩在叶子的怀里……”[1]191最后死在樟树上,成为樟树子宫里一个黑点。
其次,麻姑与蒲月的性属身份认同与坚守。“性属”(Gender)又被译为社会性别,指从社会文化层面对人类性别进行界定。女性作为个体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身份认同有两种情形:一是作为主体自我,通过寻找性别群体的传统来确认自我身份;二是通过认同已有男性中心社会给予女性的角色规范来确认自我身份。因为并非每个女性都有独立的主体性,不少女性的身份更多是通过认同男性中心社会的角色规范(母亲、妻子、女儿)来确认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麻姑属于前者。她来历不明,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老湾,目的是要跟章顺生一个女儿。因为有了女儿,她就可以带着女儿和她的女书,一起去寻找她的来处、家园——千家峒。她相信她来自千家峒,千家峒就是她的家园。她不停地书写像蚂蚁一样的女书,就是为了保持对家园的记忆和抗拒现实的遗忘。当所有有关家园、历史和记忆的女书化为灰烬后,她就再也回不去了,疯了。相反,蒲月属于后者。她的来历很清楚,是红湾“那个男人”的婆娘。章得因为迷恋她的笑,要把她变成自己的婆娘而杀了那个男人。蒲月听从那个男人的劝说,为了救儿子,来到老湾给章得做婆娘,却再也没有笑过。因此,要认同新的社会身份——做章得的婆娘对她来说,相当困难。当章得真的把再娃当自己儿子,计划着要买宅基地,盖房,为再娃娶媳妇时,蒲月笑了,从内心开始认可和接受这个男人和这个新的社会身份。然而,蒲月的生命也随之消失,她化成了“一只硕大的血蝴蝶”飞向红湾,飞回自己的来处、根部。
最后,章义和再娃的血缘伦理身份的认同与求证。与章大相类似,章义也是一个失去政治身份的人。他跟随章小一起参加革命,得到的却是“把腰弯到地上去了”的结果。特别是做了美国人俘虏后,“他所有的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血战沙场都因后来变成了战俘而抹杀掉了。”[1]138当个人历史被轻易抹去,社会政治身份的认同便成为问题。失去政治身份的章义转向血缘伦理身份的确认,希望通过血缘生命的延续来确证自己的历史。但儿子章春“你不是我爸爸!”“你是个俘虏”的话语,[1]152把他内心强烈的身份认同企望击得粉碎。回到老湾,家乡人也不承认他的身份,“他们怀疑这是另一个章义,那个真正的章义应该早就死了。”[1]154“章义彻底掉进了一个虚无的陷阱,因为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1]156他只好奔走于旷野寻找儿子,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相比章义而言,再娃是幸运的。再娃是章得杀害的那个男人的儿子。刚开始,章得看到蒲月和再娃就恐惧。但当拒绝不了他们时,只好接受这一现实。他忍受着巨大痛苦,实施“血脉勾连工程”,为再娃再造血缘,重塑身份。再娃慢慢地对章义产生依恋,两人“就像亲生父子一样”。然而,当“血脉勾连工程”进行到只剩下最后一只蝉蛹时,精血的滴浇却使它变成“蝴蝶花”飞走了。再娃生命中固有的根性拒绝完全同化,特别是他异于老湾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以及死后化成蝴蝶飞回红湾,都体现了认同的艰难和失败。
总之,上述三组人物关系中,不论是前者(即章大、麻姑和章义),他们被排拒于现存社会秩序外,内心充满惶恐、虚无,乃至绝望,因此竭力渴望重新回到秩序中,以确认自己的历史经历和现实身份;还是后者(即章一回、蒲月和再娃),他们成功地被现存社会秩序所接纳和认同,但他们内心仍固守自己的最初来处和血脉本性,属于生命个体本身携带的或原初固有的本质东西始终残存着,强硬地抗拒外在人为的任何同化和塑造。他们最终以死亡或者发疯,宣告了认同的失败。这种一致性的认同艰难和失败结局,昭示了个体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过程中的艰难,以及完全同化的不可能,体现了作者对文化认同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二 寓言写作与乡村历史叙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与推广,中国社会发展快速地汇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步伐更是不断加速,但是广大农村社会却并没有与整个现代化和工业化融为一体,而是呈现出“断裂”现象:广大农村和农民由于无法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2]4-11大量劳动力被迫涌进城市,而进城的“农民工”也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面临着位置和身份的双重尴尬。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在失去适当的资源支持和体制保障后,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状况不仅引起广大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思考,也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关注和担忧。
中国作家内心郁积着的浓厚乡土文化情结,也促使他们承续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情感经验和书写传统,密切关注着乡村社会的变化发展与盛衰荣枯,书写着那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状态、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等。贾平凹就说:当下“农村出现了特别萧条的景况,劳动力走光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原来我们那个村子,民风民俗特别醇厚,现在‘气’散了。”[3]李锐谈到《太平风物》的创作动机时也说:“农村,农民,乡土,农具等等千年不变的事物,正在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惊天动地、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些都使得“衣不蔽体的田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从容和宁静。所谓历史的诗意,早已沦落成为谎言和自欺。”[4]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费孝通所说的“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地,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这种现象,[5]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已然成为触目惊心的现实。一方面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被城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所挤兑和日趋边缘化,被甩在贫困、破败的境地;另一方面,乡村原有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等也在城市文明的渗透和侵蚀中逐渐走向败落和消亡。乡村社会在国家整个现代化和工业化格局中的位置,如同那些漂泊、游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一样,陷入了“城不城,乡不乡”的尴尬处境,崩溃、颓败成为其必然的历史宿命。它再也无法像以往承载无数文人梦想的诗意田园那样,成为现代作家知识分子漂泊、孤寂灵魂的理想寓所;也不能“通过对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并以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2]4以挤乘上现代化的快车。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同样面临着严峻而迫切的身份认同问题。
因此,书写个体生命的身份认同不是《村庄秘史》的主要创作意图,仅是通往作品深层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的象征喻体。事实上,这从作品开篇“祖先的秘密”中对老湾的祖先与神秘历史的追溯,以及“尾声”中对乡村社会现状的呈现也可以看出:
……几乎所有的老湾人都在那边建起了新房。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过的老院拋在了这里,任由它荒芜和坍塌。……每到雨水季节风雨过后,就会轰然倒塌一座久不住人的老房子。因此,现在的老湾一眼望去,全是断墙颓垣和摇摇欲倒的老屋。[1]284
这其实就是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颓败、崩溃的一个典型缩影。作者要书写的正是中国当下乡村社会的颓败和崩溃。但较少挽歌式的感伤情调,更多的是冷峻、严肃的现实思考。虽然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类似新时期乡土小说那种乐观、明朗的答案和前景预示;但是作品结尾:那执著居住老湾旧村梳理和书写“族谱”的老人,或许正是作者对当下乡村社会处境、命运和前景的一个不甚明晰的思考与暗示。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要不了几年,老湾的所有房子就会全部倒塌,唯有那部著作将长久地留赠给永远的老湾人。”[1]285古老的、落后的物质形态的乡村社会或许会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慢慢颓败、衰亡,但是,乡村文化精神及伦理价值传统将永远沉潜在我们活着的乡村人身上,并将代代相传,永远承续和发扬光大下去。这是一种文化本能,也是与生命、血脉相贯通的文化根性,更是文化认同中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作品中再娃和蒲月死后都化为“蝴蝶”飞回红湾所呈现和喻指的。由此可见,《村庄秘史》中个体身份认同的艰难和失败境况,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崩溃、颓败的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失落处境。同时,由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处境、命运何尝又不是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潮流中中国处境、命运的象征喻示?体现了作者对乡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以及中国与西方等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这些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再思考和执著探索的重大问题。尽管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这些问题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被作家知识分子所涉及和探讨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峻而急切地摆在作家们面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错综复杂和暧昧难辨,难以进行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文学作品中的乡村社会是知识分子启蒙情怀、诗意理想的寄寓地,或者是改革开放奇迹与神话的见证;那么新世纪乡村社会则成为作家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精神状态的探测器,成为他们审视和思考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处境、命运与前景的出发地。
《村庄秘史》的故事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驳杂,革命与爱情,生与死,个人恩怨,村落冲突,阶级斗争等交织一起,颇似时下盛行的某些新革命历史小说。作品以不同人物个体的身份认同串联起20世纪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化,依稀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如北伐革命、抗日战争、反右、“文革”及新时期等。然而,这些都是作为模糊的背景存在,凸显于作品前台的,主要是一些魔幻、夸诞事像。《村庄秘史》的最初写作构思产生于1985年,那是一个文学观念、方法及技巧追新逐异的黄金年代,“寻根文学”正式登场文坛,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一时。从作品实际情形来看,作者创作显然深受当时“寻根文学”及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因此,《村庄秘史》不是反映或再现式仿真写作,而是一种寓言写作。张清华曾把寓言写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刻意的夸诞,二是刻意的琐细。《村庄秘史》显然属于前者。它“越出了通常的写真逻辑而变得寓言化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深层的文化病症、心理痼疾与精神危机的洞烛与探微。”[7]不论是散落于作品各处的荒诞、魔幻、变形的情节和事像,如老湾樟树林里小矮人跳舞的幻境、试图抹去不光彩历史的章抱槐在魔镜中与真实自己的相遇、蒲月和再娃的死后化成蝴蝶飞回红湾等;还是每章故事开头所叙述的章一回“变形”的故事,都可以看到魔幻、变形、荒诞、寓言的重重魅影。这些与个体身份认同故事很好地交融一起,不仅使作品魔幻、现实与历史,写实、想象与传奇等交织一体,在艺术审美方面呈现出独特奇异的个性风采;而且也使作品主体故事,即个体身份认同与乡村历史叙事有机相融,成功地实现了借个体身份认同故事,思考和探索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命运与境遇等重大问题的创作用意。总之,《村庄秘史》是新世纪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乡土历史叙事作品。
[1]王青伟.村庄秘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贾平凹,郜元宝.“秦腔”和“乡土文学”的未来[N].文汇报,2005-04-10.
[4]李锐.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前言[M].北京:三联书店,2006:3-7.
[5]费孝通.乡土重建[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17.
[6]费孝通.乡土本色[M]//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7]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11-112.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and 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Analysis of the 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 by Wang Qingwei
CHEN Jiaohua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09,China)
With difficult and failure stori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Wang Qingwei presented the decadence and collapse of the rural society,and reflected the embarrassed and desperate situ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rural society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d their serious and urgent identification issues.Furthermore,it also reflected profound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problem,such as rural and urban,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Rural Village;Identification;country historical narrative;fable writing
I207.425
A
1674-117X(2011)04-0015-04
2011-06-10
陈娇华(1969-),女,湖南郴州人,苏州科技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