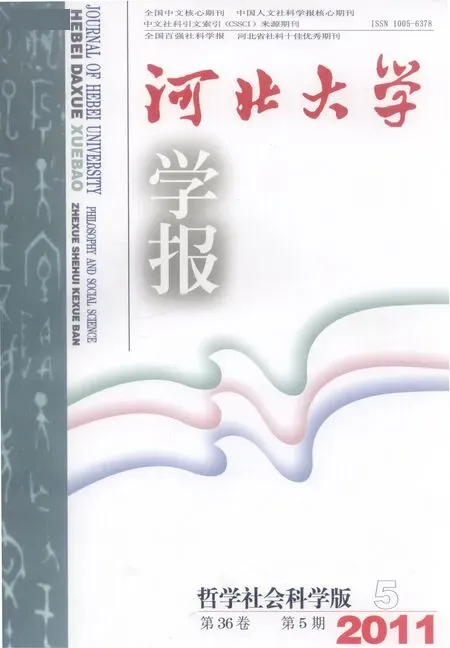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刻——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满杯》
李树春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刻
——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满杯》
李树春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约翰·厄普代克是现代美国文学界最多产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往往通过描写美国东部小镇普通人的生活琐事来揭示人生中的情和爱。以他的短篇小说《满杯》为例,解读作者如何操纵叙事手段,通过一位老人对一生中一系列往事的回忆,呈现出人到暮年时的心理状态和对人生的感悟。另一方面,小说以令主人公感到满足的时刻为主线,将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事件巧妙地串联起来,突显了小说的主题和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约翰·厄普代克;《满杯》;满足感
一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集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自1954年至2008年,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上,是极为多产的当代作家。厄普代克生前共发表长篇小说30部,中短篇小说集15部,诗集10部,散文及评论集13部;他曾分别荣获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福克纳奖、欧·亨利奖等多种文学奖项达19次之多。他的《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1981)和《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1990)曾荣获普利策奖。厄普代克是美国文学历史上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三位作家之一,另外两位作家分别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和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厄普代克是一位具有鲜明写作风格的现代美国文学作家[1]。
厄普代克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Reading),他的父亲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母亲曾做过保险推销员工作,但母亲更加热爱写作,曾担任《纽约客》的专栏作者。受母亲的影响,厄普代克自幼喜欢阅读、写作和绘画,高中毕业后曾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工作,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在哈佛大学期间,他主修英语,并为《哈佛讽刺》(Harvard Lampoon)杂志撰写故事并创作讽刺漫画,大学四年级时兼任该杂志的主编。大学毕业后,厄普代克成了《纽约客》的一名职员,但两年后便离开了纽约,移居到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北边30英里远的一个小镇伊普斯维奇(Ipswich)——这里后来成了他的许多小说的创作背景。然而,厄普代克与《纽约客》的关系并没有断,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的许多诗歌、书评和短篇小说等作品源源不断地在《纽约客》上面世[2]。他的短篇小说《满杯》首刊在2008年5月26日的《纽约客》上。
短篇小说《满杯》(The Full Glass)后来被收入厄普代克先生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我父亲的泪及其它故事》(My Father’s Tears and Other Stories,2009),是该小说集中的末篇,也是他的收笔之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将对该短篇小说的主题、叙事方式和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首先,小说的题目就已经暗示了作品的主题。要理解“满杯”一词所隐含的意思,就不得不先了解美国英语中的一句流行语:“杯子是半空还是半满 ?”(Is the glass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本句问话常用来分析和判断一个人对某种现实情况的态度。从修辞的角度讲,“半满”表明一种乐观的态度,“半空”则表明一种悲观的态度。乐观的态度会使人感到满足和快乐,悲观的态度会使人感到痛苦和悲伤。这句问话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而短篇小说《满杯》里的主人公,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回顾一生,追忆往事的时候,感到的不是“半空”(half empty),也不是“半满”(half full)),而是“全满”(the full glass),这充分体现出主人公对人生的乐观主义态度。
关于厄普代克文学作品创作的主题,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表示:“我对于谈论重大主题没什么兴趣。”[3]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通常以美国郊区小镇为背景,讲的多是普通美国人的普通生活。短篇《满杯》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通过一位年迈的男主人公,回顾了自己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满足和幸福的时光。生活是该短篇的主题,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的核心是情和爱,整个人生又由人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片段构成 ——夫妻之间无声的爱,亲人之间温暖的爱,婚姻之外的激情,青少年时期对异性朦胧的爱 ——汇在一起便是对生活的爱。
短篇小说《满杯》的梗概是由一系列的回忆构成,颇具普鲁斯特风格[4]。其创作手法可谓是意识流,故事的发展脉络随着男主人公的潜意识或思绪慢慢展开,全篇尽是回忆和内心独白。但是从整体上看,其篇章结构明显由三条主线构成。第一条主线是主人公的三个古怪的习惯:因职业原因而养成的思维习惯,渴望感受过程的习惯和年老后睡觉时的习惯。每一个习惯都使叙述者联想起一系列自己的生活经历或感受,整篇小说可以根据这三个习惯分为三大部分。第二条主线可称为“事件链”。如果将主人公忆起的一件件往事排列起来,就会显露出一条清晰的结构轮廓。第三条主线是“时间链”。虽然整篇小说的叙事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显示出明显的跳跃性,但从故事内容上讲,又可分为“老年 —童年 —壮年 —青少年 —老年”的时间链条,而且整体呈圆环状结构,寓意人生圆满。这三条主线清晰,但并非呈直线型,而是相互交叉,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用美国著名作家哈斯莱特的话来说,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诚恳、复杂、富有哲理”[4]。而厄普代克本人在谈及小说艺术时曾经说道:“文学作品应该隐藏着秘密,就像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一样,需要敏锐的读者去发现,去感受。”[3]
三
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满杯》从主人公老年时期的回忆开始。下面我们就随着他的意识之流,了解一下当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都有哪些事情难以忘怀,有些怎样的感受。
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对读者说他“时常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如同一位对自己不十分了解的熟人”。他不进行深度反思,声称这是他多年从事装修木质地板的职业习惯,他只注重“表面价值”,其实是另有隐情,为小说的后续发展埋下伏笔。这种开场白使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幽默,而且令人遐思。
小说的主人公在做了个开场白后,接下来讲了他的第一个怪习惯:
最近我养成了一个令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习惯。夜里刷完牙,用洁牙线清洗完牙缝,滴过眼药水,开始服用药丸的时候,我总喜欢随手端起一满杯水。从理性的角度讲,当我左手拿着药,右手拿杯子,我不想再用左手笨拙地去拧水龙头。不过,这样做也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生活中已没有太多的乐趣,这件小事却很有意思:吃药时总能在白色大理石水池台上看到一满杯水等着我去喝,接着吞下抗胆固醇药、抗发炎药、安眠药和补钙药(这是我太太的主意,因我睡时容易脚抽筋,许是被褥压迫到了神经),同时还要滴上几滴防治青光眼的拉坦前列素滴眼液和缓解眼睛干燥的爱尔康药水。夜里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常感到眼里有梁木,决不是刺,真的就是梁木,以前我从没把钦定本圣经里的那个意象当回事。
喝水吃药成了主人公每天都要做的重要事情,也是他在暮年可以享受的快乐。他这样说道:
不过临睡前畅饮一通却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它有益于健康,倍感甜美,我已习以为常 ——将药片抛到嘴里,把满满的一杯水送至嘴边,大口地喝下,瞬间药片就随之滑到了肚子里,此时品尝到的是无比的幸福。
“这种令人幸福的感觉大概起始于我的童年时代”。此时主人公所感到的幸福和他孩童时所感到的幸福是无比的相似,就是那种口干舌燥时能够喝上满杯凉水的那种感觉。这种幸福感把主人公的思绪带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小说继而生动地描写了他小时候在祖父母家如何玩耍,玩到口干舌燥时,到哪里去喝凉水:
在距我爷爷后院一街区远的车库里,能找到全镇最凉的水。饮水口就在吊挂式滑行门里。那里的水冰凉,喝几口激得你的门牙疼痛。我们的牙医是一名网球运动员,长得又高又瘦,30来岁就开始秃顶了。我15岁那年,因为后臼齿发炎,他给我把它拔掉了。当时他曾跟我说,我的嚼牙将来会有可能出问题,但是我的门牙到死都不会坏。可他哪里知道,尽管我每六个月检查一次牙齿,然而由于经常吃宾夕法尼亚式甜面包圈和欧亚甘草棒,我的牙齿已经严重受损。
喝凉水令他想起了他的牙医,牙医曾是一名业余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使他联想到了学校的网球场,网球场让他记起了他勤劳简朴的祖母经常接他放学回家;他的祖母使他想起了去乡下祖母弟弟家的农场,农场上的泉眼,那里的水,那里的树,那里的人,那里的景。
他兴奋的像只小鸟,总是实心实意地要带我去看他家的泉眼,于是我们穿过高大铁杉树低垂的枝叶,踏着由木板铺设的潮湿而长满苔藓的小路,来到泉水旁。在我的记忆中,在铁杉树的阴影深处,泉水上总是照着一束阳光。蜘蛛状的水黾游弋在水面上,它们的脚下荡起层层金褐色涟漪,散布到清澈透明的沙底。环绕清泉有一圈砂石,其中一块上面放着一个锡质水勺,我的远房爷爷会舀上满满的一勺泉水,笑着把它递给我,露出满口粉红色的牙龈。很显然,他没有保护好他的门牙。
这一系列的联想,这些对再也普通不过的人们的生活情景的回忆和描写,让人读起来一点都不乏味。相反,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无比真实,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美德,感受到大自然的慷慨和美丽,同时无不让人感到一种轻松和快乐,让人回味无穷。
水是生命之源,在短篇小说《满杯》里,水象征生命和生活。“喝水”即体验生命和享受生活。正如小说里的主人公所说,“冰凉的水里好像有一种什么元素,使我这个八九岁的男孩,渴望接下来的一次又一次生命中快乐的体验和令人兴奋的时刻”。
小说接下来话题一转,主人公开始回忆其他令他感到满足的时刻。“忆往昔,一生中还有哪些令人充满激情的时刻呢?”
主人公想起了年轻时的一段婚外情。当年他在做人寿保险推销工作,一天,他利用假日和自己心仪的女人一起到外地幽会。那种情况使他感到激情难以控制,开着租来的汽车,有女人坐在身边,他兴奋得简直都昏了头。
那时我还很年轻,总认为世界尚欠我幸福时光。开着租来的红色道奇牌双座汽车,身边有女人陪着,我兴奋的简直都晕了。那是辆新车,只跑过几英里的行程,如同陌生的车辆一样,你手脚稍微一碰,它就会自动滑行。我的女伴穿着宽肩粗花呢风衣,暖棕色色调,配有西班牙干椒红的斑点,之前从没见她这样穿过。厚密的赤褐色秀发,松散地盘在头后 ——我还记得,当她扭头向窗外看时,整束的秀发瞬间就从玳瑁发夹的束缚中脱落下来。那天我们肯定上了床,不过我只记得躲在车里观赏她那浓密的秀发、迷人的微笑和丰满的双臀。随后我得意洋洋地来了个急转弯,穿过帕塞伊克宽敞而阳光明媚的大街,沿着左边人行道,找到一个自动计时收费的泊车位。
在他的眼里,她的秀发,她的身体,她讲话的嗓音,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无比的魅力。甚至当他忘乎所以违章行车后遭警察查处时,他认为是她的妩媚帮他摆脱了困境,免遭处罚。他回忆道,“她火辣辣的性感展示令我惊叹,令我感动,我想那位警察也有同感。正是她这一招救了我”。他和她不能自持,发生了“邪恶的关系”,并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未能逃脱此类事情的通常结果:“我们的偷情终于还是东窗事发,结果无外乎:我妻子深受伤害,她老公怒火冲天,双方孩子感到不解和害怕。她离了婚,而我没离。”
随后一段时间,他和她仍住在同一个小镇上,难免见面,不无尴尬。其实,虽然他们已经分手,但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惦记着她。这一点在他的回忆中显露无遗:
当看到她和谁调情有可能成功,我就会感到非常愤怒。一想到她那熟悉的胴体以及那温柔令人心痒难挨的缠绵低语,我就难以忍受。她把那些男人带到聚会上来,我还要同他们握手示好。他们的手就像市场上出售的墨斗鱼一样,粘粘的有点肿胀,令我恶心。
他继而回忆起他们性爱时她对他讲的甜言蜜语以及伤害他的话。她说他不够“绅士”,这对他触动很大,“这简直是对我的中伤,但很有启发意义”。他联想到了他所从事的保险推销工作,觉得他就是个粗人,不适合做白领工作,很难每天早上穿着西装革履地去说服比他富有的群体,让他们为自己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死亡投保。因此,他辞掉了保险推销员的工作,离开了那个小镇,到另一个州做起了装修木质地板的生意。装修地板的过程使他感到充实和快乐。
人到老年,主人公其实不仅仅是在回忆那段充满激情的婚外情经历,更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反思和重新评价。
大约过了15年,康涅狄格州传来消息说我的前女友 ——她常用发夹箍着长发,笑容大方优美,双手修长而又灵巧——因患卵巢癌,即将离世。当得知她已去世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倒没有感到多么不悦。她的离世等于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困惑幽怨的生灵,也了却了一桩无法履行的潜在夙愿。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反省了吧。剥去外表,丑陋尽显无遗。
美国小说家哈斯莱特批评厄普代克的《满杯》中存在男子“唯我主义”(solipsism),并以“她的离世等于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困惑幽怨的生灵”为例证,认为主人公心中只想着自己[4]。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分析,其实主人公是在责备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剥去外表,丑陋尽显无遗。”这句话才是小说原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主人公对自己过去放荡行为的道德评判。另外,从叙事的视角来讲,叙述者,即主人公,为男性,因此这样讲也是符合逻辑的,谈不上男子唯我主义。
小说接下来再次话题一转,主人公回忆起了他的第二个怪习惯。每年的十二月,他家习惯以院子里的旗杆为支点,拉上五根挂满彩色灯泡的电线,使之成帐篷状,夜里灯光一亮,人们就会感到像是一棵隐形树上挂满了彩灯。控制灯光的开关安装在室内,自从幼年起,每晚睡觉前都由主人公来把外面的灯关掉。他曾发誓只按开关,不往窗外看,但他总是做不到。每次关灯时他都伸长脖子向外看着灯光熄灭,期望能感受到在按开关和灯光熄灭之间有个时间差,就像先看见闪电,后听到雷声一样。但是按开关和灯光熄灭总是同时发生。灯亮时,给漆黑的夜晚带来节日的气氛,而眨眼间,灯全灭了。他渴望看到这种瞬间变化的发生过程。主人公评说道:
这种感觉就像是入睡前试图留住那无法抓住的瞬间一样。我想,我是下意识里害怕,如果我不看的话,电流就会停滞或者倒流,那么灭掉的将不是灯,而会是我。
显然,对“瞬间变化的发生过程”的渴望,在此具有深刻的隐含意义。小说的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这种看似“怪异”的习惯,欲向读者传达一种认识或观念,即人生短暂,一闪即逝,要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的过程。主人公进一步解释道:
看到像蛇一样蜿蜒的电流通过长长的电线,这种欲望原始于我孩童时代对于羊肠小道的好奇。我喜欢那种一直沿着既定路线前行的感觉 ——如弹丸沿着木槽或塑料槽滚动的感觉,地铁在城市街道下疾驰的感觉,压力使水通过地下管道喷出的感觉,以及河水向大海奔流的感觉。一想到这些现象我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快乐。
现在已年逾古稀,没什么事情会使他有所感觉,唯独此类现象还会令他激动,于是他感叹道:“从事装修地板这个行当,最令我快乐的时刻莫过于完工后关门离去的瞬间,无须我的在场,聚亚安酯油漆也会慢慢变干。”
这句话里即包含着对工作或生活的满足,也难免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丝无助或凄凉的感觉。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是精疲力竭,无法再创造生活。目前唯一有能力做的令人快乐的事情就只有对往事的回忆。
另一件使主人公感到满足的经历始于幼儿园。他从小一直都暗自喜欢同班的一个女孩,但几乎从来没跟她说过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像平行轨道里的两个弹子球一样,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俩就没有交点”。一年春天,他应邀去乡下参加在亲戚家农场举办的舞会,不知哪来的胆量,这次他竟然邀请这位当地美人儿跟他一起去,而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首次与自己暗自喜欢多年的女孩亲密接触令他激动,终生难忘。他这样回忆道:
她那纤细的腰肢轻快地在我的手下摆动,那种美妙的感觉似击鼓,如接球,又如单手上篮而球又弹了回来。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潮湿和肋骨下酥软的玉体,现在因为跳舞绷得很紧。性交对于女性而言,我一直难以想象,性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要求的话,她当时可能会答应我。不过对我来讲,那会把她暴露得太过现实了。
他与她并没有发生性关系。正是这种对异性纯真的爱慕和对自己行为的把控,使主人公把这一美好的记忆珍藏了一生。现在回忆起来还会感到那么美好。
小说接近结尾时,主人公的思绪再次回到了老年,讲起了他的第三个怪习惯,那就是每天晚上上床后,先是看会儿杂志,等妻子来陪他。可是妻子总是沉迷于在电脑上与孙子孙女们交流,或观看英国古装戏。于是他就伸展全身,并大声呻吟三声 ——“哦 !哦 !哦呃 !”他回忆道 :
好似一天过去后最令我幸福的放松方式莫过于痛苦的呻吟几声。起初我的呻吟像是一个信号,妻子听到后便会关掉电脑或电视过来陪我(我特别不喜欢古装戏剧里的英国口音),而今我妻子听了也不会理我。我的呻吟已经变成了一种表演仪式,听众只有一位,那就是永远也看不见的上帝。
老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他感到度日如年。现实无法再使他感到幸福和快乐,他有些无奈,但他似乎又抓到了什么。主人公再次记起了他的那段婚外情。他想起了第一次和那个女人上床时的情景,他是多么的陶醉。他还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情景和感受:
一个夏日的晚上,我们一帮新婚朋友坐在门廊前,抽烟聊天。她穿着迷你裙,翘起二郎腿,看到她的大腿的一刹那,我的嘴巴就干得要命,就像沙漠上的一阵风呼啸过我的脑壳。人的生理欲望就像是恶魔,无法控制。从那一刻起,我就认定她就是我所渴望得到的女人。
主人公的思绪很快再次从潜意识中重新回到了现实。每天晚上,如果妻子不关掉电脑或电视来陪他睡觉,他就很难入眠,而且凌晨半夜经常醒来,听着外面大街上的动静,盼望天亮。每当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在温柔的窗户光亮的照映下,像只可爱的兔子,宁静的让他心动。他此时想起的是她的纯洁和勤劳,看到的是她的美丽,“他再也无法回到潜意识中去,就像个水黾虫,静止地悬浮在水面的张力上,尽享她的优美姿态和宁静”[4]。他等待妻子醒来,起床,并“激活”新一天的生活。对他来说,夜过得真慢,他时睡时醒。可妻子说他睡的时间多,醒的时间少。但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何时醒来,并看到“她用力地挥舞双臂,好像要从睡梦中挣脱出来一样,此时窗户变得越来越亮,妻子掀开被子,整理一下褶皱的睡袍,然后侧身坐起,下床,光着脚在卧室转来转去”。而主人公现已年逾八旬,且已退休,许多早晨还要睡一个小时的回笼觉。他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已不再属于我,我可以解脱了,它已不再需要我”。短篇《满杯》是这样结尾的:
......我左手拿着“延年益寿”的药丸,端起玻璃杯,杯里的水因在水槽上面的大理石板上放了一会儿而变得甘甜。如果我能正确地理解这个怪老头子的内心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向这个现实的世界举杯,在向这个他不久将要离开的世界告别。
厄普代克的收笔之作《满杯》延续了其作品关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创作主题,以垂垂老矣的叙述者回顾一生中幸福片段为结构,但并不特意注重情节,而是自如地利用意识及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将现实、记忆和内心活动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心理旅行,尽显了作者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满足。英国著名小说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在谈到《满杯》时说道,人到老年会变得絮叨和令人烦,而厄普代克则不同,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唠叨变成了艺术,把无趣变成了有趣”[5]。短篇小说《满杯》发表仅七个月后,厄普代克先生就永久地告别了这个可见的世界,《满杯》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满杯》又何尝不是一位现代文学大师献给读者的最后一杯美酒,值得我们珍惜和精心品尝。
[1]HART,JAMES D.TheOxfordCompanionto American Literature [M]. Fifth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784
[2]L EHMANN-HAUPT C.John Updike,Tireless Chronicler of Small-Town America Dies at 76[N].The New York Times,2009-01-27.
[3]SAMUELS C T.John Updike,The Art of Fiction No.43[J].The Paris Review,1968(45):43.
[4] HASLETT A.In John Updike’sThe Full Glass,a Final Remembrance of the Past[N].The Salt Lake Tribune,2009-06-13.
[5]AMIS M.The Master’s Voice[N].The Guardian,2009-07-04.
Moments of Full-Glass Feeling in Life——An Analysis of John Updike’s Short StoryThe Full Glass
LI Shu-chun
(Language Institute,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John Updik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prolific writers in modern American letters.His fictions are usually concerned with the ordinary life of American middle class,focusing on their passions and love in everyday life.This paper,taking Updike’s final short storyThe Full Glassas an example,analyzes how the author shows the reader an old man’s state of mind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life through his natural and complicated narrative techniques.In addition,the story develops with the moments of full-glass feeling the protagonist has ever experienced in his life as its main plot and skillfully moves back and forth in time and space,which in a way emphasizes the theme and shows the author’s love and enjoyment of life.
John Updike;The Full Glass;full-glass feeling
I106
A
1005-6378(2011)05-0120-06
2011-06-10
李树春(1957-),男,河北辛集人,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学。
[责任编辑 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