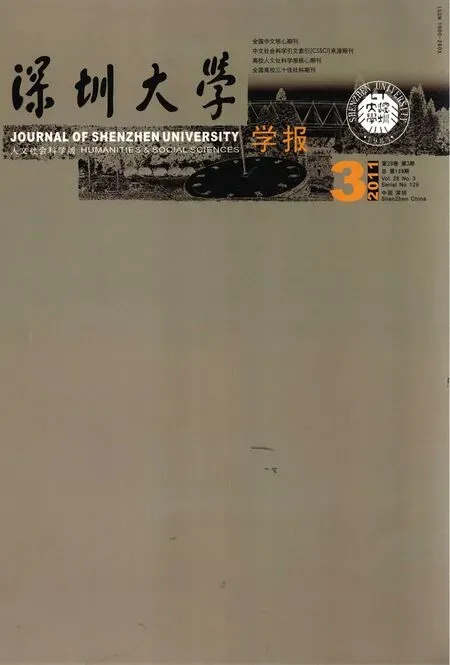春秋“聘问”礼仪与歌诗必类原则
黄震云
(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192)
春秋开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但是在诸侯之间,西周形成的聘问礼仪制度和礼乐规范仍然是社会安定、交流思想的权威规制和方式。《左传》文公四年夏说:“卫侯如晋拜。曹伯如晋,会正。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1]文中赋诗引用的是周颂《清庙之什·我将》中的句子,表示对对方的敬畏。按《论语?子路》说:“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意思是说,孔子强调《诗》的使用功能,举了“专对”作为例子。那么“专对”是俗语还是仪注,值得关切。因为三礼虽言及诸侯,但并没有提到专对礼制。又按《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说: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而,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3]
班固指出,汉武帝立乐府,通过采诗夜诵,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强调诗的信息功能和普世价值。并且和古代进行了对比:“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的古者就是指西周到春秋这段时间,约600年诸侯交接的重要仪注:赋诗。赋诗通过微言相感,也就是聘问歌咏《诗经》的形式,完成外交任务。显然专对的仪注是存在的,程序是在揖让之后,也就是见面时先行揖让礼,然后赋《诗经》章句,说明来意。那么,这一仪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考《左传》文公三年说: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1](P1840)
《左传》引诗用诗约200处,主要来自《诗经》,少数为《诗经》不收,也就是逸诗。文公三年,晋侯与庄叔盟誓,庄叔参加了盟誓的宴会,也就是享礼,晋侯赋了《小雅·彤弓之什》中的《菁菁者莪》。那么庄叔降(下台阶),然后行拜,表示感谢。然后晋侯降,也下台阶,表示尊敬,然后辞,就是辞谢。最后互相登,回到座位,成拜,就是拜礼成。庄叔赋了《大雅》生民之什中的《假乐》,表示感谢。这是《左传》中记载最详细的赋诗专对仪注,专对就是为着目的进行的用诗 (礼乐)来表现的方式。
又考《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幸,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1](P1990)
这是诸侯会同时候的赋诗情况,也是专对的形式。在晋侯举办的享礼上,赋了《大雅·生民之什》的《假乐》,表示盟主明德诸侯,齐侯的代表赋了《小雅·白华之什》中的《蓼萧》,表示对晋国的敬仰,郑国的子展赋的是《郑风·缁衣》,表示对晋国的友好,因此晋侯拜言,表示感谢。但是仍然没有释放卫侯,因此让赵文子做了晋侯的工作,又举办一次聚会,重新赋诗。《辔之柔矣》为《诗经》逸诗。《逸周书·太子晋解》载:“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4]国子赋此诗,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烈)马,以此暗示应释放卫侯。)子展(郑臣)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均万民是西周的正典,具体就是劝赏、畏刑、恤民,春秋时代仍以为三大礼,强调有礼无败。说明礼的价值在春秋时期没有受到影响。晋公子重耳在流亡的十九年中曾遇到不礼的诸侯,因此在专对时就更为谦恭。《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也活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従。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1](P1816)
在秦伯的享宴上,重耳因为没有晋侯承认的正式身份,按照常礼应对,而秦伯只是降一个台阶,而不是降到底,也是基于这样的处境。重耳赋的是《河水》,不见今本《诗经》。杜预注《左传》:“《河水》,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1](P1840)韦昭注《国语》:“河当作沔,字相似误也。其诗日:‘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国,当朝事秦。”[1](P1840)《六月》见于《小雅·彤弓之什》。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说:
晋栾鲂帅师従卫孙文子伐齐。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1](P1968)
《黍苗》见《小雅》中《都人士之什·黍苗》,《黍苗》是宣王时赞美召穆公 (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范宣子赋诗表示亲切友好。季武子兴,就是从座位上起来,再拜稽首是要表示感激之情,增加了敬意。稽首与再拜为感谢的仪注。《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十七年春,小邾穆公来朝,公与之燕。季平子赋《采叔》,穆公赋《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国,其能久乎?”[1](P2082)宴享虽然都有宴会,但享是礼仪的重要形式。在宴会中赋诗,应该是受享礼的影响,享礼一般用在诸侯之间,比燕礼高一个规格。按《仪礼·燕礼》记载的仪注是“:公坐,取大夫所腾解,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坐,莫解,答再拜,执解,兴,立卒解,宾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5]燕礼的仪注两兴两解,还有稽首,比起专对赋诗要复杂一些,但比享礼要简单。赋诗专对是享礼的关联仪注。
诗歌见《小雅.》中的《桑扈之什·采菽》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表示顺从。而穆公赋《小雅》中的《彤弓之什·菁菁者莪》,表示甘愿为君子之才。赋诗充满了应酬的成分。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往往有超越礼制的行为,而首先超越礼制的就是周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1](P1825-1826)
郑伯和晋伯是周王东迁和乃以生存的政治基础,也因此一直受制于两位诸侯。当重耳强大时,享受的待遇就出现僭越。郑伯用平礼就是非礼,诸侯与王平起平坐,当然也是王有不得已的苦衷和处境了。重耳享大辂是享受天子身份。因此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一方面表示重耳明礼尊礼,反复稽首;另一方面,说明奉扬天子休命。其中用敢字,表示反问,反问的方式,正是产生于非礼状态下的矛盾心态,与金文中的敬畏心态不同。西周金文中用很多的敢字,但都不是这样的事态表述的惯例。
诸侯中,像重耳这样的五霸实际上是代天子行政,五霸是西周礼乐制度仍然存在的调和的产物。但是,一般的诸侯或者大夫,普遍并不会接受这样的僭越。《左传》僖公十二年传、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1](P1802)礼是规范社会的法规制度,管仲恪守周礼,显示了齐鲁风范。
赋诗专对是一般情况,也有的以行为对。《左传》襄公十四年说:
夏,诸侯之大夫従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蟜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従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従之。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子命従帅。栾伯,吾帅也,吾将従之。従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1](P1956)
迁延之役,诸侯会同,攻打秦国。《匏有苦叶》,古人多解作刺诗,今人以为爱情诗,但从文字上看是克服苦难前行就有希望的意思,穆子赋诗表达了他的意见,因此叔向开始渡河。按照春秋歌诗必类的原则,诗歌都是用的本意,没有什么寄托。今人解是。又,《左传》昭公十六年说:
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1](P2078-2079)
诗歌用《小雅》的《祈父之什·雨无正》诗句,表现了反对意见。从引用的诗意看,很多只是说明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并不能表示确切到具体的过程行为。有的还只是从赋诗中得到启示。《左传》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古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羊舌职曰:“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武子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1](P1888-1889)
引诗见《小雅》的《节南山之什·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6]带有警示意味,因此得到启发,效法王事,讲究法度。
聘问赋诗中经常遇到僭越现象,上言王室奖赏重耳就是,郑伯用平礼宴请周王等都是这样,但是像管仲这样拒绝僭越的也不乏其人。《左传》文公四年说: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1](P1840-1841)
又检《左传》襄公四年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1](P1931)核之《国语》说: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7]
从两条材料的对比中我们看到,春秋盛行断章取义适用礼乐风气,这是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因为礼崩乐坏,所以礼乐赋诗出现僭越,但是遭到了抵制。这样,就引出了赋诗的原则。按《左传》襄公十六年传说: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请!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领西望曰:‘庶几乎!’比执事之间,恐无及也!”见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従执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鲁及此。”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 ”[1](P1963)
歌诗必类的类就是本义,这是赋诗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违反了这样的原则就是不庭,就要受到盟而讨之的结局。但是,到春秋后期,人们已经普遍不熟悉《诗经》的本义,因此赋诗就进入了引诗句和不用整首诗的诗义的阶段。春秋后期,对诗义的寻求成为风气。《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
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及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准为右。[1](P1822-1823)
诗书被当成义府,而义是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六诗当然就成了六义。赋诗必类和周礼可以说拥有共同的命运。也就是说王权和礼乐一体。《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1](P1820)
显然,秉承周礼规范就是国家有道的体现,就神圣不可侵犯。其理论基础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左传》闵公元年传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従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昬乱,霸王之器也。[1](P1786)
正因为如此,仍然是依礼用兵,礼成为出师的理由。《左传》僖公四年传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1](P1792-1793)
但是,礼的本质是勤政爱民,一统天下,而不仅仅是仪式。《左传》昭公五年说: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1](P2041)
赋诗专对,在春秋后期逐步变得并不严格,丧失功能。主要表现为:
一、以言代赋,结束赋诗。《左传》襄公八年说:
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1](P1940)
春秋赋诗皆在享礼开始,赋诗后对方以诗对。享礼结束时赋诗的并不多见,但不是没有。《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说:“楚薳罢如晋莅盟,晋将享之。将出,赋《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1](P1998)这也是将出赋诗。
二、赋诗不应,规制消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
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1](P1994-1995)。
齐国聘使连《相鼠》都不知道,因此作为笑谈。这至少说明,当时的齐国完全丧失了礼乐教育,其次赋诗专对已经不具有普遍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1](P2061)
三、赋诗断章,用以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1](P2000)断章不是断句,杜预的理解符合事实。但就赋诗说,断章有时候是一章,有时候也会是三章,不完全确定。这表明,襄公后期已经进入实用主义诗学时代。赋诗引诗具有政治功能,因诸侯国都很重视。《左传》襄公十九年说:
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1](P1969-1970)
《鹿鸣之什·棠棣》七章表示兄弟家庭和睦,但宋人贿赂武子,因此武子含糊地说聘宋正是时候,但襄公赋《南山有台》,希望他承载重任,发扬光大的时候,武子不能承受,所以说不堪。由此看来,不仅聘问诸侯要赋诗,复命君王,享礼上也要赋诗陈述。赋诗一般都是整首诗,如上列材料我们看出,也可以赋一章,且位置并不固定。这类材料虽不多,但亦不是个例,时间在春秋晚期。
享礼赋诗具有广泛性,不仅在诸侯之间。《左传》襄公十四年说:
(对曰):“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于是,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1](P1955-1956)
《青蝇》为刺诗,批评小人谗言构怨,《论衡·商虫》说“谗言伤善,青蝇污白[8]。戎本四岳之后,因为主要居住在边疆,因此时间一长,和中原联系很少,语言也就生异。但是使者能够赋《青蝇》之诗,说明戎狄有人专修中原文物,水准很高。又《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1](P2029)
上引材料表明,在齐宋等国,在鲁襄公和鲁昭公时代,赋诗专对仪式消亡。但在鲁国,此风犹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后闻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只见疏也。”公谓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谁敢违君!”公与公冶冕服。固辞,强之而后受。公欲无入,荣成伯赋《式微》,乃归。五月,公至自楚。[1](P2005)
究其原因,诸侯国有了自己的礼乐和《诗》。《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公曰:“善哉!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1](P2016)
上引《卫诗》见于《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6](P296-297)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诗经》将卫诗和邶诗搞混淆了。但是我们认为,不仅如此,这反映了编诗者的选择。同时,《卫诗》名称和《周诗》并存,意味着孔子说的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符合事实。《诗经》的名称也由《诗》变成《周诗》,与《卫诗》等并列。从《左传》赋诗情况看,郑国赋诗皆出自郑风,表明郑国在当时的礼乐强势。在《左传》中郑诗的出现与郑伯宴飨周王用平礼之后开始。但显然,鲁国和晋国没有自己的《诗》,所以所谓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诗。这些国家当时都拥有了自己的《诗》,这些诗的来源,一是西周以来天子的赏赐形成的风诗,二是为享乐制作的礼乐。但是,编定《诗经》的人站在王室的立场,选择了三百零五篇,将这些诸侯的诗命名为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诗三百》之类都是编订《诗经》的时候出现的名称。因此,《诗经》最后编订的时间在孔子时代是合适的。随着新《诗》经的编订,诸侯的诗乐随之失去地位。
[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840.
[2]邢昺.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50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5-1756.
[4]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99.
[5]郑玄注.仪礼[M].北京:中华书局,1998.71.
[6]孔颖达,等.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49.
[7]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8.
[8]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