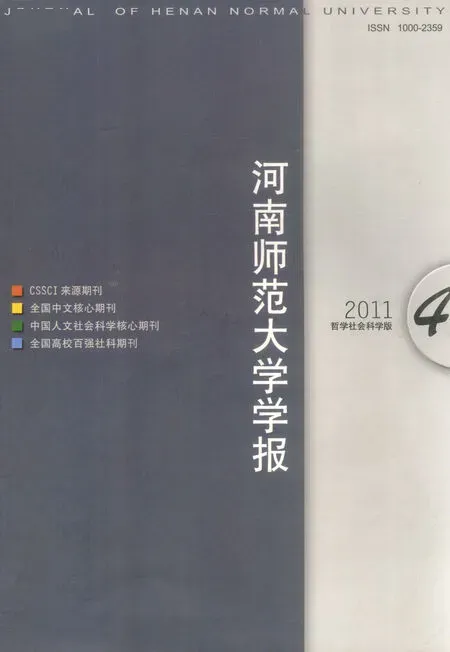狐精故事的流变及其人类精神内涵的演进
黄 果 泉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狐精故事的流变及其人类精神内涵的演进
黄 果 泉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中国古代各类传世故事中,狐精(或谓狐怪、狐仙、狐妖等)故事可谓是源远流长,不绝如缕。其滥觞于《山海经》,光大于《搜神记》,唐传奇愈益精工细密,至清代则蔚为大观,单是一部《聊斋志异》写及狐精的就有八十余篇,其后如《子不语》有四十余篇,《阅微草堂笔记》多达一百八十余篇。
在众多的狐精故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格外关注:不同时期的狐精故事,其中所折射、寄寓的人类精神具有如何的内涵。
本来,狐精概念的外延是不存在的,因为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无法观察并指陈此一对象的实际存在。所谓狐精,不外乎人们根据狐狸的动物原型,赋予某些人类错觉、想象以及精神寄托而虚构出来的。人们的狐精观念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粗加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划分为秦汉、魏晋六朝及唐宋以降三个时期。
秦汉时的狐精观念,无论是作为吉兽,如《山海经》中所言之九尾狐,还是作为妖兽,如《说文解字·犬部》释义的“鬼所乘之”,大体都与早期先民的鬼神观念相关,可以看作原始宗教想象的遗存。质言之,其时狐精在自然属性之外,被赋予了超越于人的神异能力,相对于人类它们是异类,而且是高高在上被崇拜或畏惧的异类。
魏晋时期狐精故事不仅勃然而兴,广为传写,而且明显出现了人形化、人性化的趋势。其一,狐精最突出的神异能力就是化形为人,进而修炼成仙。“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玄中记》),其化形为人的程度,成为它们修炼神通的直接标志。其二,狐精乐于并善于隐迹人间,已经融入了人类社群。它们不仅具人之形貌,与常人无异,而且获得了人的能力及身份:或为博士,“教授诸生”(《搜神记》卷十八),或“好音乐医术之事”(《异苑》卷八),个别的雌狐精,化为“美姿容”的女子,与人间男子相悦,发乎情而止乎礼,持守“父母并在,当问我父母”的人间礼法(《幽明录》),几与人间淑女无异。此类狐精的形貌及性情,已经很难辨其为异类了。当然,魏晋志怪作品在传写狐精故事时,往往强调它们作为异类的自然属性或精怪特性:体有臊气、忌猛犬、尚存三尺狐尾等,以及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特别是异于常人的博学和预知能力。至于狐精之蛊魅人类,也大多出于害人尤其是“吸精”的修炼目的。归根结底,狐精仍旧属于精怪一类的异类。
唐宋以降,狐精故事中的异类属性日渐淡化,而人形化、人性化的特点愈益凸显。这一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狐精的异类属性中,“性”的因素愈益凸显。秦汉时所传狐精作祟手段,不包含性因素。魏晋六朝志怪中精怪开始出现“性”蛊惑,而较之其他精怪如蛇、犬、龟、树等,狐精却远有不及。而且,在狐精诸种异类属性中,最为人们传写的是其善变化与善预知,“性”蛊惑并不突出,以《搜神记》为例,其中与狐(狸)精相关者十五则,涉及“性”蛊惑的仅一则(卷十八《阿紫》)。唐宋以降,狐精故事在明显增多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其中的性别及性的作用。以《太平广记》为例,卷四百四十七至四百四十五共卷为狐精专区,另计其他零散叙述,述及狐精者百则左右,而标明其性别特征的不下于四十则,不少篇目都或隐或显地含有“性”蛊惑之意。二是在狐精的性别中,雌狐数量增多并逐渐成为叙述的主角。魏晋六朝志怪狐精以博学、智计见长,出现较多的是雄狐,即使在偏重“性”蛊惑叙述的故事中,也是雌雄参半。而在唐宋以降的同类作品中,明显出现了狐精雌化倾向,甚至进一步形成了狐与妓相结合的狐妓形象,典型者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任氏》中的任氏,卷四百五十一《李黁》中的胡妇“多媚黠风流”,似乎也属妓女一流。三是狐精与人类交往性质中,人情化乃至非礼法化内涵不断增强。人、狐交往而注入以男女间的性爱内涵,形成所谓的人狐之恋,易于导向缘于个人感官与性情吸引的爱情追求,从而使人狐关系更富于人性化、人情化特性。《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一《冯玠》写雌狐之魅惑冯玠,乃在“本图共终”即白头偕老,爱而不得故“流泪经日”,表明她追求的是真心相爱,不再是单纯的魅人或害人,与魏晋六朝狐精故事中以修炼为目的的性蛊惑迥异。至于《任氏》中的人狐(妓)之恋,他们一见钟情、戏谑同居的结合方式本身,本身就具有背离世俗礼法、自由性爱的性质,而任氏的美丽、多情、忠贞,俨然成为既美且善的完美女子形象,完全消解了狐精故事惯有的精怪色彩。清初《聊斋志异》承继于此,堪称狐精故事的集大成者,所写狐女形象的篇目居一半以上。婴宁、小翠、青凤、红玉等等,这些人间少有的另类“姝丽”们,不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人物画廊添上了一笔笔亮丽的笔墨,也使得狐精故事终于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形态。
从狐精故事的流变轨迹,不妨探索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精神内涵。秦汉狐精故事主要反映了古代宗教信仰观念,而宗教信仰观念的核心是对确认对象的极度信奉与尊敬。无论此一对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想象,是得自传闻还是得自错觉,均信之不疑。狐精故事亦作如是观:在“信”的心理前提下,狐精获得了主体性实存的意义。换言之,狐精观念是先民认知的结果,虽然以今人科学批判的眼光看完全属于神秘认知,其中当然包含着浓重的想象虚构的成分,但其时却是在非自觉状态下达成的。通观中国古代,自秦汉而至明清,狐精故事所具的神秘认知、非自觉虚构的内涵都是相沿不辍的:就魏晋言之,不但是狐精,旁及鬼神均信之不疑,而志怪诸书无非“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唐代,“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敬畏有加(《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七《狐神》),甚至在《聊斋志异》中也不乏描写狐精致人死地、残忍至极的篇什,如《董生》。就此而言,狐精故事如同其他鬼神故事一样,最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神秘认知的精神内涵。
其间当然也有变化。首先,不同时代的宗教精神、文化精神融入狐精故事之中,如魏晋六朝时期,神仙道教兴盛,受其房术修炼思想方法的影响,狐精故事中凸显了“性”的成分;而玄学思潮中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弘扬,不但促进了狐精意象的人形化、人性化,而且大大增进了人妖之间包括人狐关系之间的人文内涵,由此造成狐精故事的变异。其次,社会生活的丰富及其观察、表现视域的拓展,使得狐精故事与其他人事混杂互植,狐精故事成为其他志怪故事、社会故事的片段之一,从而使狐精故事富于其他的社会文化意味。这在唐宋狐精故事中较为突出。如《王度》(《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全文记王度古镜得失始末,其中植入了收治狐精鹦鹉一事;又《昝规》(《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五)叙述主人公因贫卖妻事,末尾乃言“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特别是《任氏》通篇写郑六与教坊女子任氏相遇、相挑、相交之事,几乎可与唐传奇其他男女爱情故事等而视之,而任氏的狐女身份则数笔带过,被完全包裹在层层故事叙述之中了。最后,由于传统“香草美人”的诗性思维及比兴手法,在不触及狐精存在真假值问题的前提下,中国文人大可借助狐精意象所蕴涵的文化隐喻作用,别具怀抱,言此而意彼,《聊斋志异》中那些优秀的狐女故事皆可如是观之。在此类狐精故事中,狐精固有的神秘认知内涵被弃置,具有了自觉意义上的虚构特性,与此同时,狐精故事的狐精主体性地位被彻底颠覆,作者情志成为创作的主体性依据,其中所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精神。
概而言之,狐精故事所寄寓、折射的人类精神内涵,其内在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表述如下:其所发端并贯穿始终的宗教神秘认知,依因于人形化、人性化趋势的增强,社会现实意识及其他文化精神混杂其间,造成了狐精故事内涵趋于复杂、变异,甚至使得狐精观念为其他社会意识所遮蔽、消解乃至置换;特别是“性”、“女(雌)性化”因素的凸显,不仅大大强化了狐精故事的社会意味,而且最终使狐精意象与传统“香草美人”的类比思维、诗性思维相融通,从而完成了狐精故事由宗教精神向艺术精神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