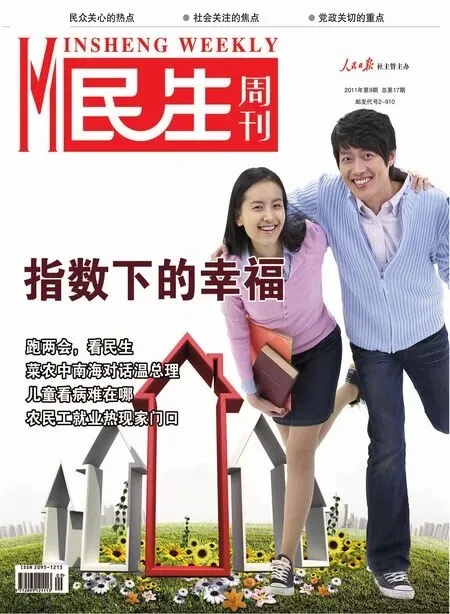守望西部法治光明
□ 本刊记者 陈 晓
守望西部法治光明
□ 本刊记者 陈 晓
2011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会议再次提出解决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短缺、通过司法考试难的问题。
事实上,这一关系西部法官命运的政策早在几年前就被提及。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自2008年起在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800余个基层人民法院试行法官助理工作,根据审判工作需要,符合法官条件的法官助理在将来也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被选拔任命为法官。担任法官助理不需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条件”的法官助理将被选拔任命为法官。
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司法考试分数一降再降,从2004年的335分到2010年的315分。
这一系列规定被认为是为西部法官资格的取得松了绑,有助于缓解西部法官短缺现象。
进入“十二五”规划新时期,我国西部地区法治建设将进一步深化,法律人才需求将日益增加。然而,西部地区法律专业人员始终面临着人才紧缺、流失和断层问题。
据悉,我国律师队伍已经发展到了17万多人,而目前我国西部律师的分布极不均衡,整个西部仅有3万律师,尚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其发展规模、业务技能、管理能力与东部律师相比也有不小差距。另一显著的情况是,“西部地区一个省的律师收入不及一个中型律师事务所”。
尽管伴随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倾斜,也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选择投身西部,为改善现状而身体力行,但是仍然要看到的是,在众多努力背后,依然折射着西部法治的紧迫与无奈。
西部法官荒
来自陕南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表示,全县18万人口,法院共有法官35名,平均每个法官每年办案不足20起,还有许多法官全年一案未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法院法官人均年结案有的达200件以上。法庭每年的收案量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400多件增加到700多件,增长了近一倍。
越边远、越贫困,其案多人少、法官断层的问题就越严重。据报道,在云南,德钦县、镇康县法院只有10名法官,还有一批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不足20人。在南涧县法院公郎法庭,5名干警中只有庭长龙进品一人是法官。他每年办案100多件,而且“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什么都管”。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表示,在中、西部地区的基层,由于大多经济欠发达、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福利待遇偏低等原因,难以吸引符合条件的人才。
2009年颁布的司法改革意见被认为是司法改革领域的一份纲领性文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红认为,改善政法机构的装备和基础建设,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困难地区的政法经费的保障,是司法改革意见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政策之下,物质保障似乎成为缓解西部地区法官荒的主要动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治处副主任安立平介绍,自2006年招录600多名公务员后,基层法院法官短缺现象有所好转,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留不住人,甚至春节前刚刚招录来的工作人员在春节后就提出了辞职,“工资低,生活艰苦,这就是现实”,安立平也很无奈。
受益于国家的定向委培计划,宁夏高院决定今年增加申请名额,在基层招募考生,培养成材后使他们回到当地就业,“这样的法官在当地更有归属感,会长期留下来”,安立平说。
那些西部律师的故事
2010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西部地区首届律师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西部12个省份,包括17个少数民族的50位律师学员参加学习。
这些律师来自蒙古包中、昆仑山下、怒江江边……他们当中有的人是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坐飞机。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当中有的人只能收取老百姓的鸡蛋当作律师费。一位来自四川阿坝州执业20余年的老律师,也是全县唯一的执业注册律师,他说:“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每个月能有1000元到1500元的收入,并且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钱。
培训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出现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西部律师的故事。
来自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吴朝进律师已经做了25年的律师,做律师前,他曾当过7年县司法局的局长,由于当地缺少律师,更缺少懂彝语的律师,他便辞去了局长职务,专心做律师工作。吴朝进说,25年的律师生涯中,他很少接过大案子,收费低的就一两百元,高的也不过一两万元,而办理一起法援案件,政府的补助只有200元。

法律援助志愿者在西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贵州威宁草海律师事务所的陇康副主任是一位彝族律师,他说,威宁县有130多万人口,执业律师却仅有7名,律师事务所也只有1家。“在我们那里,信访不信法现象比较普遍,老乡们遇到法律问题,习惯于找政府、习惯于上访‘闹事’、习惯于托人找关系而不是花钱请律师。我们7名律师一直在坚守,我们也把每个案件都作为法制宣传的阵地。”尽管有点无奈,但陇康律师乐观地面对这一切。
一位来自云南的律师介绍,云南共有454家律所,4000多名律师,但大多数事务所都集中在昆明,发展很不均衡。
记者在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徐建时,他表示,“西部没有律师的县已经从去年的210个增加到230个,他们是律师中的弱势群体”。徐建说,作为律师学院成立后上马的第二个项目,培训班获得了多方关注,计划今后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第二届将于2011年下半年举办。
徐建坦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费”,首届培训班支出约30余万元,这些经费全靠自筹,徐建表示愿意和社会慈善机构或基金会共同合作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徐建说,“我们听过的西部律师的故事不多,见过的西部律师所受的艰辛就更少,通过交流能使我们及全行业、全社会都能真实地了解西部律师,了解他们职业的艰辛、生活的简陋,以及他们的坚持守望、拼搏追求。”
志愿者走进西部
由司法部、团中央发起,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等6家单位共同组织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于2009年开始实施,目前已有三批志愿者走进西部。
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会长张秀夫介绍,行动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定期轮换的机制,每年从全国律师队伍和政法院校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律师和优秀学子,到全国无律师的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在志愿服务期内,每名律师志愿者每年至少无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0件。
浙江义乌律师陶旭明是首批进入西部的志愿者,2009年他放弃几十万年薪来到贵州省长顺县做起了法律援助,在这里他亲眼目睹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法律观念的淡薄,往往利益争夺很小的案件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天大的纠纷。
在当地传播法制观念成为陶旭明的愿望,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办理了23起案件, “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才是最终渠道”,陶旭明说。
北京律师马兰在甘肃省山丹县服务,对马兰来说,认真研究案情,用心思考,永远都是一个律师应该时刻记住的办案准则,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前线,女性志愿者对弱势群体的伤痛和疾苦有更多共鸣,她们的行动也为法制赋予了更多柔情。
2009年由香港明星吕良伟、关之琳等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法治阳光基金,成立当天即筹资达1100万元。据悉,该基金会将为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提供全面的资金支持。
基金会工作人员钟卫平却始终在为基金会的运作而头疼,由于没有知名度,许多人对他们的工作不了解,甚至传来质疑的声音。“我来自农村,深深了解农村地区法律纠纷多,人们法律意识淡薄的真实情况”,钟卫平感慨道。
“所幸我们有这些志愿者,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感动”。谈到志愿者,钟卫平对他们的顽强、敬业表示敬意,他表示,有了他们,“我们的事业定会越做越好”。
西部增速之后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部地区案件单一,主要集中在刑事、民事等传统案件。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治处副主任安立平表示,在宁夏,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这几年来民商事案件占了总案件的半数以上,伴随西部的发展,经济活动的频繁,西部的法律诉求也日益改变。
曾任中国首位律师协会会长的徐建长期服务于律师行业,对律师行业的一般规律十分熟悉,他表示,解决西部法律人才短缺的根本在于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达了、当地有了案子,律师就能稳住”。
这一观点得到了各方印证。去年两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甚至提出这样的建议,“要实现能动的司法目标,除了对西部法官进行必要的培训之外,还要让发达地区法官到西部工作,可以切实提高西部法官的专业化水平。”
一年已过,再次时逢两会,西部法律人才缺失的话题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并呈现出更加紧迫的局面。伴随着西部经济发展的推进,西部民众法律意识逐渐提高,法律服务市场需求不断扩大。
□ 编辑 刘文婷 □ 美编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