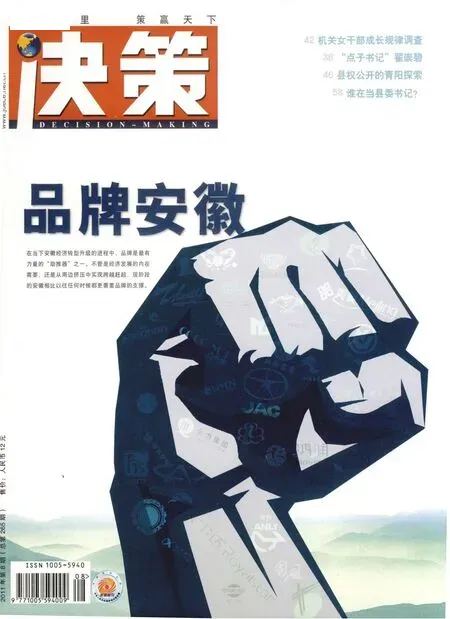群众史观与官民逻辑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现代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社会服务之中,除了为了缓和社会关系,增强社会认同外,还在于可以“用服务换管理”,“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并且用社会服务的“外部经济”效应来支撑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137次提到“人民”这个词汇,44次提到“民主”概念,最后发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警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遗憾的是,在最近发生的多起公共事件中,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应对思路和方式似乎偏离中央的要求很远,其迟钝笨拙令人匪夷所思,甚至不及常识。结果不仅不能让当事人满意,甚至造成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局面。
固然,造成这类结果的因素有多种,有的具有强烈的个案性和偶然性,但是不同事件、熟悉的行为、类似的结果足以说明,它们背后隐藏着某种共同的逻辑,即“官民”逻辑和“敌我”逻辑。这两个逻辑分别主导着事件发生的两个阶段。在问题发生和发展阶段,一些官员在判断问题上使用的是“官民”逻辑:问题出现后,先是推卸拖延,视为“刁民”惹事,导致小事变大,大事激化,矛盾成为冲突。在问题激化和应对阶段,一些官员尤其是决策者很容易就落入了“敌我”逻辑,将冲突的发生判定为“敌对势力”作祟,于是“上手段”,找“敌人”,用警力,很多事件的平复是通过恫吓甚至暴力手段达成。虽然实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在相关人内心埋下了怨恨。这两种逻辑显然有悖于我们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群众史观”,都离“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预期相去甚远。
既然我们的制度设计理念是“群众史观”,为什么“官民”逻辑和“敌我”逻辑依然根深蒂固,时有蔓延的趋势呢?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制度设计和运行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其提供了土壤,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和执行的不得力为其提供了机会。
“官民”逻辑说到底是封建残余,内含上下等级关系。官是命令者,是“父母”,是“大人”,行为高尚者为“清官”;民是服从者,是“臣子”,是“小民”,不服从即为“刁民”。按照这个逻辑,一些党政干部潜意识地将自己等同于“官老爷”,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根本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于不同意见则加以压制甚至打击,斥为“不和谐”之音。在多元社会中,不同声音说明了社会充满了活力,本是“问政”、“问需”和“问计”的重要资源,但是一些地方部门的主政者却将其视为影响政绩工程,破坏执政形象的消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采取任何举动也都能心安理得了。
“敌我”逻辑的根子是阶级斗争观。虽然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已有30多年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是阶级斗争意识依然在许多领域潜伏着,并且在一些问题的应对过程中浮现出来。当然,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用阶级划线,判断对错的方法简便易行,更重要的是,也能在问题无法收拾的时候,找到最后的“黑手”,把责任推给莫须有的“敌人”。
这充分说明,要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将“臣民”逻辑、“阶级”意识改造为权利逻辑、公民意识还有着漫长的道路和艰巨的任务。作为把人的管理和服务作为核心的社会管理,要真正地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除了要不断推进制度改革外,更应该着力消除潜藏在制度背后的那些有毒的理念和逻辑。
——从于欢案“官民”互动和江歌案的中日舆论反差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