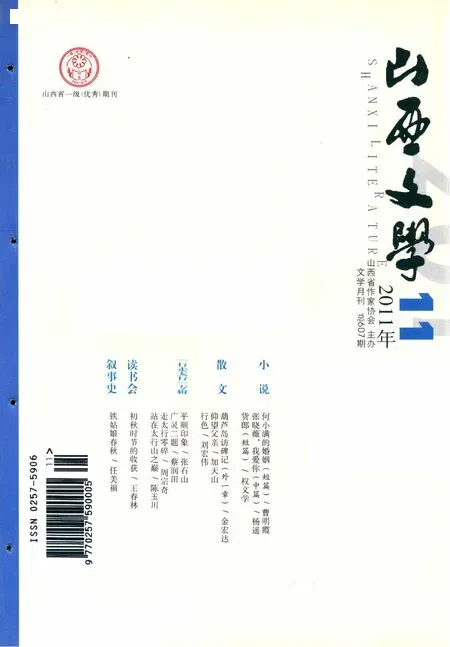初秋时节的收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巡礼
王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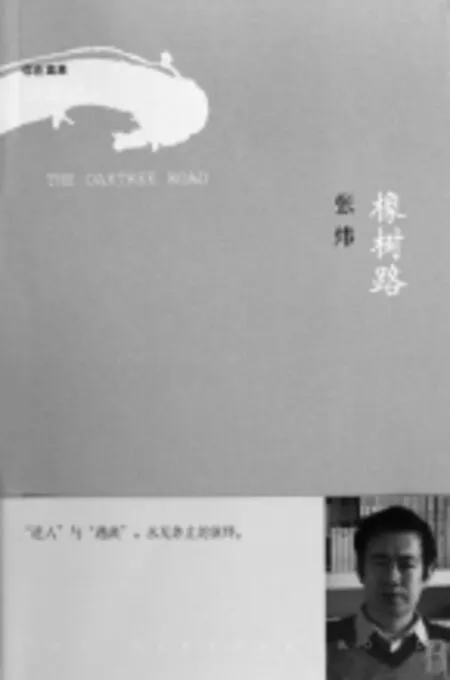
2011年盛夏,我有幸接受中国作家协会的聘请,参加在中国文学界备受瞩目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长达20天的集中阅读和评奖过程,固然比较辛苦,但能够参与如此重大的文学奖项的评选,见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诞生过程,却又的确非常幸运。亲历了这次评奖过程,参照前几届的评奖结果,参照这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形,我觉得,这一次的评奖,确实称得上是最公正、最透明、最具艺术含金量、评奖结果被普遍认为最不“离谱”的评选。在这里,结合我多年来对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追踪阅读体会,对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情况,进行一番巡礼式的描述和分析。
首先要进行分析的,当然是已经获奖的五部长篇小说。按照顺序,首当其冲的,便是名列榜首的那部长达450万字的巨型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这部小说的引人注目,与它那简直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巨量篇幅,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有没有必要耗费心血创作一部如此巨大的长篇小说呢?作家张炜必须通过这么多的字数,才能够完整全面地传达自己对于时代现实的理解和看法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这部字数浩瀚的长篇小说?面对着《你在高原》,以上这些疑问的生成,自然而然。然而,只有在实实在在地接触到文本本身之后,我们才真切地意识到,这是一部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绕过去的重要作品。关于《你在高原》,铁凝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一种评价:“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询、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充分认可铁凝评价的同时,我个人觉得,《你在高原》最起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是难以被忽略的。一是它的结构宏阔和规模巨大。不要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即使是将其置诸于人类文学的大视野之中,如此结构和规模的作品也相当罕见。很显然,作家张炜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艰难曲折的发展进程,进行一种艺术式的梳理与概括。能够拥有如此一种艺术雄心,并以《你在高原》对此进行充分的艺术实践,这种创作行为本身就应该赢得我们高度的敬意。二是小说所表现出的社会批判力度。张炜对于市场经济时代以来出现的诸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批判性反思。三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说实在话,当下时代多的是那些描写表现一地鸡毛般琐碎人生庸常现实的文学作品,如同《你在高原》这样一种具有浪漫气息、极力高扬理想主义精神的小说,就显得凤毛麟角般的难能可贵了。虽然说《你在高原》从艺术角度衡量并非一部无懈可击的作品,但因了以上几方面特点的具备,则这部长篇巨制之荣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上一届茅奖评选中,本来获奖呼声很高,结果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最终遗憾地落选。从这个角度来看,《天行者》的获奖,也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迟到的补偿。众所周知,刘醒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创作过一部名为《凤凰琴》的中篇小说,小说曾经在社会各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而《天行者》,则是在《凤凰琴》的文本基础上扩写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与小说中所描写的主体人群——民办教师,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当代教育史上还曾经存在过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体,但实际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真正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真正把现代文明传播到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世界的,却真的也只是如同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这样特别不起眼的普通民办教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天行者》界定为一部为中国的普通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虽然说是一部读来充溢着温暖感觉的长篇小说,但刘醒龙却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苦难。不仅没有回避苦难,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天行者》的感动人心,与作家对于苦难的充分展示,其实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惟其苦难,所以,这些民办教师那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为才会让人倍觉温暖。惟其温暖,所以,渗透潜藏于故事情节之中的作家刘醒龙的悲悯情怀,才能够极明显地提升小说的思想品质。综合以上的林林总总,我才愿意用“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刘醒龙的这一部《天行者》。
莫言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惟其久负盛名,所以,莫言在前几次茅奖评选中与茅奖的几度失之交臂,才能够成为文学界长期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蛙》的获奖,就既可以看做是对于《蛙》这一文本本身的肯定,也可以看做是对于莫言长期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突出思想艺术成就的一种整体褒扬。这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说,莫言的此次获奖,都是名至实归的。具体到这部《蛙》,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艺术价值,显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首先,这部以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长期存在的计划生育这一事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是莫言第一部以重大的中国社会问题为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这也就是说,莫言的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虽然说由于受到所谓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问题小说一度被人所诟病,但在我看来,对于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仅不应该被看做作家的问题,反而应该赢得我们的高度尊重。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要看作家是不是在一种艺术层面上创作社会问题小说的。莫言的《蛙》,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次,是对于某种深入骨髓的罪感心理与忏悔意识的真切表现。具体来说,《蛙》中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的主要体现者,主要是女主人公姑姑与身兼叙述者重任的“我”即蝌蚪。而“我”即蝌蚪此种特别心理的最终形成,又与小说中的收信人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罪感意识的强烈感召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这样,三位人物形象的罪感意识也就以彼此映照相互交织的形式,自然构成了《蛙》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主基调。第三,则是莫言在小说语言形式上的积极创新。莫言小说的语言一向以所谓汪洋恣肆泥沙俱下滔滔不绝而著称于世,但在《蛙》中,我们却可以感觉到作家在语言的运用上已经内敛节制了许多。不仅如此,莫言还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方面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努力。然而,与小说的语言相比较,更值得注意的,恐怕还应该是莫言对于小说形式的精心营构。从整体上看,通篇小说都是由“我”即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六封书信构成的。具体来说,前五封是“我”即蝌蚪为了完成一部以姑姑为主人公的话剧剧本,对杉谷义人讲述着与姑姑的计划生育事业有关的事情。或者,也可以看做是“我”即蝌蚪收集材料酝酿写作的整个过程。最后的一封信,则是完成之后的话剧剧本本身。这就是说,《蛙》所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可以看做是“我”即蝌蚪的一篇巨型内心独白。那么,莫言采用这样一种叙事形式的真正意图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于主要人物罪感意识的深入挖掘与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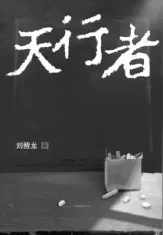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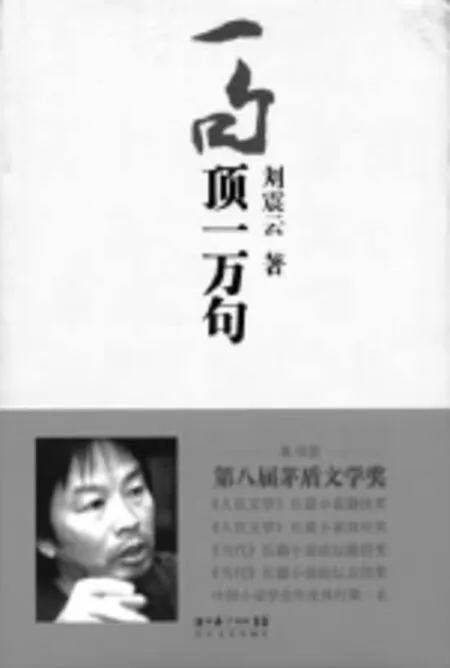
毕飞宇是这届茅奖评选中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虽然严格地说起来,毕飞宇的获奖小说《推拿》并没有能够抵达作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原》所已经企及的思想艺术高度,尤其是小说结构的相对狭窄,更是使得《推拿》缺少一部理想长篇所应具备的宏阔结构,但相比较而言,《推拿》却依然不失为评奖年度内特色鲜明的长篇佳作。从题材的意义上说,《推拿》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它是一部以盲人为具体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虽然说表现盲人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但相比较来说,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却是,毕飞宇是以一种平等的而非俯视的姿态来面对这个盲人群体的。通过对于盲人世界细致的描摹和悉心的体会,负责任地告诉广大的读者,其实盲人的世界和我们正常人的世界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和区别,可以看做是《推拿》最大的一个艺术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推拿》的写作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对于盲人世界而言的“祛魅化”过程。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一贯以其细腻的鞭辟入里而为读者所推崇。这一点,在《推拿》中同样体现的十分明显。无论是王大夫与小孔既带有几分羞涩而又孤注一掷的恋爱历程,还是小马被“嫂子”的气息所吸引,整日里的惆怅徘徊、辗转反侧;无论是都红在众人掌声中所感受到的“歧视”和“羞辱”,还是沙复明和张宗琪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激烈“心理交锋”;无论是金嫣为追求泰来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冲动,还是张一光在矿难中死里逃生后的微妙心理变化,都得到了具体而微的充分铺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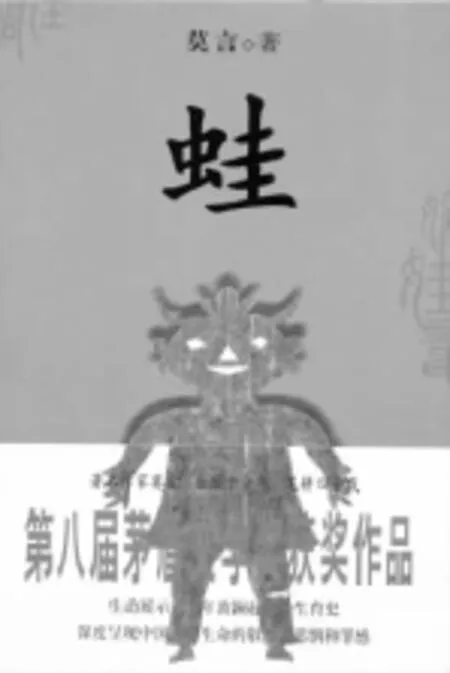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看做是表现现代人的一种精神漂泊与精神追求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始终是围绕着发生于乡村世界中的种种言语活动而展开的。对此,他自己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说明:“所以说人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一个话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话,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甚至比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要重要得多。”能否创作出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关键是要看作家有没有一种对于日常生活独到而深刻的领悟和发现。而刘震云对于生活的最大发现,则恐怕就是他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所特别强调的人与人之间言语活动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反复描写着的一个中心事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语沟通问题,或者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说得着和说不着的问题。客观的情况是,说不着的状况往往是绝大多数,要想真正地发现一点说得着的状况,实际上是难乎其难的。说到底,小说上下半部的两位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生阅人无数,但真正能够和他们说得着的,也不过只有巧玲与章楚红这样两个人而已。事实上,正因为说得着的情况极为罕见,所以刘震云才不由得发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由衷感叹。这里的“一句”,指的正是人与人之间颇为难得的一种心灵精神层面上的沟通与契合状态。然而,正是在这看似围绕日常的言语活动展开的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入思考。
以上五部获奖作品自然名副其实,可以说,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水准。然而,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一种评奖活动都无法做到绝对的公正,都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具体到这一次的茅奖评选,根据我自己阅读感受,我觉得,最起码包括宁肯的《天·藏》、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关仁山的《麦河》、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秦巴子的《身体课》等在内的几部小说,如果能够有幸进入获奖作品行列,恐怕也都是当之无愧的。限于篇幅限制的缘故,在这里只能对于以上提及的作品略作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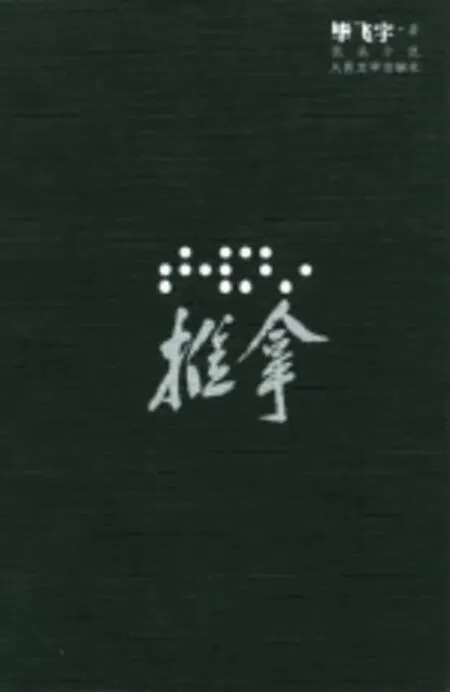
宁肯的《天·藏》,是我几年来所读到过的最优秀的一部具有现代主义艺术品格的长篇小说。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与情节层面上双重故事,如同坛城的布局一般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所构成的立体艺术图景,是《天·藏》文体上最根本的特征所在。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不断地相互交叉碰撞,不断地离离合合,二者实际上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携手前行,以此来推动小说的叙事不断向事物的纵深处发展演进。这样看来,注释部分的实际功能其实已经不再是注释,而是一种带有极大创造性的有效叙事手段。同样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在小说所采用的双重叙事结构之外,也还有对于感性和智性双重叙事话语的混杂运用。具体到小说文本中,所谓的感性叙事话语,就是指那些主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部分,而所谓的智性叙事话语,指的就是感性话语之外那些以哲学、文化等为主要谈论内容的理论性叙事部分。
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则是一部厚重异常的对于中国农民,对于所谓的国民性,进行着深入的批判性反思的长篇力作。贾平凹的《秦腔》固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一部表现乡村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但我觉得,与《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也毫不逊色。其中,既有对于复杂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巨构。
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既是一部把时代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融入到了个人命运中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充分体现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长篇小说。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在无形中受到过度重视现实功利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制约的缘故,中国的作家作品中很少能够表现出带有某种彼岸超越性的宗教情怀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普遍文化背景的存在,所以如同方方《水在时间之下》这样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带有一定宗教超越性的长篇小说,能够出现在中国文坛,才应该得到我们一种积极充分的肯定性评价。
大凡优秀的长篇小说,都必须具备一种“顶天立地”的艺术品质。所谓“顶天”,就是指作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描写层面上,必须得想方设法从具体的故事情节中跳身而出,具有某种超越性艺术品格,体现出某种形而上的思考特征来。所谓“立地”,就是指作家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必须用鲜活灵动的笔触,对于日常生活进行生动的描写与展示。关仁山的《麦河》,可以看做是一部“顶天立地”的长篇小说。其“顶天”,正可对应于作家关于白立国与苍鹰虎子的奇异描写,其“立地”,则可以对应于小说主体部分所讲述着的关于土地、关于鹦鹉村众乡亲的故事。正因为已经鲜明地具备了“顶天立地”艺术品格,所以,关仁山的这部《麦河》才不失为近年来一部难能可贵的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变迁的优秀长篇小说。
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是一部通过人性与革命之间尖锐矛盾冲突的捕捉和表现,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进行深入反思的长篇小说力作。具体来说,一种双重多视角后设叙事方式的熟练采用,是《父亲和她们》这部小说最根本的文体特征所在。所谓双重,第一重指的是最早出现的第一人称“我”也即子一辈的叙述者马长安,第二重则是指马文昌、林春如以及肖芝兰这三位父一辈的叙述者。所谓的后设叙事,一方面指的是马文昌、林春如以及肖芝兰这三位父一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当他们开始叙述活动的时候,都已经是在他们所叙述的一切全部结束之后了。相对于已经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马文昌他们的叙述当然就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后设叙事。然而,多少类似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句成语的是,虽然马文昌他们的叙述已经是一种后设叙事,但是,在这三位叙述者之后,却又出现了马长安这样一位子一辈的叙述者。相对于马文昌他们这一批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马长安的叙事当然就是一种后设叙事的后设叙事了。
《身体课》是著名诗人秦巴子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虽然只是诗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秦巴子能够一出手就写出如此一部令人格外刮目相看的具有明显现代主义艺术品格的长篇小说来,却还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强调《身体课》已经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就是因为作家的叙事重心已经彻底地远离了传统长篇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取而代之的,是叙述者对于笔端人物形象所进行的那些堪称精彩的心理精神分析。就我自己有限的阅读体验而言,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历史上,如同秦巴子的《身体课》这样彻底地放逐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完全把对人物的心理精神分析作为文本核心构成的长篇小说,绝对是第一部。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意义上,只有严谨的学术著作才会采用逻辑层次分明的理性分析式的写作方法,而小说创作尤其是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是应该采用具有强烈动作性的感性叙述手段,方才有可能吸引更多读者的阅读注意力。秦巴子所采用的这样一种以心理精神分析为核心的小说写作方式,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艺术实验精神。单就《身体课》所凸显出的这样一种鲜明的艺术原创意味,它就应该在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虽然不能说这次的评奖活动不尽如人意,但是,如果说在这次第八届茅奖的评选过程中,真的能够有如同《天·藏》、《身体课》这一类具有现代主义艺术品格的长篇小说获奖,那就明显地意味着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度。假若说,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评奖面前,各种创作方法一视同仁完全平等,那确实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件幸事。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一位长期的关注追踪研究者,我真切地希望能够有彻底打破传统评奖格局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到了那个时候,茅盾文学奖无疑将会拥有更加令人信服的权威性与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