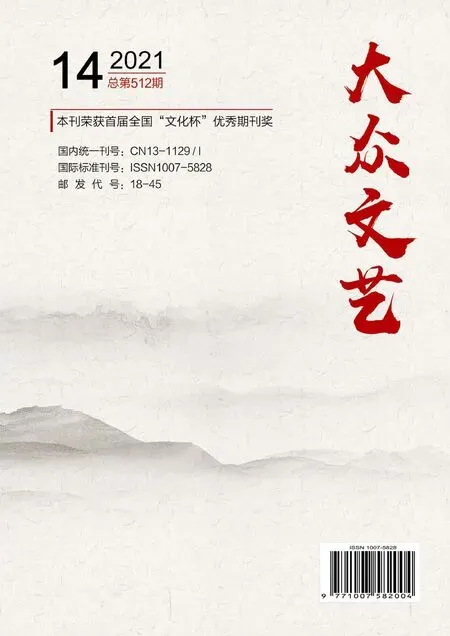世俗的叙事与审美——上海都市视野下女性形象的文化特质
朱晓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上海始终占据着无可取代的中心地位。从小渔村到“十里洋场”,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传统与现代在这里碰撞。1856年上海开埠,其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缩影,这座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起,经历了理性、科学、财富、权力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并随之不断变化。这些改变既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审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关于上海的书写,与这座城市一样,新潮与守旧、智慧与愚蠢、活力与焦虑并存,而这些矛盾的碰撞和冲突,更是有着他自身独有的魅力。
在关于上海的文本叙述中,女性能够成为载体与焦点,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女性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的,受控于父亲、兄弟、丈夫等男性家族成员。类似于“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观念将女性紧紧束缚在家庭中,从肉体到精神。女性实际上沦为父权文化的一种符号,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法制的烙印。而近代中国最早的女性解放,恰恰发生在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并且因为经济的发展更早地提出了社会变革需要的上海,这是必然的。女性在上海,逐渐摆脱了传统宗法制道德的束缚,从闺阁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所以说女性是“第一批都市‘现代性产物’”。[1]所以以女性为载体展开对上海的叙述就是必然的,是人对于自身解放和发展的一种需求,体现了中国人渴望变化的深层文化心理。
20世纪初,张资平以他肉欲张扬的享乐型小说风靡一时,尽管他笔下的女性几乎只是肉欲的化身,但他悄然地把女性带上了现代文学的中心舞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关系格局。
特丽莎•德劳•瑞提斯曾经说过:“城市是一种文本,它通过将女性表现为文本来讲述关于男性欲望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的笔下,女性作为中心意象出现。她们通常透过男性的眼睛投射出来,作为欲望的对象被观看。于是就有刘呐鸥笔下的女性:“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赋的嘴唇”。[2]还有穆时英描述中“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3]的女性。“欲望的快乐来自女性的窥视”,[4]对于女性外表和性征的窥视成为惯常的描写,都市女郎也就成为了作者都市欲望的具体对象,成为迷乱癫狂而又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上海的最好载体。
二
如果说30年代“新感觉派”的上海书写中呈现出的是对女性的“他者”叙述,那么,40年代民族危机下的上海,张爱玲、苏青等女性作家则完成了从“他者”叙述到“自我”叙述的转变。上海给予她们书写的机会,让她们从女性特有的角度和视野出发,由“外”而“内”,进入了女性生存的内在世界,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文本格局。
她们笔下的女性不再只是代表着都市欲望的“恶之花”,不再刻意追求刺激与享乐,而是回归日常与温情,真正地成为一种生活现实的象征。她们推倒新感觉派用浮华的意象与刺激的文字所构建起的上海文本,摆脱对于城市浮光掠影的叙述,真正走进上海的内部,走进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走进上海女性的内心世界,从而通过女性完成对上海更为内在的书写。
西方文明和都市文化的洗礼,传统文化和家族观念的熏陶,使得上海女性拥有复杂并且看似矛盾的多重性格。她们世俗而又时髦、敏感而又颓废、妥协而又柔韧。40年代的战火遮掩不住上海最市井最日常的生活,张爱玲和苏青避开了政治,而是在无数鸡毛蒜皮的家常琐事中,表现着最世俗的上海生活和上海女人,利益至上的物质观维持着表象的乐观与暂时的安定。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金钱和情欲的双重枷锁扭曲了人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毁灭于金钱和欲望,一个个生动的女性形象,真实地还原了三四十年代最日常的上海。上海“小女人”虚伪之中又有着真实,浮华背后又流露出朴素,这才是上海这座城市最感性、最真实的一面。
三
四十年之后,在走过历史巨变、经历涅槃重生的上海,王安忆默默地开始续写被中断了的上海精神。同张爱玲一样,她试图在上海表面化的符号背后,挖掘出深处的城市精神,所不同的是王安忆摆脱了“他者”抑或“自我”身份的束缚,而是把上海女性的命运和这座城市更为宏大的历史联系起来,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人的现实,都在不动声色的表面之下,和城市的命运紧紧相连。她跨越了身份所带来的写作局限,将叙述的视角放大,将叙述的空间从张爱玲的家庭扩大到整个都市的角落,叙述的时间也从不再是静止而是流动着的,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书写变化中的上海和女性的新传奇。
每个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读着城市,作家诠释着变化中的城市,而城市的变迁又同样打磨和塑造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上海是基本的背景,而女性更是“第一性别”,她把女性放到更为广阔的背景和空间中,不再局限于家庭的束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对都市女性的命运进行阐释。心理学上认为,童年对于人的影响是终生的,对于王安忆来说,作为城市“外来户”的南下干部家庭,这样的一种身份是微妙的,在她的成长经验里,似乎与上海始终是“若即若离”的,而正是这样一种“若即若离”,使得她更为热情地描写上海,重塑上海。她的“城市是一座女性视野的城市,是一座女性体验的城市”。[5]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妹头》中的妹头……王安忆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摆脱不了上海和女性。王安忆自己就曾经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他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几乎不是“上流阶级”,也很少触及到“贫民”,她通常选取的是她所熟悉的弄堂里普通的上海女人,她们的生活方式,才是这个城市最稳定最常见的一面。女性的城市是相对稳定而绵长的,岁月蹉跎,但女性的城市却总是有迹可循,王琦瑶们本身就是一部上海生活的风俗史,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才是上海这座城市,最真实的面目。女性的命运就是上海的命运,上海的变化也是女性的变化,王安忆将自己作品中的上海处理成一个风情万种的女性,而作品中的那些上海女性则包含着对上海的隐喻,在琐碎的日常描写中,探讨女性的命运,同时也自觉地完成了对上海命运的诠释。
[1]史书美.性别、种族和半殖民主义.刘呐鸥的上海都会景观[J].《亚洲研究》.1996(11).947.
[2]刘呐鸥.都市风景线[M].上海.水沫书店.1930.57.
[3]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M].上海.复兴书局.1934.3.
[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0.
[5]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