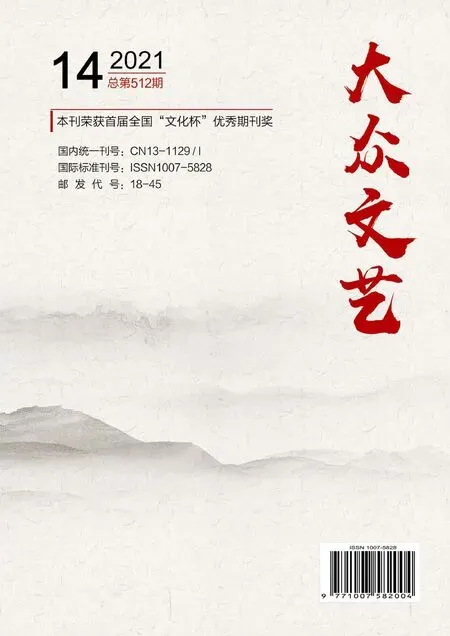明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探析——以麻风病为中心
张金婷 徐凯敏 (温州大学 浙江温州 323000)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疾病描写随处可见,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的是疾病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它本身早已超越简单的病理学问题而更多的被带进社会政治、宗教、文化、思想认知状况内加以渲染。此时的疾病被不自觉的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变成了文人眼中种种惩罚性与感伤性的意象,即疾病不断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了。
何为隐喻?“首先他是一种语言行为。表面看来,隐喻只是一种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润饰辞藻的一种修辞手段,是以言示意的表达方式”[1]。然而从更深层而言隐喻更是人们认识、理解、思考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所以说,隐喻是一种语言行为的同时又是一种心理行为。其实质即“隐喻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现象,却暗示出更深意的心理现象”[2]。而在这种暗示的情况下,两类事物之间或明或暗的便衍生出了新的意义,在两类事物彼此的联系之间生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中,隐喻不自觉的生成了。疾病作为人类生命的阴面,身体的不健康便在人们的暗示下衍生出了新的文化内涵。于是疾病的隐喻成为了上天对患病人道德伦理败坏有意的惩罚性结果。特别是麻疯病作为中国古老的恶疾之一同样经历着人们不自觉的隐喻化处理。所以本文主要是梳理考察古代文学典籍及小说当中文人笔下对麻疯病的认识与理解,重点考察麻风病在明清小说作品中的演变状况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隐喻价值。
一
但据笔者统计,疾病意象在各朝代不同的小说作品中都有其出现的痕迹。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笔记小说的黄金时期,据笔者考察资料来看许多轶事小说,志怪体小说中对疾病的描写与表现更加复杂化,即疾病除了作为小说叙事语境的血药外,疾病更多与宗教、伦理道德,社会文化等缠结在了一起。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志怪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等笔记小说中都不乏对疾病的描写与渲染。志怪小说《宣验记》中描写了沛国周氏三子喑不能言,在一道人的指引下周氏道出为何其父子三人喑不能言的原因即上天对其幼年时期杀死燕子行为的因果报应。此故事将周氏父子的喑疾与宗教道德联系在了一起。此外,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骂鸭>一篇同样将疾病与人的道德伦理掺杂在了一起: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末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深畏骂焉,骂之亦可儆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骂,其病良已。
异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3]
故事中偷鸭人要向邻翁讨骂其罪责才可稍减,而邻翁骂人却是善事一件、功德无量。居民某茸生鸭毛这种怪病成为了道德败坏的隐喻象征。作为古代小说顶峰之作的《红楼梦》对疾病的描写更是不胜枚举,林黛玉的“不足之症”、薛宝钗自打娘胎便带出的热毒、特别是对秦可卿妇科疾病的描写都似乎与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那么的紧密相连。当然对于古代小说作品中疾病意象的隐喻化现象许多学者也早已给予了不断的关注与研究。如王一杰的《<红楼梦>中女性疾病的概念隐喻分析》、段振离的《医说红楼》、詹丹的《古代小说中的医案描写---以<红楼梦>为考察中心》以及硕博论文许敏玲的《麻疯病与明清社会》等都从不同学科与角度对古代小说中疾病隐喻作过独具一格的研究与考察。
疾病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下,都是我们不愿谈及的一个话题。在我们看来疾病本身就代表了世界上丑陋的事物,疾病的终极便是恐惧、是死亡。 而麻疯病此种病理复杂、难以治疗、病患外表易变形的疾病自古至今同样承载了丰富的隐喻内涵。“西方学者Susan Sontag曾提及任何疾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疗无效,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4]麻疯病在明清时期不仅是可怕的疾病,更成为“‘戚里恶闻,骨肉远避’令人极度恐慌、排斥的疾病。”所以说对麻疯病的研究是考察明清时代社会文化本质特征及进一步探讨疾病在一代社会中所存在的隐喻文化价值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据笔者掌握材料而言文学作品对麻疯病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小说作品当中。并且这些小说对麻疯病的描写侧重点已经超越了麻疯病本身,更多的掺杂了社会、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
二
中国医学、史学家几乎都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厲’‘大风’‘恶风’‘癞’‘大风癞’‘疯癞’以及‘(大)麻疯’等应可能即是今天所谓的麻疯病”。[5]对于麻疯病发病时的外在表现南宋也有明确记载:大风恶疾,疮痍荼毒,浓汁淋漓,眉须堕落,手足指脱,顽痹痛痒,颜色枯悴,鼻塌眼烂,齿豁唇揭,病症之恶无越于斯。负此病者,百无一生。[6]此外,道光十二年袁世熙在《疯门全书》序文中指出麻疯病的可怕:疾病之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者,曰瘟疫,曰癘疯。……癘疯几千百年明哲代出,无不为之束手,圣如丹溪,治效四人,后三人犹复发而毙。[7]也正因为麻疯病这种发病时外表及其难看、令人厌恶的疾病常常让人恐慌;医学上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原因‘过癞’仪式在民间非常盛行,且小说中同样也对这种仪式的描写。所谓‘过癞’指异性之间通过性行为可将自己身上的病毒传给他人可使病情减轻甚至是完全治愈的一种民间疗法,并且这种疗法多是女性传染于男性。
对于麻疯病的描写最精彩、最凄艳的当属清朝宣鼎《夜雨秋灯录》中<麻疯女邱丽玉>的故事。在宣鼎的笔下,麻疯女邱丽玉凄艳的爱情故事使人印象深刻,以及麻疯病在当时社会的不容于世的悲惨情状以及过癞仪式这种人们基于对麻疯病恐惧而想象出的民间疗法在小说中都带上了隐喻色彩。故事讲述的男主人公陈绮因父亲再娶,后母冷酷,在生母的遗愿嘱托下入粤地寻舅父依靠,得知舅父已客死异乡,在一名和善老叟的“好心”建议下,至邱员外家投靠为婿。但洞房之夜,身患癞毒的丽玉面对陈绮却“粉黛间隐有惨悴色”,细问其故,丽玉乃以真情实告:‘妾麻疯女也。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却以千金诱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体遍瘙痒’[8]。陈闻之恍然大悟,后来丽玉便帮助陈绮逃走了,陈绮离开后不久丽玉忽毒发,家人便将其送到了麻风局。无家可归的丽玉不得不离开家乡,行乞卖唱,千里寻夫。丽玉在仙道的指引下找到了陈绮,陈绮便安排丽玉住在了酒窖。他每日亲自侍奉汤药,甚至睡在丽玉身旁。一日陈绮外出,丽玉见大蛇盘旋屋梁,堕入酒中而死,丽玉为了不拖累陈绮决意寻死,遂掬饮数次,谁知肤痒顿止“肤之燥者,转莹如玉;发之卷者,转垂若云;面目手足之皲裂者,转如花如月,如嫩笋芽矣”[9]。丽玉康复后陈家即备礼合卺,后生贵子,从此蛇王乌风酒亦广为流传。此故事可以说是描写麻疯病最婉转、离奇且比较完整的事例。在宣鼎的笔下,一对生活坎坷不平的男女在众人嫌恶的麻疯病的捉弄下,善良、纯真的情感,不离不弃,最终走向幸福的结局让多少人唏嘘不已。然而,据笔者考察资料来看,小说作品对于麻疯女故事的记叙并不始于宣鼎。作于乾隆年间的《秋灯丛话》卷十一《粤东癞女》是对癞女最早记载,同样有过癞这一土疗法,而且女主人公的癞也没有过,癞女将少年放归,其因毒发被家人赶出家门。就在癞女流浪行乞之时却得到了卖胡麻油少年的帮助,偶然的机会女主人公喝了浸有乌梢蛇的麻油后,麻疯病竟奇迹般的痊愈,后来才知此少年便是女主人公昔日赠金放走之人,于是“为之执伐,成夫妇焉”。此外,在《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麻风女》也有麻疯女不愿听家人安排,放走“顺德某生”,不久便“为生投江死矣”的故事;笔记小说《小豆棚》中<二妙>讲述的是粤女二妙素与吴贾褚文兴来往,但二秒不幸感染大麻疯,“其父使妙移于褚。……妙至褚所。褚喜,求合,女愀然曰:‘我不忍祸君也’。遂告以故,且令褚速去”[10],褚离去后,二妙病益重,“众共弃之”。于是,妙乃流丐至吴阊,褚便收留了妙。因院中槐树空腔中的蛇常食二妙的食物,妙亦吃蛇食过的食物,一日妙竟“忽收脓结痂,脱然以起”。褚与妙也喜结连理。采衡子的《虫鸣漫录》中善良的富家女同样不愿伤害他人得以食蛇涎而治愈。在这几篇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患麻疯病的都是女性,并且过癞这一疗救方法都因女人公无害人利己之心而没有完成,并且在文人的笔下,这些具有贤良美德的女子几乎都得到了美好的结局。然而,在宣鼎《夜雨秋灯录》中的小说《东野砧娘》同样描写麻疯病人的故事,但作者却从另一视角将患麻疯病的人改为了男性。故事中女与闵祝从小便有婚约,只因闵祝患麻疯病女方家人欲要解除婚约,但女为证明其贞德日日侍奉于闵祝左右,闵祝偶因误服砒霜麻疯病得以痊愈;冯梦龙《醒世恒言》中《陈多寿生死夫妻》描写男主人公陈多寿与少女朱多福从小有婚约,但因其患了麻疯病女方家人要解除婚约但朱多福誓他不嫁每日侍奉左右。两人成婚后几经波折两人终成正果。综上几篇短篇小说患麻疯病的人物成为了男性,并且女性面对对方的恶疾誓死不改初衷侍奉与男性患者左右,最终男女双方都有了一个美好结局。
三
为何同一题材会不断出现在各种文本当中,首先我们不排除男女主人公的深情厚谊感动了许多痴情怨女,故事题材的轶闻性满足了大部分人的好奇心理以及麻疯病在明清时期的不同凡响,而更多的就是麻疯病在小说中隐喻化的艺术特征。沈之问《解围元薮》曾指出夫妻间会透过交媾传染风毒且遗传子女,也就是说患麻疯病的女子是婚姻中的大忌。《大戴礼记》亦早记载:‘女有五不取’其中之一便是‘世有恶疾不取’因为患有恶疾者乃是为天所弃,为鬼神不福佑之人,是不洁净之人,他们禁止参于祖宗祭祀场合的。麻疯女成为了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边缘人,她们会很不幸的被婚姻这个城堡所隔离。“女性的空间是低的,疾病的女性生存空间更显得狭小”[11]。邱丽玉这等麻疯女在疾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得到的不是家人的照顾,旁人的人情关怀,而是落了个被送进麻风局或被遗弃的下场。在无奈的情况下,她们有的选择速速求死,放弃那被人厌弃的不成样子的躯体;其次,‘过癞’仪式在小说中同样被赋予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女性欲要治愈自身的疾病,就必须有男性与之发生性行为,当然这种治愈方法是不可告人的。“万恶淫为首”,麻疯病女性要用一个女性最重要的贞德才可换得自己的重生,这种过癞仪式本身就已经将女性带入了隐喻的泥淖;同样男性因为接触了患病的女性感染了麻疯病,难道这不是认为女性身体乃为恶的本源的隐喻性思维方式吗?另外,麻疯病人皮肤的溃烂,容貌的变形这种令人厌恶的外在显现在小说中成为了一种对女性道德败坏的惩罚,疾病成为了道德沦丧的隐喻符号。人们看待麻疯病人已经在一种不自觉的心理暗示下,将麻疯病发病时丑陋的样子与上天的惩罚与人性的堕落联系在了一起,隐喻便产生了。
总之,疾病作为医学领域研究的内容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是作为象征的意象而存在的,疾病意象更多的被古代文人赋予了复杂的社会文化隐喻意义。作为一个隐喻,麻疯病病理的复杂与病因的不易掌握经常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伦理道德感到不正确的事物。而对于女性疾病患者,麻疯病更是成为了她们不堪重负的肉体与精神的隐喻,从中我们也能看到女性在古代宗法社会文化下自身生存的悲剧隐喻化色彩。
[1][2]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黄清泉.明清笔记小说新选[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45页.
[4]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许敏玲.麻疯病与明清社会[D].台湾: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6](南宋).陈言.三因极---病症方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卷15,27页.
[7](清).萧晓亭.疯门全书[M].北京:中医药出版社,1999.第二册.776页
[8][9](清).宣鼎.夜雨秋灯录[M].黄山书社,1999.
[10](清).曾衍东.小豆棚[M].济南:齐鲁书社,2004:133页.
[11]顾广梅.多维的验证[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