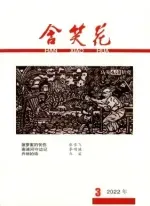宁静有多远(外一篇)
◆蒋德海
宁静有多远(外一篇)
◆蒋德海
从大厅里出来,不需一分钟,便到了这幽静的一角。这是个话吧。观其光鲜程度,应该是刚刚建成的,新鲜的墙体,崭新的架构,一缕缕木香不时扑面而来。空间不大,仅够五、六个人容身,多几个人便显拥挤。石棉瓦屋顶,空心砖墙体,一面墙上挂有报纸,是《中国剪报》、《中国旅游报》、《云南政协报》等,尽管三个报夹,报纸却混杂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看来,前来看报的人应该不少。另一面墙上,挂一个盛放碗筷的篾箩,一把干净的稻草躺在里面,算是铺垫,但有风吹草动,篾箩便不由自主地颤起来,稻草也一颤一颤的,瞬间,弥漫着谷子的气息。箩是空的,不见一碗一箸,此情此形不由使我联想到,一家人均已外出,未归,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青灰的水泥地皮中央,一张八仙桌,辅以六只小方凳,就像六个孩子围着大人听故事。墙根一只大靠椅也是闲着。左山墙和右边白漆栏杆之间,是一道没有门板的门,显然,此门是敞开的,并不拒绝每一个想走近它的人。
我取了报夹,搬了凳子,坐下。阳光静静地舔在脚上,就像泡在温水里,暖暖的,舒服极了。渐渐地,温水下面就像有团火,水温渐次升高,升高,我仿佛看到了袅袅升腾的水汽。此刻,我身上似乎也有那种水汽,潮潮的,润润的,有点粘性。果然,额头冒汗了,密密麻麻,汇成一股清瘦的小溪,不时从鼻梁上跌下来。思维开始像一匹骏马,驰骋在想象的原野。然而,如此的高温,我终究不能经受多久。我终于把脚缩了回来。
挺想静静地翻翻报纸,看看里面有什么好新闻,有什么值得玩味的东西,但是,未能如愿。我看见了小蚂蚁,黑色的,不多,只有七、八只,一个劲地行走,看样子,既不像参加什么盛会,也不像组织什么特别行动。它们也许在野外呆腻了,便相约着,进屋子溜达溜达,顺便避避暑,感受屋里的美好。就像我们老是困在乡下,坐井观天,时日长了,便向往城市的繁华,就想出去走走,开开眼界;就像我刚才在大厅里呆倦了,听觉麻木,视觉错乱,就想出来透透气,梳理一下紊乱的思绪。
正前方是一片树林。阳光像利箭一样齐刷刷地射下来,草们都耷拉着脑袋。微风。枝头的绿叶悠闲地摇来晃去,洋丝瓜随意地搭在水冬瓜树上。透过斑斑驳驳的光影,我还发现,那些枯叶,以及那些已经成为干巴的虫子,悬悬地挂在蛛网上,就像儿时荡秋千。突然,“嘎吱、嘎吱、嘎吱……”叫声由远而近,朝我的方向逼来,这陌生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怪物发出的?我立马起身,举起凳子,以武松打虎的架势,准备迎战。记得爹说过,在野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有风吹草动,都要警觉。可是眼下,它却哑然无声了,怪物会不会悄悄地潜过来?我的身子湿透了!“嘎吱、嘎吱、嘎吱……”叫声更为响亮,一阵紧似一阵。我作了最坏的打算。
终于,那些家伙露面了。一群珍珠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它们一股脑儿地奔过来,原来,是集体捕杀一只蝗虫,为了争取胜利果实,在我尚未回过神的瞬间,都争先恐后,闪电般地消失了。不一会儿,我又听到那声音,那叫声舒缓多了,不像先前的咄咄逼人,叫人不寒而栗。“嘎吱——嘎吱——嘎吱——”像树干与树干的摩擦,像大风撕扯着干树皮,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此刻,我心里却踏实多了。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看清它们的真面目了!肥嘟嘟的身子,珍珠般瑰丽的羽毛,淡红色的耳朵,戴耳环,一边优雅地走着,一边啄食路边的草叶,很有绅士的味道。这家伙大胆得很,见我在那儿呆着,一点儿都不怕人,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溜过,那光滑的羽毛还触碰了我的脚杆,弄得我酥痒痒的。常言道:万物有灵。我深以为然!我想,人和大自然本来就不应有隔阂,只要和它们多接触,多沟通,说不定,彼此间还能建立起某种信任,能完善人的某些情感,弥补人的某些先天不足呢。譬如爱心,譬如自尊心,譬如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出于真心?能否放得下架子?
宁静是什么?宁静在哪里?宁静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近前,但见青麻抒情地撑起绿伞,红辣椒自信地结果,老南瓜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向日葵满足地吸纳着阳光;不远处,“黑头翁”的鸣叫像唱歌一样地婉转;天边,云彩像牛奶一样地白,蓝天像秋水一样地明净。其实,美妙的景致,并非都在远方,亦在近旁,在身边,只需一个转身,便触手可及。不信,你试试。
敬畏蚂蚁
为那些卑微的生命立言,我最为敬佩的要数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他怀着对生命的敬重和敬畏之情,50余年深入到昆虫世界中,用毕生精力对昆虫的种类、习性、觅食、乃至婚俗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实验,并翔实细致地记录了各类昆虫的本能特性,用第一手资料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形象地展示给世人。法布尔将人性统照虫性,又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正如法国著名戏剧家罗斯丹所言,“这个大科学家像哲学家一般的思考,像美术家一般的观察,像文学家一般的写作。”因此,法布尔被法国的文学界、科学界授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的称号,并被举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之所以引出以上的段落,是因为法布尔关于昆虫的文字首先引发了我对那些微小生命的兴趣。
愧疚地说,对于昆虫,我充其量算个虫盲。不要说那些完全陌生的面孔,就连平日司空见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小蚂蚁,对于它们的品类、习性,亦是一知半解。通常的情况是,见到蚂蚁,要么不理不睬,视而不见;要么即刻将它们踏扁,掐碎,以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以为,这么卑微的家伙,于人而言,微不足道,简直轻若游丝、轻若尘埃。这么渺小的东西,是否和它友好,是否了结它的生命,全凭自己一时的意念,根本用不着伤精费神。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小蚂蚁,见证了它们的所作所为,不由不使我对它们充满了敬畏!
那是一个傍晚。准备晚餐的时候,我打了两只鸡蛋,在我用筷子调匀蛋黄蛋清的当儿,一不小心,蛋清及部分蛋黄便一跃而出,溅到了窗台上,亮汪汪地,成了个淡黄色的“椭圆”。当下,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惟有一门心思火速烹调心爱的“番茄炒鸡蛋”,而没有立马清理现场,收拾残局,于是就让它们汪在那儿,在窗台上过了一夜。
翌日,中午,吃罢早饭。我在窗前看风景。一眨眼,便瞧见了两只小黄蚂蚁,只见它俩抖动着触须,一前一后,津津有味地在“椭圆”上美餐。按以往的做法,我当然会立刻走过去将它俩掐死,或者把它们撵走。可是此刻,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出乎意料地没那样做。我想,都是泼出去的东西了,反正自己也吃不成,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浪费,只要它们情愿,就让它们尽情地享用吧!
下午,我又在那儿看风景。天哪!哪儿来那么多的小蚂蚁?“椭圆”的上面,密密麻麻的小黄点儿,来回蠕动,好不热闹!粗略数了一下,约有40多只。再巡视右边的路线,只见蚂蚁“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奔忙,仿佛赶赴一场盛大的宴会。你看,它们不慌不忙,不紧不慢,踏着齐整的步伐,就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它们不拥不挤,不打不闹,秩序井然,既像举行一次大练兵,又像组织一次大生产运动。你看,它们来的时候,轻松自如,激情满怀!回家的时候,几乎都满载而归,几乎都衔了一小块金灿灿的蛋黄。我想,那一定是它们饱餐之后,额外分到的、带给妻儿老少的礼物。我一时惊叹不已!
是谁通风报了信,是谁走漏了消息?难道它们也有先知先觉,心有灵犀?
其实,我曾拜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我也曾浏览过相关的电视节目。我知道:蚂蚁体内具有一种独特气味的分泌物(示踪激素)。这种激素由肛门排泄而出,当出巡侦察的蚂蚁发现食物后,就在回来的路上撒下示踪激素,使其它蚂蚁嗅着这种分泌物的气味,前进。这样,即使路线暂时被中断了,蚂蚁们也一样可以很快找回原来的线路,而不会迷路。
然而,此景此情,我以为如果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阐释,那是多么的肤浅,苍白!
我不由想起乡下老家的那些牲口。喂养它们的时候,把恁多的食料倒在面前,满盆满钵的几欲溢出。按理说,那些食物足够它们吃饱喝足,甚至撑破肚皮的,但为什么都把眼珠子睁得卵大,嚼着嘴里的,霸着面前的,瞪着人家的,谁的动作稍不规范,动辄踢踢咬咬,大打出手。为了填饱自己的肚腹,它们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下口时便下口,完全不惜伙伴受苦,完全不怕伙伴受伤、残废。多残忍!
我不由想到了我们的万物之灵!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乍一听,似乎有失偏颇,可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啊!且看:我们某些所谓的“公仆”,平常的时候,大公无私,道貌岸然,一副慈善家的嘴脸,一副菩萨心肠,一眼看去,活脱脱的正人君子。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再说直白点,就是到了最有利可图的时候,他还想得起你,管得了你,还认你是弟兄、朋友?只要见到那么一丁点“蛋黄”,便蠢蠢欲动,把曾经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还由得你来“有福共享”?更有甚者,本属于弟兄朋友们共同的“蛋黄”,竟也敢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廉耻地独享、独吞。多恐怖!
通常所说,“蚍蜉撼大树”,泛指力量很小而妄想动摇强大的事物,比喻不自量力;亦说,“贱如蝼蚁”,用以比喻力量薄弱或地位卑微之意。反过来,倘若蚂蚁有知、有灵的话,站在人类的角度思考,它们又将如何定位人的某些陋习呢?“人模狗样”、“人面兽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并非没有可能!果真如此,我们还能在它们面前雄赳赳、气昂昂,摆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吗?!
小小蚂蚁尚能“有福共享”,为何我们人类却难于登天呢?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人应当自愧弗如,虚心向蚂蚁学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