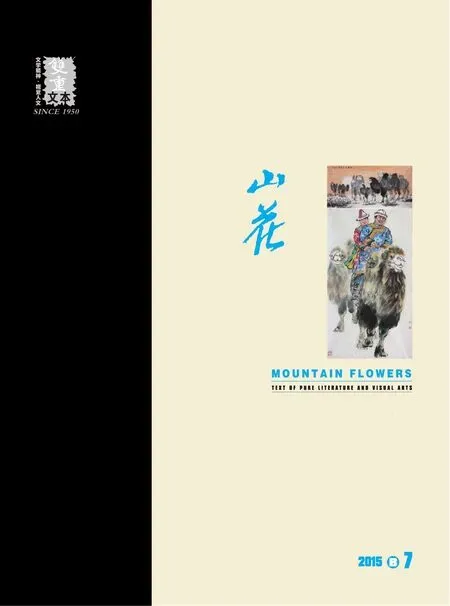井上靖文学创作中的“斗士”性格与“中国文化”情愫
刘振生
日本作家井上靖在文学创作上锐意进取,不断探求。他发表了很多诗歌、随笔和评论,也创作过剧本和电影脚本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小说。1976年新潮社出版了他的小说全集共三十二卷,主要有《猎枪》、《冰壁》、《斗牛》、《天平之瓮》、《楼兰》、《敦煌》、《苍狼》、《风涛》、《城堡》、《夜声》、《杨贵妃》、《孔子》。他的作品主题深刻,题材广泛,社会性强,富有艺术感染力。他以当代社会为题材的许多小说,如《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暗潮》等,多方面地再现了战后日本错综复杂的生活图景,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人民的不幸与不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情感大多数是蕴藏在字里行间以及每一个人物之中的。陈嘉冠评价道:“井上靖描写日本现代生活的若干小说,虽对现实社会很少大声的诅咒,坦白的暴露,却掀起寻求真善美的浪潮,蕴涵着作家的真情,显现了纯真、清幽、婉约、旷达等多层次的艺术灵境。”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的人生经历,以及走上创作道路过程中对现实的关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其富有“斗士”性格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与日本传统的审美情趣“物哀”及中国大陆文化精粹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一、作为“斗士”文学性格的《斗牛》、《苍狼》
中篇小说《斗牛》于1950年由文艺春秋社出版。该作品在日本发表后不久,就获得了当年的芥川文学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被看做是开创了介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之先河。作品描写新大阪晚报社编辑主任津上,在组织一次比赛的过程中,与投机商人钩心斗角,以及他在爱情生活中的波澜与选择,深刻地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生活原貌。斗牛和爱情两条故事情节交互发展,纷乱活跃,但又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爱情为斗牛起了渲染和烘托的作用,斗牛又将爱情置于了一个火热难当的境地。津上的同学在侵略战争中死去,他的妻子笑子委身于津上,同他姘居了三年之久,但两个人一直处于感情与事业难以两立的纠葛之中。笑子置身于渴求个人幸福的意愿与迷茫之中,津上则把全部精力倾注于事业开拓之上,而对她若即若离,两个人都为这种哀怨缠绵的爱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品中着墨最多的是对津上这一人物性格的刻画。津上刚毅果断、老练稳健,为了在险峻的战后社会中开拓一番事业,对笑子的温情表现的非常冷漠。与此同时,作品中还揭露了许多肮脏的黑幕交易,勾勒出田代、冈部以及三等投机商等人的丑陋面孔。
《斗牛》采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交织的表现手法,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就像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同样的爱好一样,“赌”是万万不能没有的。这种以津上为代表的人物性格特征,更多地透视出战后日本人对侵略战争所带来的废墟、伤痛、死亡等的无奈和悲观情绪。事实上,津上的情人笑子也是在进行赌博,不过她的筹码不是其他财物,而是她本人。小说在写法上紧紧围绕斗牛一事展开,从最初的一般设想,到一步步地把所有的人物都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并利用下雨来对事件进行一个了结,入情入理。另外,作品在描写津上与笑子两人的情感关系上,始终弥漫着一种抑郁感伤的气氛,字里行间浸透着无奈,表现出作者对这种“不伦之恋”的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批判。
长篇小说《苍狼》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7月间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作品中的主人公成吉思汗是一个令世人注目的英雄。作者之所以选择了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有他的创作意图。成吉思汗是在斡难河的族部祖先接受天窗照进来的一道光而受孕生子成为苍狼之后。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苍狼后代,但他更知道“即使不是苍狼的后代,也要成为真正的苍狼”。他为这个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189年28岁的他登上了部落汗位,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他看到了广阔的草原有用不完的疆域,湖畔河边也多得令人数不清。从那时起他便逐渐产生了统一部落和征服整个草原的欲望。征服是欲望者实现其欲望的残酷实践过程,它最终需要通过战争来完成。战争带来破坏,而统一之前就是破坏,但破坏之后也是建立新天地的开始。1206年他终于终止了各个部落、族群无休止的纷争、杀戮,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家,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的广大区域。他不愧是一个领袖,除了对内加强统治,还对外不断扩张、征战,并建立了一套严密而完备的政治及军事体制。他坚持“有了信仰才能有统治的力量”的观点,接受新文化,留用俘虏的工匠。另外,他对文明生活的向往、对社会进步的渴望还表现在重视教育和接受异族文化上。为了征战他把亲生儿子放在平民家中生活,希望他将来即使作为一个庶民的儿子,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同时他深信这个通过苦难锻炼的儿子也一定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苍狼勇士,与未来的各种困难进行不懈的斗争。井上靖在描写英雄的时候一方面不忘其历史背景、英雄特质,另一方面还给予他多重的情感,表现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蒙古族男子汉形象。
《苍狼》注重在语言上的表现,但某些描写透露出了日本人的审美习惯,如美女吸引人的“光亮的头发和雪白的脖颈”,就受到日本自古以来对女性美的认知个性的影响。小说中较大篇幅是用于铁木真的内心独白和对事件的叙述。整个作品风格平实如写史,这也是井上靖一贯的创作手法。另外,尽管人物之间的对话不多,但这些对话中充满古朴的暗喻、象征、借代等,流露出原始氏族艺术的独特风味和魅力,同中国的氏族史诗如《格萨尔王》、《江格尔》、《嘎达梅林》、《伊玛堪》等相似,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民族史诗乃至中华文化的眷恋。
二、作为“物哀”与“中国文化”合璧的《天平之瓮》、《楼兰》
“物哀”是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中就存在的传统审美情趣,它在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中有很多取材于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北方、西域的作品。在其三十二卷本的文学创作中,历史小说达十一卷,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这些历史小说时间比较久远,空间比较广阔,上溯隋唐,下至明清。从艺术成就以及作品的比重来看,中国历史小说,尤其是以西域为背景的小说居多,并成为其历史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天平之瓮》、《楼兰》则是以中国为题材并支撑其历史文学的代表作品,并带给岛国日本一股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之风。
长篇小说《天平之瓮》1957年2月至6月在《中央公论》上连载,同年12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单行本。小说从公元732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出发赴唐时写起。荣睿、普照、玄朗和戎融等人作为入唐学习的学问僧同行。入唐后,他们为唐朝的繁荣所惊叹,也使这些日本人从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凄凉。面对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为了解前辈留唐经验,他们拜访了即将学成归国的玄昉和吉备真备,但因玄昉的态度傲慢而毫无收获。倒是学无所成,老耄落魄的景云还能同他们共话衷肠。经景云介绍,他们又找到了在唐二十年的业行。业行拙于口舌,性格孤僻,自知难以学成,就终日躲在一个不见阳光的房间里抄写经书,以便带回故土。荣睿、普照考虑到自己在唐学习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就决定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识渊博的传戒师去日本,弘扬佛法,设坛传戒。玄朗不堪生活的寂寞,娶了唐女安家,戎融则放弃学习,托钵云游。五年后,荣睿得知自己推荐到日本的传戒师因僧员不足,不能传戒时,他决心再请高僧及早归国。得到宰相李林甫的支持,荣睿、普照到扬州拜请高僧鉴真,得到鉴真肯定回答,便做东渡准备。几次东渡都失败了。第五次渡海时,竟被大风浪刮倒海南岛。他们只得回到桂林南下广州,等待出海。途中,荣睿不幸染病身亡。因渡海无望,鉴真只得返回扬州等待,这时,他年已六十,双目失明,但赴日之愿未有丝毫动摇。公元750年,日本派遣第十一次遣唐使到了中国,普照说服了大使和官员,于翌年返日时,带上鉴真师徒,到达日本。在日十年,鉴真传授戒律,建造寺院,传播文化,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极大尊敬。在建造唐招提寺时,普照收到有人从唐土带回来送他的一块瓮,安置在唐招提寺金堂屋顶上。大寺落成之后四年,鉴真以七十六岁高龄圆寂。
《天平之瓮》主要根据日本奈良时代文化名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的史实,加以小说化而完成的。它以史实为主,辅以虚构,将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恳请而东渡日本传法的全过程,以及当时日本奈良的佛教状况和日本留学僧在唐朝的动态,以形象的艺术形式真实地展现出来。荣睿、普照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有详细的记述,作者完全尊重这段历史的真实。但他并没有囿于史料,对《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只留其名而无事略的人物玄朗,根据当时日本许多留学生或留学僧以各种理由长留唐土的基本事实进行了艺术塑造。陶德臻评价道:“《天平之瓮》的抒情性还表现在景物描写常常和人物内心感受交织,使情与景水乳交融,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复杂的感情与心理。”作品中除了对鉴真和尚承受自然与社会的压力,前后十一年六次东渡,双目失明后仍矢志不渝,最终到达日本,还描写了其他五个留学僧的不同命运。作者以这种悲剧的结果,展现一幅壮美的平安文化发展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图景。作品自始至终将日本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识“物哀”置于人物性格塑造之中,在反映主人公的孤独、凄婉的心境的同时,展现了人物的命运及对社会、人生的感慨。唐月梅评论道:“井上靖在其艺术创作中,把‘物’与‘哀’辩证地统一起来,在悲中求其壮,在哀中展其美,融会贯通了‘物哀精神’,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成就。”
长篇小说《楼兰》于1958年发表后便受到了日本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并获得每日新闻大奖。小说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彷徨湖》中获得的创作灵感,但它并没有进行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而是借助于历史中关于楼兰的片段存在,精心地还原历史。那些无法求证的空白,则靠合理的想象与推断去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加工。在楼兰发掘出来的女性木乃伊,被井上靖想象为自杀的楼兰王妃,这显然是采用了浪漫主义或者是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在她身上体现出的却是国破山河在的悲痛以及背井离乡的无奈。虽说是举国迁移,但是这些念头却曾在无数人的心头荡漾。反之,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出现,那倒是楼兰的一种悲哀了。在大迁移的途中,曾经有三个人脱离了队伍,打马回了楼兰城:一个是为了拿上自己的厚刃刀,另一个是为了把自己的宝贝藏在楼兰,还有一个是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把楼兰的大街小巷细细地转了个遍。井上靖似乎早已洞穿了人的感情世界,因而作品中的描写是那些离乡背井的人的伤心、痛楚、眷恋。小说中并没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存在,甚至除了历史上留下的那些名字,连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都少见。但历史并未因此而变得模糊,也许是因为芸芸众生才是历史的主体,无名之人才会让历史变得清晰。透过阵阵风沙,那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楼兰人的形象是那么清晰。他们的忧伤与苦难,决绝与留恋,梦想与失望都紧紧地与那个叫楼兰的国家和那个叫罗布湖的神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时空的这一端,仿佛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蹒跚的脚步。
楼兰—鄯善人作为命运的“抵抗者”,他们虽然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但其求生的欲望却同样十分强烈,直到最后失败仍一直坚持与其他民族乃至大自然进行斗争。这样的楼兰—鄯善人其实是被赋予了一种悲剧色彩。《楼兰》中人们的命运也主要围绕它来展开、深化。小说的叙述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始终扮演着客观讲述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将史实纳入虚构的框架中的同时,却做了隐蔽的并带有倾向性的描述。另外,在语言表层安排即叙述者的讲述中,那些关于自然的描写或叙述会给读者以“决定命运的因素是来自政治历史”的模糊认识乃至误导。所以当我们将其预言性或者回顾性的语言联系起来看时就会明白,是自然和历史同时决定了主人公的命运。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1]陈嘉冠:《温乎如春风凛乎若秋霜——井上靖小说艺术初探》,《日本文学》第1期,1986年,第208页.
[2]以杂志《小说新潮》的出现为契机,纯文学作家转而创作通俗小说。代表作家还有丹羽文雄、井上友一郎、田村泰次郎、舟桥圣一、石坂洋次郎等.
[3]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287页.
[4]唐月梅:《论井上靖的艺术世界》,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散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