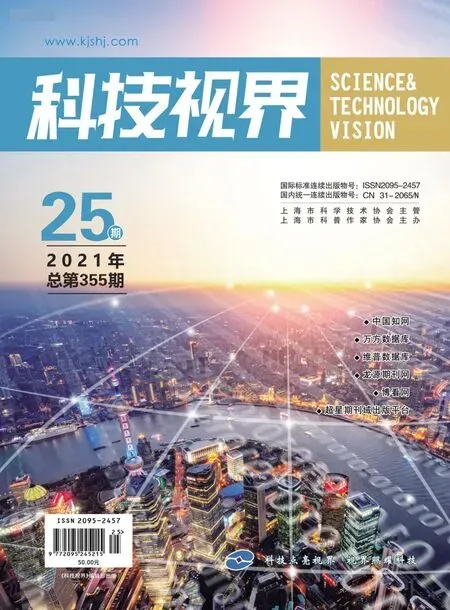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秩序——基于广州火车站春运拥堵事件的分析
白国强
(暨南大学特区与港澳研究所,广州市社科院 广东 广州 510053)
1 问题的提出
2008 年初广州火车站拥堵事件,震惊中外;这场事件起因于前所未有的持续低温、凝冻雨雪极端天气突袭大半个中国,造成电力中断,交通受阻。 归家心切的外来务工人员从珠三角大批涌来,从1 月26 日至2 月5 日的11 个昼夜,大约350 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一时间,广州火车站地区人潮汹涌、拥挤不堪。 最危急时在火车站广场及周边封路区域约5.7平方公里范围内最多滞留人数近40 万, 远远超越了安全容量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随时可能发生踩踏事故,危及旅客安全。 所幸的是最终旅客得到安全疏导,没有发生群体性的危及生命安全的交通、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因踩踏导致的群死群伤事件。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起典型而复杂的事件折射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实质。 在这一事件中,旅客的“进站上车”、保暖、安全、生理需求等与集体行动的秩序之间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按照集体行动的典型理论模型,在此情况下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这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的作出的贡献来分配。 这样,集体行动的理性结果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事件将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 但经过科学合理的控制和管理,却最终使事件回归秩序,回归安全,回归集体理性。 因此,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回顾和思考这一复杂而典型的集体行动事件,揭示其对于社会公共秩序引导和管理的意义,无疑具有现实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 集体行动的三个典型理论模型及其治理之道
关于集体行动的本原状态,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 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①而哈丁、图克和奥尔森则分别用公用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个模型,经典性地概括了集体行动的基本运作之道;实际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对前两个模型的综合和提升。
2.1 公地的悲剧及其治理之道
1968 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 Hardin)针对个体行为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使公共利益受损的现象,在美国著名的《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 《公用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 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 每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只羊,以增加个人收益,虽然每个人都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但每个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都选择多养羊来获取收益, 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于是,“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所有牧民也无法再养羊。 这个“悲剧”的原因在哪呢? 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 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②。
对于公地悲剧问题的治理,哈丁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说明了通过确立土地产权,把公地变为私人领地,可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因此,“公地悲剧”的治理之道在于:确立产权,清楚地确立“公用地”占有与使用的边界。 因为在产权不能够得到明晰界定的情况下,“过度放牧”的短期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边界的不清晰和非确定性,只能使公用资源过分提取直到耗竭。
2.2 囚徒困境及其治理之道
图克(Tucker)1950 年提出了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 该模型讨论了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出于降低刑期的个人理性选择而作出的检举背叛对方的选择。 这说明按照既定的博弈规则,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利益都受损。 在日常生活中,“囚徒困境”无处不在。
关于囚徒困境的治理之道,有学者③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是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若博弈各方都能采取“冷酷战略”的话,每个参与人就都能走出“囚徒困境”,从而使合作永远持续下去。但事实上,许多情况下只能是一次博弈。 二是信息沟通。 博弈各方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来达成某种协议,促成合作,以实现“囚徒困境”实现双赢或多赢。 而这需要信息畅通和博弈方的信守承诺。 三是引入某些群体规则,每个参与人都遵守这些规则群体规则。 用这些规则来约束群体中个体的行为, 并且每个参与人都相信对方也遵守这些规则。 四是引入第三方,对不合作者实施惩罚,这种方式也能使参与人走出“囚徒困境”。
2.3 集体行动的模型及其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模型是由奥尔森于1965 年提出来的。 其基本内容是:个人自利不会导致集体利益。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理性和自利的前提中推演不出人们会作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因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 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 如果团体中的成员都是自利且追求效用最大化他们就会采取以下行为方式: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上尽量少投入, 将自己应付的成本转嫁到他人身上,而尽量多地消费公共物品。 也就是大家都存在“搭便车”的倾向,因此,个人自利不会导致集体利益。 诚然,并非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不可能达成,一个人是否会参与集体行动,这取决于:个人获益度、效益独占的可能性和组织成本,是个人理性分析、算计和选择的结果。
而要达致集体行动的利益,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采取选择性激励。奥尔森认为,在规模较大的集体中除非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行动的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否则,集体行动难以形成;导致集体行动形成的重要手段是采用“选择性激励手段”。 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能自发地提升社会效用, 公共物品的产生要靠强制性的或选择性的方式,即要么强制执行,要么以奖惩机制来使外部性内化④。二是隐性激励。罗必良(1999)认为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所构成的隐性激励,可以有效约束或减缓“奥尔森困境”⑤。 除外,陈潭(2003)⑥认为对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通过政策配置或制度安排来达到目的: 即明晰产权,责任明确;市场交易,降低外部性;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
3 春运拥堵事件与集体行动理论模型:适用性和特殊性
春运广州火车站拥堵既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又有其特殊性。 因此,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对于分析和解决春运拥堵有着明显的理论指导意义,该理论的总体分析框架上完全可以用来分析火车站拥堵事件;而揭示春运火车站拥堵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对于公共管理也无疑甚有裨益。
3.1 适用性
(1)在追求公共产品特性上总体适用于集体行动的模型
解决春运火车站的拥堵,维持正常的交通秩序,对所有旅客乃至这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公共产品。 这符合公共产品的特性和判别标准。 首先解决拥堵和维持秩序是对所有旅客、现场工作人员乃至整个社会都迫切需要的,具有消费的兼容性;其次,对这种秩序的“消费”是非竞争性,对大家来说是平等性的,具有公益性;最后,这种秩序的维持和获得又必须是具有强制性的。
(2)春运集体行动中的一次性博弈
春运拥堵的解决和秩序的获得,对于一定范围一定时段拥堵在火车站及其周边的旅客和普通的工作人员人员来说,是一次性的博弈。 适合于“囚徒窘境”中描述的一次博弈的情形。 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旅客们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这种情况下的利益不仅表现为挤上火车、 还表现占领有利位置、 满足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等等),若任由这种状态“自然地”发生下去,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结果必然导致重大交通事故、重大治安刑事案件、打砸抢烧事件,以及因踩踏导致的群死群伤事件。 也就是说,博弈的结果对于牵涉其中的庞大的旅客和工作人员团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
(3)典型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春运拥堵与秩序形成是典型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 在奥尔森看来, 集团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关联性与排他的不可能性。 奥尔森在为桑德勒《集体行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几乎都是围绕两条定律展开的: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果”⑦。 第二条定律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不论个人如何理性的追求自身的利益,也不会导致集体理性结果的出现⑧。 在广州火车站拥堵事件中,众多旅客在个人理性的支配下,难以达致集体行动的理性结果,难以获得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拥堵”。
3.2 春运广州火车站拥堵的特殊性
(1)资源极端有限性与多种共时性公共品需求的衍生
在广州火车站区区5.7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由于旅客的高度集中,导致多种资源的的极端短缺。 并且衍生了许多共时性的公共品需求,这就形成了一对激烈的矛盾。 由低温冰冻而交通中断,运力的短缺;由运力短缺而致旅客的拥挤(公共空间的短缺);由旅客的拥挤而致秩序的混乱,公共资源严重不足。 更为严重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许多通常为私人物品的需求,由于旅客行动不便,受到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也演化为公共的物品(如个人的饮食、御寒衣物、药品等)。 而且,对这些公共品的需求在时间上是具有共时性的,几乎要求得到同时的满足。
(2)存在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多重博弈
春运火车站拥堵除个人参与博弈之外,还有群体之间参与博弈,形成了多重的博弈关系。 从其所涉及的直接群体来看,可分为三大类:民工、学生以及收入较低微薄的工薪阶层;另外还涉及到当地党委政府、铁道部门、公安武警、医疗保健和临近地区的居民、商户等。 从群体的细分来看,各种不同的群体,包括家庭式的群体、同事性的群体、同学性的群体、朋友性的群体、商业团体等以及参与维持秩序,解决公共需求的相关单位。这构成了一种多重的博弈关系。而且,群体的形成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春运火车站人群的流动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为获得秩序而牵涉其中的群体不是定型的“集体”。 这与一般惯常的集体行动有明显的区别,具有不定向性、无规则性和博弈结果的多种可能性,这进一步增加了火车站拥堵事件解决的难度。
(3)呈现多维度的扩散和波及效应
各种不同的群体,受各自利益和心理因素的影响,有不同的动机。 如回家者、返回工厂者、家庭团体票、学生团体、朋友、政府机关与团体等都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不同时间空间内,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并进一步出现多维度的扩散和波及效应。 从广州火车站拥堵看,它会进一步导致传染式的扩散,造成广州以及珠三角许多城市的交通拥堵。 这又进一步对其他的交通方式产生需求,导致其他交通方式的“拥挤”;而春节后大量旅客北上,是拥堵事件在时间上的延伸和波及;而个别情况(如旅客疾病、丢失物品、抢偷等)的发生,还可能会向更大的范围扩散,影响社会心理和秩序。
(4)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需求的高度聚集和相互转化
火车站拥堵事件中,公共物品与私用物品是高度聚集在一起的。 牵涉在火车站拥堵事件中不同个人和群体对各种公共物品与私用物品的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高度聚集。 这使公共物品与私用物品的性质和边界变得不确定和模糊。 事实上,在严重拥堵的情况下,许多私人物品的“私人”性质都发生了变化,靠消费者个人在市场上都无法得到满足,只能依靠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提供,如饮水、盒饭的提供。 而所有公共品的“公共性程度”却似乎变得更加严格,变得必须“公共性”、强制性地加以保障。
4 公共秩序的获得:类春运火车站拥堵事件的治理之道
春运广州火车站拥堵事件的治理, 除了上述理论模型抽象所反映出来的一般性解决途径之外, 针对春运拥堵事件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还应寻找更多的途径。
4.1 时空延展与资源扩展
为解决资源极端有限性与衍生共时性的多种公共品的需求的矛盾,必须进行时空延展和资源扩展。 春运期间,广州为了确保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的安全, 面对前所未有的人潮,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分流管控,统筹兼顾,因情施策,对滞留旅客建立起点、线、面全方位的控制疏导体系。 按照“科学划线、分区安置、有序疏导、控制外围”的原则,将疏与堵、安置与分流等措施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控制了旅客的盲目流动。 通过“延长路线,控制前冲;分区安置,疏导人潮;穿插切割,安全组合”⑨,达到了错峰、区隔和缓冲的目的。 另外,针对春运,有人提出“分流休假”制度,也不失为一种错峰的重要方法。 资源扩展也是一种应对此类事件的重要方法。 如广州市政协朱俊强委员建议加快建设新广州火车站。
4.2 秩序主导性群体的相互配合
在火车站众多群体中,党委政府部门、公安民警、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民兵、治(保)安员等多种力量都属于这一“博弈”事件的主导性群体,对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秩序起引导、控制性作用。 它们之间的力量整合、合成作战、协同配合, 保证了多重博弈中火车站春运正常秩序的恢复。如果不是各种安保力量密切配合、同心协力,确保了警力调集及时到位、后勤保障及时跟上、思想动员教育及时跟进,如此艰巨的春运安保工作任务是难以完成的。
4.3 信息畅通与信息过滤
在群体性事件中, 共同知识和一致信念是十分重要的。共同知识指的是所有参与人知道的知识。 在共同知识的基础上,达致一致信念的形成,有利群体行动整体效益的实现。 对火车站拥堵事件的解决来说,在春运前就应对天气状况和返乡人员人数进行评估,摸清春运期间的人员流动方向、购票地点的分布、确定疏散候车地点;建立及时、科学的告知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将天气状况、交通运输状况、车站的候车状况、候车或滞留旅客的安置状况及时告诉广大外来务工人员。 宣传春运安全知识,增强旅客人身安全意识,形成安全意识的一致理念,也十分重要;事实上事件本身也暴露出旅客个人安全意识的不足。 因此,保持信息畅通有利于“共同知识”和一致信念的形成。 另一方面,对有误导旅客、不利于公共秩序形成的信息要加以甄别和过滤,这样才能有利于公共秩序的恢复和维持。
4.4 统筹考虑私人物品和公共品的供给
鉴于在“拥堵”情况下,个人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限制,许多“私人物品”无法通过市场上的交易得到满足,从而转化为“公共品”。 因此,必须充分估计私人物品可能转化公共品的种类和数量,在考虑正常状态下公共品供给的同时,统筹考虑私人物品的供给,形成一种公共品和私人物品(包括服务)供给的系统应急机制。
[1][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8.
[2]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in science Dec.,1968,Vol.168:1244.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隋静.走出“囚徒困境”[J].价值工程,2005(9).
[5]王慧博.集体行动理论述评[J].理论界,2006,4.
[6]罗必良.“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J].学术研究,1999,9.
[7]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J].中国软科学,2003(9).
[8]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353-359.
[9]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5.
[10]陈翔,等.创新八大战术 破解世界难题[N].广州日报,2008-2-26.
注释:
①[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8.
②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in science Dec.,1968,Vol.168:1244.
③隋静.走出“囚徒困境”[J].价值工程,2005(9).
④王慧博.集体行动理论述评[J].理论界,2006,4.
⑤罗必良.“奥尔森困境”及其困境[J].学术研究,1999,9.
⑥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J].中国软科学,2003(9).
⑦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353-359.
⑧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5.
⑨陈翔,等.创新八大战术 破解世界难题[N].广州日报,2008-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