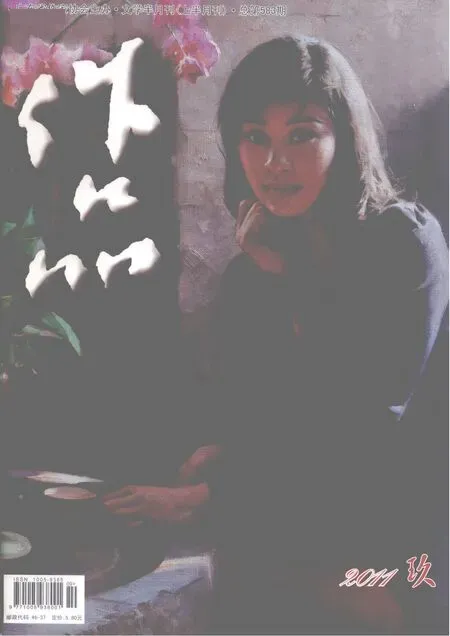给“T”们写点什么
◎张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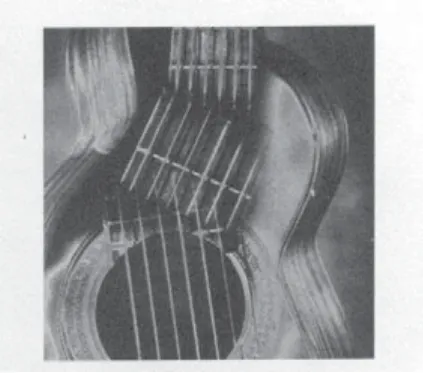
A
在与人的交往之中,有时会出现一个奇怪的规律。比如一个时期结识的朋友都姓李;这些北鞑南蛮的大李小李彼此不认识,但神秘地有着一刀切齐的共性:穷、倒霉、命不好。害得我——可是我又能有多大本事帮别人呢?害得我费了不少想帮人的心思。
过了些年,有一天不意中掐指一数,咦,朋友变了!
和那些稍嫌窝囊的李族人不同,这一拨的他们都姓王。我夹在当间,自然难免暗中比较:王族的人,不管他是哪一省的,都是胸中大志、身上一技,虽不能说个个顶天立地,却人人有惯做大哥的习气。弄得我也时常下船登车,得了不少的借力。
你问了:最近交往的朋友姓啥?
这回,不是在第一个字上同姓,而是在最后一个字上同名:净是“晖”(当然也有例外,如这一回的叶舟)。我很奇怪他们爹妈(正是我的同龄人)为什么就偏偏认定了日字边的晖,而不爱火字边的另一个。
他们的共性?几个晖,每一个都是老编辑、小作家、68-70后,差不多个个都是北漂。
他们作为编辑,淘汰了一批在体制的鸡窝里慢慢架子变横了的、我的编辑旧交。他们作为北漂,和我鸡犬之声相闻,自然想见就能见。他们作为6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能对我深入理解又能给我纠正的提示。他们作为小作家——或许就摸出一本书要我写序。
B
给人写序,这事和听人读书不同。我总是大大为难、左闪右躲、托词借故,如果依然不行,何止一口拒绝,我会不惜撕破面皮甚至恶语伤人——虽然那样做,无聊又不值得。
有没有主动想写的序呢?有一篇。给我一个海军的战友,海鹰弟的。他如黄继光一样冲向哒哒哒的枪口,我渴望能在给他的序中倾诉我理解的军人精神、尤其是“海军精神”。但他的那本集子并未诞生,许久以来,我发现他并不在意出不出书。也就是说,我没得到写的机会。
总之可以说,我是给人写序最少的。
很简单:我缺乏信任。我怕那种强说愁、轻盟誓的为他人立言,在后日被彻底地嘲笑。
那种与自己的序恰成悖论的、他的选择对我的语言的否定,使得我好像成了更主要的失败者。懊丧的感觉尤其无聊。谁都明白,倒这种霉无非由于耳朵软和心软,那么我要学会心硬,我开始了拒绝便没有拖泥带水,那以后再也没写过序。除了唯有一次的例外,但那是对李家老友的。
C
也就是说还是有例外。我非圣人,岂无例外?
我冷冷地注视着,这不大的小视野里,有些东西所以扰人心烦,就因为它们粘着情义、理想、初衷、原则……等等道理。在这时代,对中国人,上述的道理,是不好讲了。
但即便如此,给人例外感觉的催动,还是潮汐一般,时而涌来。
与此同时,世间的序产业比草原的畜产业变化更快,听说,已经有人写序收费,而且行情已经涨到了两万一序了!
我想,要求后世里的始终不渝,或许从根本上未必正确。在一个英雄主义被禁的时代,人很难扑向敌人的枪眼。
不如追求——至少把自己的子弹打出去。战火在电视的鼓吹下肆虐,新十字军的铁蹄动地而来,今天,那种通常藏在序言里的、二人盟誓般的潜语和关系,应该改变。一切都要服从“抗战”,一切都应该为着有效抗击新帝国主义的全球进犯。
给小字辈一点援助就是斗争;阴冷世间的无情,使得他们比盼望誓言更盼望温暖。拉他们的手一把,再踢他们屁股一脚,让他们动起来拉栓开枪,别在意明天他们怎么样。
是的,盟誓不如合作、话语不如行动、要紧的是——如同抵抗的合作、如同战斗的关系、如同战友的感觉。哈!我摸着了“2000后”的方式!
D
因为他们渐渐地一个个逸出晖字,我便随之应变,把他们统称为“T”们。
这一个年轻朋友的名字,是与晖不沾边的叶舟。叶舟不是北漂,在兰州,大概因为他与兰州一个叫做“一只船”的下町土巷有着感情纠葛吧,一叶扁舟的图景被他用做了名字。
兰州是茫茫大西北的码头。我自己的大半生,也经常从这儿下海,向着西固海、河湟甚至青藏新疆,撑开一条漏船,漂向万顷黄土。
我想,一是由于异族的色彩,二是因为叛逆体制的习气——这些母体的供养,使得西北的魅力决非东北所能比拟。于是,闯关东的不多,出西北的不少,为着代言或表达,为着成为这片热土的代表,世间一直层出着寻章问句的诗人,冒险跋涉的行者。只不过,如“午夜进城的羊群”,他们大都很快就消匿得无影无踪,由于不能溶入那片色彩,或者不敢那么叛逆。
一个青年自报家门,划着“一只船”,也进入了这片旱海。
他有锐敏鲜活的感觉,有快速流畅的文笔。他捕捉住了这座恋恋不愿脱尽昔日古风的城市的一些碎片,把它们写成可视可触的印象。然后他企图表现自己,如同辈人一样,把满腔莫名的思绪恣情倾泻。也许他和他们一样,一直没有与这片黄土深处的岩心,发生轰击般的相遇,也就难能在作品中纠缠一些更大的命题。
包括我,每个在这片海里的人,都探寻和碰擦着拦路的质问,有意或无意识地到达过一些关口。有些是严峻的、真正的关口之前的质问。叶舟怎样面对这些提问呢?——这是大有意味的问题。
至少他没有清晰地回答。他的作品厚厚地积累着,为他打开的门愈来愈大。兼之时光如白驹过隙,在我们都在旱海里逐日衰老的过程中,渐渐我看不清那只船了。
——那只船究竟正在驶向哪里?好像没有谁这样问。
E
所以,当他们要我写序,我就提出疑问。

我想说,他们下手和表态都太快了。写的也许也太多。虽然一些诗人在“七十年代”费了那么大劲才学了点皮毛的现代派手法,虽然一些老者在半个世纪挣了半条老命才凑够了篇幅的长篇大部头——对他们乃是无师自通玩耍自如;但是我不愿假装没看见他们的——某种空洞和一丝轻浮。
他们缺乏大时代的灵感启迪。缺乏文学之外的政治颠簸。他们的一首两篇经常是相当优秀的;但当他们获得了话语权、大量地印刷和出版以后,他们的书,常呈现为一种——愈是苍白愈无限堆砌的、哲理与感情的杂乱搅拌。
但是他们靠这一手锤炼了自己。应该说,“T”一代的语言异常流畅,他们处身的生活也许是苍白的;但他们传达自己的枯燥、苍白、空洞的情绪,则是浓浓的、绘声绘色的、真挚的。
没人愿猜这一代人会走向何方。
没关系。也从未有哪一代像他们这么随时准备破罐破摔。他们从自己父兄身上,看惯了人在历史中的被淘汰,信服了人在历史中的渺小。抱着这一点经验,他们自认深刻,冷眼看着自己疯狂地攫取题目。
他们因为知道再也没人会对他们的时代喝彩、于是挑了文学躲避和自娱。他们都读着北岛听着崔健直到进入社会,他们没有流露——他们惟妙惟肖的复制,导致了他们对偶像的怀疑。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与横行全球的反革命主义并不一样——因为只差一个台阶,革命与他们交臂而过,使他们三生抱憾。乏味如腐的生活,映衬出革命的魅力,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哪怕飞蛾扑火,哪怕一回就死,愤怒至极而无计挣脱的他们,是人道主义的革命(不能没有这个定语)、和丰满的文学(对见多识广的他们,文学的身段不丰满可不行)的后备军。和老、中、小三代孪生的右派相比,他们的遗传不一样。也许他们身上不安鼓噪的,正是这古老民族赖以回生的、最后的基因。
——或许,这就是你我的维系,我的弟弟们。
最初北漂的潜台词,往往是早年的清贫。我直觉我的这一伙“T”都不是纨绔子弟。他们都有石灰窑或者一只船的记忆,都有老百姓的背景。他们编造不出也不愿编造童年细节,但朦胧的人生襁褓,控制着他们的现在。
这样的一种襁褓,使得他们在爬行了漫长的模仿之后,不仅对文学的赝伪渐渐扬弃,而且也对政治的谎言逐步识别。最终话语是简单的,就像炉火纯青的文学都朴实无华。但社会公正的真理,也决不是帝国主义的宣传,待他们认清这些的时候,他们自会选择行为。从黄继光,到迈克尔·杰克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