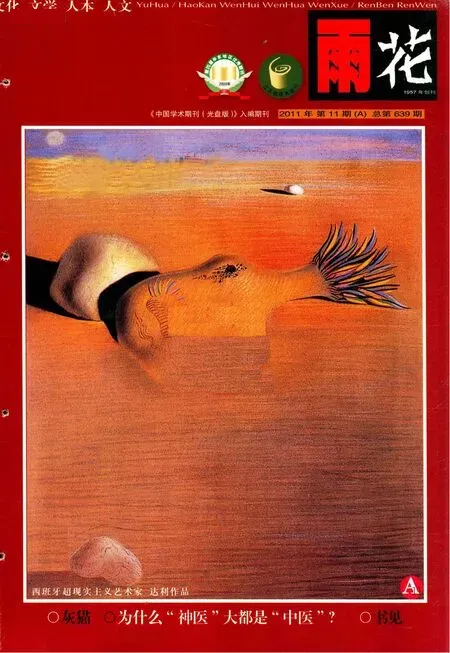我的两个母亲
● 郭苏华
在静夜里,母亲切芦苇的声音很脆,我喜欢母亲的这个动作,带着母亲性格里的坚毅,这个动作还意味着母亲一夜的工作将要结束。
楝树下的家
很小的时候,门前长着两棵楝树,高大的母亲常在楝树下坐着,和邻居聊天,说一些家常话。母亲常常去田里割草,背着一个柳条编的篓子。母亲的脸上总是流着汗,后背的衣服常常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的鞋子里全是泥巴,脚丫里也是,一直沾到脚面上。
母亲没有孩子,她把我领养了回家。我常常由祖母带着。她不怎么管我的事,她要慢慢习惯生活里多出来的这个角色,这个陌生的孩子天真地喊她妈妈,而她心里会觉得很不自在很别扭吗?我没有问过母亲。
小时候,祖母在土屋自己的床沿上坐着,母亲的门旁边挂着一盏浑身乌黑的煤油灯,母亲在昏黄而柔和的灯光下编席子。母亲的身下已经编了厚厚的席子。祖母带着我,坐在床沿上讲故事,我的两只脚在床沿下晃荡,眼睛却一直看着母亲。母亲像一个温柔的模糊的影子,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身子的动作很轻,芦苇在母亲的怀里跳跃,一花编上去,一花编下来,到头了,母亲用菜刀把芦苇的梢子切掉。在静夜里,母亲切芦苇的声音很脆,我喜欢母亲的这个动作,带着母亲性格里的坚毅,这个动作还意味着母亲一夜的工作将要结束。但,母亲的身子又转过去了,她又开始了另一边的编织。祖母的故事已经告罄,不得不继续搜肠刮肚来满足我的欲望,祖母的故事带着明显的编造的痕迹,这个连幼稚的我都感觉到了。但,我愿意在母亲的陪伴下,被祖母的故事迷住。
母亲没有孩子,父亲没有责怪过她。祖母曾经责怪母亲早上起得太迟了。因为,她和父亲拥抱着,一直睡到天亮。在那个家长制还比较严重的时代,母亲这个看起来不怎么勤劳的女人是要受到批判的。但父亲庇护了母亲。我常常想,这也许是母亲的爱情。
高大的母亲其实很壮硕。我以为她会一直那样强大。她会和村上的婶子嫂子在晚上去偷生产队里的山芋藤。在漆黑的夜里,我听见我家的塑料纸蒙的窗户嘭嘭地响起来,很神秘的声音,然后,母亲在黑暗里,悄悄起身,生怕惊动身边的我,然后黑着灯就出去了。
那时,我开始知道什么是生活。有点残酷的生活,把母亲变成这样一个斤斤计较的甚至有点不太光明的人。很容易的,我就原谅了母亲的行为。
只有阴天的时候,母亲才会安静下来,在清静得有点过分的屋子里坐着。她坐在屋子的门旁边低着头做针线,她把破旧的衣服拿出来缝补,或者给我做鞋子。母亲尽量用好看的紫色或者红色的布给我做鞋。可是,我一直为此感到羞耻。我们班上只剩下我和一个男生在穿母亲做的鞋。我过分敏感的心常常感受到贫穷给我的打击。我不敢在人前走动,我不敢对母亲说,我不穿你做的鞋。我怕伤了母亲。
母亲也会坐到堂屋古老的桌子前,从黑暗的屋里拿出两面都可以照的圆镜。找来一根锥子,一根长长的白线,把白线的一头拴在锥子上,锥子固定在桌面上,她就用白线来扯脸上鬓边的一些汗毛。我常常在桌子旁边趴着,看母亲给自己做美容。我从来不觉得这样会使母亲美丽。但母亲总是反复做着这样一件事。在母亲杂乱的梳妆台上,我发现了一个装了白粉的小盒子,上面放着一个粉红色的毛茸茸的粉扑子。我这时才想起来,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爱美的女人。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她用那个粉扑子,我甚至以为,她即使搽了粉,也是不好看的。
母亲有时候也会对我讲村上男人的一些事。她说,一个父亲的朋友来看她,掀了门帘就进来了。一进来就坐到母亲的床边。那是个风流成性的男人,几乎村上所有好看一点的女人都和他有染,但他却和严肃的堂堂正正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正色道,你坐到那边的凳子上,我们正正经经说话。他一下子变得讪讪的,坐到一边去了,自此,他一直很尊敬母亲。
可是,我并不懂男女的事,母亲为什么要告诉我呢?那样一个男人,我也是喜欢的,在冬天里,穿着漂亮的大衣,大衣里面是红色的毛茸茸的衬子,穿在一个年轻的男人身上,别提有多么吸引人。可是,母亲拒绝了他。
其实,长时间地爱一个人,总会厌倦的。虽然,父亲那么好,善良,厚道,有着温暖的爱,可是,在一个女人的心里,总会想一些什么的,在漫长的而且是贫穷的日子里,总会有一点幻想的吧。母亲从来是温暖的贞洁的自制的。可是,她为什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很长的时间后,我想,母亲是不是也喜欢被别人喜欢的,哪怕是那样一个风流的男人,他的倜傥实在没有多少人能够拒绝。
母亲渐渐老了,单薄的身体那样瘦弱,你甚至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年轻时候的母亲的壮硕。
像那轮美丽的夕阳,母亲的晚年就这样来了。我站在夕阳的光辉里,有点惆怅地想,这样温柔的美丽的光辉,不知道还能照耀我多久,我站在那里读着夕阳,我怎么能读得懂,读得透母亲长长的沧桑的一生。
河边的母亲
小时候,很早就知道有一个姨娘,在一条叫唐玉河的水边住着。母亲常常带我去看她。她们姐妹的走动真的很频繁。姨娘家低矮的草房,那么矮,几乎要碰到大人的头,姨娘家的屋子很黑,白天也视物不清。一些颜色不明的低柜挤满了屋子,柜里存放着粮食。母亲不止一次暗示我,姨娘家很贫困。可是,姨娘脸上的笑容总是灿烂的,那微笑里有一种烛照我心灵的光辉,那么温柔的。我喜欢姨娘脸上那些柔和的线条,竟然胜过对母亲的。姨娘一见我们来了,就异常快活起来,在门前的丝瓜藤里到处找青色的长长的丝瓜,要给我们煮丝瓜蛋汤饼,金黄的鸡蛋打在碧绿的丝瓜里,不知道有多么和谐和美。我从此爱上这样的吃法。好像每一样经过姨娘手的东西到我这里都会变成最爱。
夏天的时候,姨娘会突然从小路走到我家。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包里放着自家园子里长的黄黄的杏子,直到现在一看到街上开始卖麦黄杏子,我的脚就走不动了。姨娘往往留在我家吃午饭。门前的两棵楝树就成了午饭时给我们遮荫的大伞。母亲烧了韭菜,青翠的韭菜,我是不喜欢吃的,塞牙。我对食物的不喜欢,母亲从来都迁就着我,因为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姨娘给我裹了一个韭菜饼,圆筒状的,每一层里都有摊匀的韭菜。我接过来,居然一下子把它吃掉了。从那之后,我就喜欢上这样的吃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真的有原因,那就是因为姨娘这样裹给我吃过。
我心里常常是不明白的,为什么看见姨娘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姨娘是我真正的母亲。
姨娘有七个孩子,死了两个。我是最小的。在生活里,姨娘是一个坚强的人,我没有看见她哭过。六十岁的时候,还给小哥他们挑水吃。七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到唐玉河边去割芦苇,一个人在密密的芦苇里钻来钻去。八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给小哥他们种地,小哥一家出去打工了。
姨娘从来都是那样乐观的,没有一个媳妇说她不好。她在苦日子里熬过,但从来不叫苦。
我回家的时候,她会自责地说,什么也没有给你。我笑说,我什么都有了。我不要。
姨娘老了。我因为忙,很少回去。我坐车从唐玉河的这一座桥过去,总忍不住把头朝向河的另一头望去。姨娘在那里住着,我能想象她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喊她一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