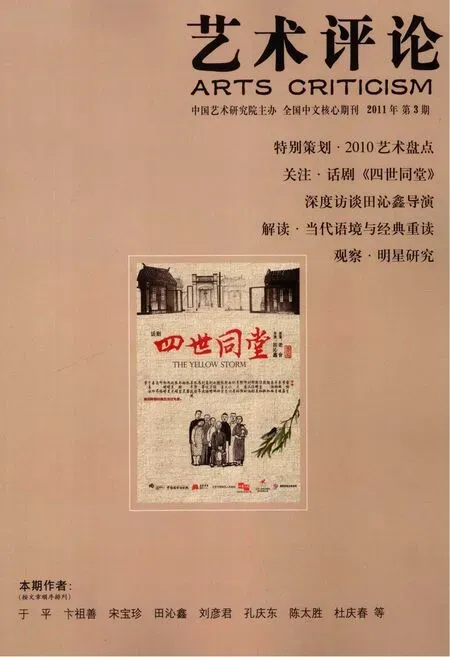童年记忆的世界
——读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石天强
童年记忆的世界
——读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石天强

如同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莫言小说《透明的红萝卜》[1]中存在着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冲突。儿童世界——即黑孩儿的世界——是审美的,叙述人通过塑造这个孩子对声音、色彩的独特感受,构建出一个独异而自由的空间。而成人的世界则是现实的,这个世界充满着暴力、冷漠和人情冷暖。而孩子的世界就在成人世界的不断挤压中被逐渐摧毁。成人的世界因此是反审美的。显然,莫言小说这种空间的塑造形式具有明显的象征色彩。而我们的问题则是,作者的叙述形式,对这种世界的塑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又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两个世界
我们注意到,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黑孩儿在工地上干活,发现了透明的红萝卜,然后努力去寻找被小铁匠毁灭掉的红萝卜。一条是小石匠、小铁匠还有菊子姑娘之间的感情纠葛及其悲剧结局。两条线索相互纠缠,互相牵制,并在叙述层面上形成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
其实莫言小说的情节性并不强,故事结构也并不复杂,这一特点在这部小说中就显示得十分清楚。但莫言更注意故事的塑造方式,通过转换故事讲述的视角塑造一种阅读的惊奇。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叙述人在讲述故事过程中叙述视角的跳动,尤其是当谈到黑孩儿的时候,叙述常常会转移成为孩子的视角,也只有如此,小说中色彩斑斓的世界的出现才具有叙述的合理性。这个世界与成人世界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对立的、复合的、协调的等等。小说中黑孩儿的世界存在于成年人世界的缝隙中,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空白之处,也是在成人的世界之外,黑孩儿世界的审美价值才具有独特的意义。但是这种叙述视角往往又会被成人世界的视角打断,这时,粗粝的现实世界就会凸显出来,而将审美世界流放了。
莫言十分注意对感觉世界的塑造,尤其是刻意放大叙述的主观感受,从而塑造出一个光怪陆离、不同寻常的声、光、色、味的世界。有评论者很早就指出莫言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植根于农村的童年记忆中的世界,一种儿童所独有的看待世界的全新眼光”,在莫言最优秀的篇章中都表现出了“儿童所惯有的不定向性和浮光掠影的印象,一种对幻想世界的创造和对物象世界的变形,一种对圆形和线条的偏好。”[2]也因此,许多评论都集中在对莫言小说感觉世界塑造的独特性上,而忽略了这种独特的塑造方式和叙述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莫言小说中叙述时间往往与故事发展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由于注意塑造个体的主观感觉,这使得故事的讲述时间往往要慢于故事发展的实际时间,并因此而削弱了故事的情节性。同时故事的结局往往又是悲剧性的,对于故事的叙述由于刻意从一个“儿童式的”视角去刻画,并着力于塑造出一个美感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冲淡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儿童世界时刻处于成人世界的挤压中,同时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在语言叙述的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前者总是处于一种诗意化的语言结构中,同时讲述的速度明显放慢;而后者则常常是一种普通的乡村土语,叙述性很强,这种语言充满了一种暴力、粗俗的色彩,带有明显的乡土世俗气息。而儿童世界的想象性会在这种粗俗的语言中突然出现,又往往被这种语言突然中断。这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暗示出叙述人在叙述态度上的差异:即存在于儿童记忆中的乡土和存在于理性思维中的乡土之间的差异。前者是美丽的、充满了个体童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精神幻觉;后者则是现实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反思之后的结果。前者努力在塑造一个美的世界,而后者则在塑造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前者充满了温馨、愉悦,而后者则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前者是儿童似的,后者则是成人化的;前者更富有感性的色彩,而后者则充满了理性的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成就了《透明的红萝卜》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莫言自己也承认,一方面他认为,“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另一方面,“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3]前者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体体验形式,而后者则是一种带有理性反思意味的思考;前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也因此在小说中以“美”的形式出现,后者则是一种在文学价值层面的追求,也因此具有一种批判的意味。此二者纠缠在一起,就成为《透明的红萝卜》中两个色彩对立分明的世界。
悲剧性结局
但两个世界在小说的结尾都以悲剧收场,其原因何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儿童世界的毁灭不仅仅来自于物质的贫困,来自于情感的匮乏,还来自于个体的麻木和蒙昧。而成人世界的毁灭则来自于现实世界中个体之间的利害冲突,来自于个体的无知与人性的弱点,还有命运的强力。小说中,小铁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挤走了师傅,而他的师傅也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烫伤了徒弟的胳臂;小石匠和小铁匠为了菊子姑娘大打出手,老队长因为黑孩儿拔光了地里的萝卜而愤怒地将黑孩儿踢倒……现实世界就处于这样一种争夺和为争夺而出现的暴力中。暴力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中,还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中,而且也只有这种语言模型的日常化才意味着暴力的日常化。
在这样一种世界中,黑孩儿的行为是怪异的,这种怪异不仅来自于他对自我世界的沉迷,还来自于现实世界对他的判断——他的种种行为都不符合现实利益支配的逻辑。但在现实世界中,黑孩儿的行为同样具有一种暴力形式,他为成人世界的暴力所侵犯,同时他也以暴力的形式回击成人世界。而且一旦黑孩儿进入到成人世界中,他的行为就只能如此。小说中,黑孩儿最让人费解的行为就是在结尾帮助小铁匠打小石匠。而其根源则在菊子姑娘身上。菊子姑娘在黑孩儿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她几乎是出于母性的本能照顾黑孩儿,从而使这个丧失了爹娘、又生存于继母暴力下的孩子获得了从未体验过的爱。但黑孩儿无法容忍这份爱被他人剥夺,尤其是当他发现了菊子姑娘和小石匠之间的情感秘密时,他脸上闪现出的“冰冷的微笑”几乎展示出了这个孩子内心深处的冷漠和仇恨。爱与恨处于如此紧张的两极状态中,也因此黑孩儿才会毫不犹豫地在关键的时刻去袭击曾给予自己帮助的小石匠。这时候,小石匠以前的一切都无法替代他强占菊子姑娘带给黑孩儿的愤怒,也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孩子丰富的感受性的内心深处所隐含的可怕的一面,我们才可以理解黑孩儿行为的怪异,而菊子姑娘给予黑孩儿的爱则成为自己命运悲剧性的重要原因。
有评论认为,莫言的深刻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试图超越历史直接窥查人的本性,历史在他这里只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刺激,他更关心人心和人性的种种反应。他不愿恪守任何关于文学的既定规范,甚至也对还在禁锢人们的道德律条产生怀疑。他极为痛恨虚伪,而宁愿用自己的笔去真实地揭示丑陋。”[4]黑孩儿的矛盾性就体现在作为一个被想象的个体和作为一个想象世界的个体之间的矛盾,前者寄托着叙述人回归故土的情思,展示的是记忆世界中故乡璀璨华美的乐章,展示的是人性中美丽灿烂的一面;而后者则是故乡在反思世界中出现的形式,这种人性深处“恶”的力量对个体的毁灭,并塑造一个出具有“恶”的因素的个体;黑孩儿不仅是一个被摧残的对象,同时他还是一个摧残世界的形象。这种个体形象上的矛盾在小说叙述层面上的表现,就是小说塑造方式和叙述行为之间的矛盾。
苦难的张力
这种由“恶”的力量支配的世界同样是苦难的世界。《透明的红萝卜》是苦难、饥饿和美丽共同组成的世界,黑孩儿是这个世界的生存者、体验者,也是这个世界的见证者和描述者;而他在被他人毁灭的同时,也以暴力的形式参与到对世界毁灭的进程中去。叙述人努力通过不同人的眼睛改变着我们对于乡土世界的感受和体验,重新组织一个新的经验世界。莫言承认《透明的红萝卜》有着强烈的童年经验色彩,一是童年时代对于饥饿的记忆,二是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与我的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儿虽然不是我,但与我的心是相通的。”[5]
来自于乡土的作家对于乡土的描绘往往不同于来自于城市的作家,二者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乡土是否存在着童年记忆,而且童年记忆往往以各种形式进入到小说的文本中。来自于城市的知青作家对于乡土的描写十分复杂,例如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就充满了对乡土的赞美,小说几乎没有太多的情节,以回忆的形式将自己在乡土中遭遇的困苦还有面对困苦的坦然,与乡土农民的淳朴、热情、真诚表述了出来。而另外一些作家则往往将乡土描述为一个神圣而苦难的地方,一个重新塑造自我灵魂情感、重新拯救自我沉沦的地方;而个体在乡土中的遭遇既是一种不公正的历史境遇,也是个体感受农民生存苦难的机遇,更是重新塑造自我神圣形象的开始。因此在苦难的塑造上其着眼点更注重知识阶层个体在其中的感受。如张贤亮的小说《马缨花》、《绿化树》等。这类小说对于乡土苦难的描述往往更是实现叙述人主体精神价值的修辞手段,并使主人公具有分担“苦难”的价值色彩。但在上述诸种类型中,叙述人的叙述语气具有明显的“客居”色彩,这种态度不仅将个体置于故事之外,也将叙述人置于整个叙述之外。
莫言对于重塑乡土具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他认为“农民的苦难感与知识分子、右派的苦难感还不完全一样,不要把知识分子自己的苦难感强加到农民头上,结果写出来的农民一个个像知识分子。”“从我自己对农村的感受出发,我觉得农村生活并不像‘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笔下所表现的那样暗无天日,悲悲戚戚。农村生活的确很艰苦,但农村生活并不是一点欢乐也没有。我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能够体会农村生活的欢乐与痛苦。为什么不能写农村生活欢乐的一面呢?”[6]也因此,莫言笔下的农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尤其当这个世界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时。莫言将乡土世界中人们的言语,劳动的行为,还有这一行为中蕴涵的复杂的情感以一种美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看一下小说中打铁的那段描写,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有魅力的章节之一:
老铁匠从炉子里把一支烧熟的大钢钻夹了出来,黑孩儿把另一支坏钻子捅到大钢钻腾出的位置上。烧红的钢钻白里透着绿。老铁匠把大钢钻放到铁砧上,用小叫锤敲敲砧子边,小铁匠懒洋洋地抄起大锤,像抡麻秆一样抡起来,大锤轻飘飘地落在钢砧子上,钢花立刻光彩夺目地向四面八方飞溅。钢花碰到石壁上,破碎成更多的小钢花落地,钢花碰到黑孩儿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钢花与黑孩儿肚皮相碰撞以及反弹后在空中飞行时,空气摩擦发热发声。打过第一锤,小铁匠如同梦中猛醒一般绷紧肌肉,他的动作越来越快,姑娘看到石壁上一个怪影在跳跃,耳边响彻“咣咣咣咣”的钢铁声。小铁匠塑铁成形的技术已经十分高超,老铁匠右手的小叫锤只剩下干敲砧子边的份儿。至于该打钢钻的什么地方,小铁匠是一目了然。老铁匠翻动钢钻,眼睛和意念刚刚到了钢钻的某个需要锻打的部位,小铁匠的重锤就敲上去了,甚至比他想的还要快。
姑娘目瞪口呆地欣赏着小铁匠的好手段,同时也忘不了看着黑孩和老铁匠。打得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也是老铁匠最悲哀的时候,仿佛小铁匠不是打钢钻而是打他的尊严。
这不仅是师徒打铁的过程,也是两个铁匠之间竞争角力的过程:老铁匠的局促,小铁匠的放肆,老铁匠对自己力不从心的掩饰和小铁匠步步紧逼、得势不饶人的心态,都在这个过程中被传达了出来。同时叙述人又通过不同的人的眼睛重新叙述着这个场景中的含义:在菊子姑娘眼中这是一个充满了美感的世界,小铁匠的身影映在石壁上,充满了力量和动态、还有生命的活力;而在黑孩儿的眼中,这是一个让他窒息,让他沉醉甚至是忘记自我的场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世界中。也是在这种投入的状态中,可以看到黑孩儿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他无法真正感受到这种场景中微妙的竞争状态、无法感受到这个场景中老铁匠内心世界中的悲哀和恐惧,面对年龄的衰老而将丧失一切后所带来的对世界的恐惧感。
但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塑造,莫言不是回避了乡土世界的苦难,而是将这苦难推到了小说的远景。黑孩儿是一个身在苦难中却没有苦难感的人,在小说中,苦难是通过老铁匠的声音,通过老铁匠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老铁匠那满是窟窿的围布,还有默然的姿态,无不是苦难和安于苦难的缩写。而那猛然间唱出的戏文,既是对苦难世界的表述,也是对世界苦难的无奈抗争:
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
这段凄怆的旋律曾反复在文中出现,它曾化解过小石匠和小铁匠之间的冲突,也曾传达出老铁匠在临走之前的凄苦无奈。它与黑孩儿的想象世界形成了呼应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老铁匠是一个洞彻苦难世界的觉者,而黑孩儿则是沉于苦难世界中的迷者。这一老一少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又不无相通之处。而在这种苦难中个体之间关系的漠然,更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冷寂。
《透明的红萝卜》所呈现的世界就存在于这冷与热相交叉的世界中,黑孩儿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份子。但他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中困难的体验者,苦难的背景化使黑孩儿在精神上外在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激情与这个世界麻木的自在性之间,叙述人对故土的所有情感得以释放。
注释:
[1]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2]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1页。
[3]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1页。
[4]夏志厚:《红色的变异》,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8页。
[5]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6]莫言、杨杨:《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第11页。
责任编辑:唐宏峰
石天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