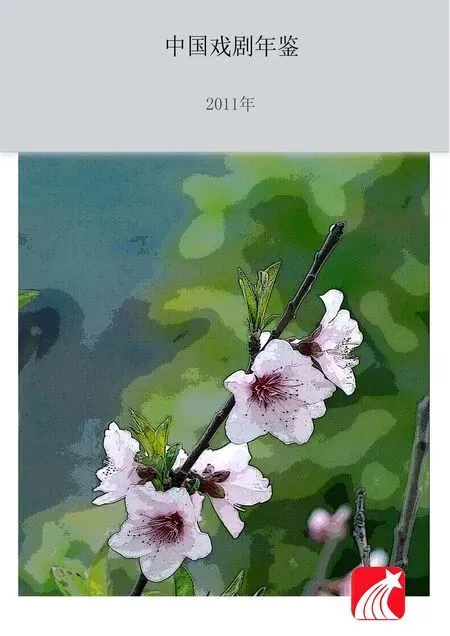关于《陈仲子》
王评章
关于《陈仲子》
王评章
《陈仲子》是一部写得很古朴、很有古意的剧作。这种古朴来自作者的才华,也来自他对传统戏曲的理解。这个戏也有人称它为一个哲理剧,然而其中深刻的人物形象及其作者所倾注的对时代、对精神追求者的灼痛的关心和无奈,则是更深入的内容。
在当代戏曲文学创作中,元杂剧明传奇的诗文传统大多被日常口语化、叙事工具化所取代,戏曲性有被话剧性所取代的倾向。中国戏曲元、明、清在其鼎盛的文人士大夫戏曲中,宗的是诗学,走的是由诗及词及曲和文(包括文人小说)的方式来叙事的道路。文人戏曲的创作源头、写作惯例并不来自社戏祭祀和变文说唱,并不来自民间。《陈仲子》唤醒我们的正是这种久违的文人戏曲的审美兴奋,它兴灭继绝的正是戏曲士大夫诗学的传统,使人蓦然有戏曲这一传统“魂兮归来”的惊喜。的确,新时期以来的戏曲文学几乎把这优雅古典的一脉彻底斩断了。就这点说,是让人非常怀念张庚先生的“剧诗”说的,他必是感受、意识到创作实践中戏曲“诗”的传统、精神、美学特质的流失和远离,必是感受、意识到小说、话剧的叙事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覆盖戏曲的危机。
《陈仲子》呈现出鲜明的语言、文字意识,风格、文体意识。王仁杰的语言、文字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他追求的是诗文的简约、韵味,朗朗上口,于雅致中求本色,于韵味中求通达,而不求案头文字的华丽、意象、用典。唱词用字用词古雅,但力求叙事抒情的直白,书卷气浓却不深奥迷离。对白则几乎都是韵白,用词文白相杂,但白都被文浸润,念起来既明白,又有文绉绉的节奏与韵律。对白用词并不晦涩偏僻,句式却是文字化的,句子短而不促,讲究平仄声调,多用虚词衬字,句子基本是词组性、连缀式的,而非修饰性、主谓式的,多是四字、二字的节奏,大体上是文言的而非日常口语的句法句式。他将语言文字化,因为比起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流失更少,古典的意蕴积淀更多,传统的隐性支援更大,比起语言,文字更加洗炼,更有节奏和韵律;他又将文字语言化,因为语言更加明快、晓畅、生动。他的语言、文字充分、直接地呈现诗文所要求的语言、文字本身的美,本身的诗意,本身的音乐性。这种“古典”的文字,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剧作家能够达到了。
《陈仲子》有一种透明、洗净、古朴而又典雅的诗文风格,总体上给人重笔墨、重文体、重韵味的感觉,有一种散淡、舒缓的节奏和韵律,从容不迫,不露痕迹,不见烟火气。这也是王仁杰剧作风格、文字的基本特点,但在这个戏中显得更为突出。似乎他决心在这个戏中把一切进行简化,以使自己的审美追求更加风格化,通过简单化来实现纯粹化。或者这一是与题材、主题有关。表面上这个戏也可以看作是个哲理剧,戏中表现了方法论的思考:再好的追求,再严肃的精神追求,只要极端化,就转向反面。戏表现了这样一种“异化”的过程。当然戏更深一层,写的是面对着巨大的社会、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坚守、追求越来越显得渺小、孤独、脆弱,命运越来越“荒谬”。这就要求与现实性戏剧的丰富性、写实性有所不同。但对于王仁杰来说,或许题材、主题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能否满足文体、表达风格、适合语言。风格、文体并不只是为题材、主题所决定,而且本身也选择、规定着题材、主题。重视怎么写而不仅仅重视写什么,这是王仁杰与当代绝大多数戏曲剧作家的不同之处。这也包含着他对戏曲的理解:比起话剧等等,戏曲的形式要求、形式美是更紧要的。
二是与对戏曲结构的理解有关。除了采用传统的副末开场、自报家门等手法外,戏采用了传统的“一人一事”写法。一人即陈仲子,一事即求廉。戏由求廉的一个个精致有味的故事和场面联辍起来,其中的联系,并不以事件、场面的叠加造势来构成推进的速度、紧张的气氛和高潮的冲击,而大致是传统的平稳有致的“起承转合”,求的不是话剧的矛盾、冲突、高潮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一气呵成,而是文气、诗意的流转贯通,文体上的滴水不漏。杨绛先生说中国戏曲的结构与章回小说结构相同。茅盾先生说章回小说的结构是园林式的,故事情节有时只是园中小径,它串起的不同景点才是重要所在。观众在这里流连忘返,演员在这里施展浑身解数。这些景点之间有结构、逻辑的关系,但并不一定层层相扣、第一景点成为第二景点的铺垫、直赴中心景点,并且中心景点也不—定就是最好看的。人物性格、心理单一、定型,没有什么发现、突转,戏剧性在于人物心理的细微活动,看来平平淡淡,絮絮叨叨,却写得有情有趣,摇曳多姿。传统戏曲的戏剧性,有时往往在于生发细节的巧妙之中,剧情、人物便蓦然爆发出灿烂的光彩。中国戏曲与诗、词、画—样,不以复杂为美。但这需要提炼,单纯是为了深致。剧情的简约正是为了抒写人物的情感,性格的提纯正是为了叙写心理过程的一波三折,对人心人性幽微曲折、闪烁不定的角落进行开掘和放大,即所谓的“散点透视”。大事件有震撼力,观众易被故事、情节的轰轰烈烈裹挟而去,取的是“势”;小细节不着痕迹,观众有时间去品味、咀嚼,得的是“味”。戏曲的观众是既要投入剧情又要有距离地观赏,他们不能老是被紧张的剧情和急遽的语速拎着走,要有时间让他们拼七巧板,太快了他们就是在看万花筒了。
《陈仲子》的戏剧性还来自喜剧性。这一方面是人物性格、思维方式的喜剧性,真诚与荒谬、严肃与滑稽的反讽;另一方面是科诨,这主要是门子的戏,那些即兴的调笑,充满生活和艺术的经验和智慧,既交待了历史背景,又讽刺了当前的现实。这些戏谑使得历史与现实的界限瞬间模糊、开放,观众的心理、情绪一下子生动活泼起来。
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陈仲子》“写一位认真、执着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历史人物,在那个时代,不但完人当不成,最后竟连人生的目的也迷失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要认识陈仲子,还得从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谈起。
关于陈仲子,我只见过《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以及剧本所取材的明人小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中的“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对陈仲子先是酸溜溜地称赞,然后是讽刺和数落,说他哪里廉,这样做人只能变蚯蚓了;荀子说陈仲子是比贼还坏的盗名贼,说他又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而以斯惑愚众;韩非子挖苦他是一无是用的石头一样笨重的实心葫芦;齐威后则破口大骂:于陵那个陈仲子既不为朝廷效力,又迷惑百姓,干吗至今还不杀他?使人奇怪的是陈仲子竭力使自己销声匿迹,一不干政二不设馆三不著述,干吗这些显赫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此容他不得?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陈仲子太纯粹了,从而使精神、政治权威们甚至使时代陷于狼狈。陈仲子以其存在,使他们的冠冕堂皇都露出破绽。如果陈仲子的行为构不成对他们内心遮掩的东西的烛照,他们本不必共同声讨他们所藐视的小人物。倒是“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另有见地,称他是时代人心的“药石”,可以浊里澄清。既是药石,自不能当饭吃,只是教大家学习陈仲子精神而非都来成为陈仲子。春秋战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充满杀君弑父、尔虞我诈的时代,孔子称之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所以他倡导克己复礼。他看到的更多是那个时代士人大夫乘乱而起的失德。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吕不韦、韩非、李斯、商鞅、张仪、苏秦等—大批这样的人物,相比之下,孔子、孟子、季札、陈仲子等精神坚守的人少得可怜。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孤独地抗拒乱世诱惑,进行精神的自我追求,象征意义是很强的。
此外,我看“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关于汲水自省、绝食三日的情节时,几乎怀疑作者抄写的是心学家刘宗周的事。刘宗周在《人谱》记警戒梦中写道:“尝夜入林园,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昼义心不明,以致此也。为之三日不飡。”时隔一千五百年,两个人的反应方式如此一致,这样的重复,实在使人不能不从精神原型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陈仲子》所以扰人,也是因为我们无法满足于这个故事的表层。陈仲子激动着我们内心深处,他已经超出作为历史人物的陈仲子,使我们联系到我们民族和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联系到我们的内心。他是无数同一经验在种族心理留下的沉淀物,他已经作为一种精神形象而具有种族意识、记忆的延续力。虽然他是陌生的,然而一看到他,我们就砰然心动,并且使人觉得这个题材,“其令人亲切的程度似乎在作家未使用之前它就具备了某种审美价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并镂刻在民族心灵中了”。陈仲子代表着一种精神原型,要命的还在于它本身几乎就是一个现成的现代寓言,表达着一种民族精神追求的主题在当代的变奏,并由此引起一种接受的急切性、诠释性。这样的人物容易溢出作者囿于自身的经验和理解,这样的题材也容易因其深刻的意蕴而挣脱剧作家立意对它的束缚。
这就是为什么剧作把陈仲子看成一个带喜剧性、讽刺性的唐.吉诃德式人物,而人们更多把他看成是浮士德式人物。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对当代精神原型及其特殊境遇的认识与理解。在浮士德中,精神原型是肯定性的,在唐.吉诃德中精神原型是以一种降格退化的形态出现,这当然有时代本身餍足骑士理想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在他身上表现的是变形、退化、掏空的骑士精神。他缺乏真正的精神能力,只余精神原型的外壳特征,悲剧因此变成喜剧性。这种情况在《海鸥》、《樱桃园》主角的讽刺性中也可以看到。或许陈仲子也正如此:天才转化为学究,激情堕落为迂执?但这要说服人,必须得到历史和现代的支持。春秋战国是百家争起的时代,急于用世是当时的主要精神特征。陈仲子之流既没有成为过时代的主角,也没有成为过时代精神的主流形态,从他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无法成熟地隐匿自身,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自身盲目的不自觉的正暗示着潜在发展的精神原型性人物。或者说他不过是被时代、种族的需要挑选出来显示时代、种族潜意识需要的症候式人物,如果不是挑选他,也一定要挑选类似的别人。因而他是肯定性的、悲剧性的。福克纳在悼念加谬时说:“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寻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找,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福克纳刻画的正是这类精神原型在当代境遇中的形象。而这也正是人们惜爱陈仲子的内在原因。因为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如此脆弱如此难找。现代的外部条件使这些不合时宜的精神追求者日益狼狈不堪、自惭形秽,现代精神原型因此带有自嘲性反讽性。他们是作为时代的“精神病症者”来彰显着时代本身的精神病症的。同样是一种夫子自道,加谬把西绪弗斯看成是伟大的精神长征者,从被迫中读出自觉;我们却从自觉中读出了被迫,将陈仲于看成是精神追求的迷失者。这便尽管是剧作家内心灼痛的冷静表达,我们却对此意犹未平的原因。或者是急不可待的渴想,使我们一下子不能体会作者冷静、客观的理性表达。
就这点说,陈仲子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正在于不为楚相去拯一方百姓于水火,否则作为相爷的陈仲子很可能早已灰飞烟灭,而作为人类荒谬的脆弱成员,作为时代的“精神病症者”,于陵的陈仲子至今仍有人忆起。陈仲子作为一种精神范式,表达着的是精神理想而不是实践理想。它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的普遍、完整实现,而在于永远彰显人类、历史、时代的非完整性。种族必须有这种超越精神的智慧和牵引,才能自我挽救、自我提升。
《陈仲子》饱含着对于时代的忧虑和关怀,倾注了作者的不安与无奈,更难得的是艺术上又是如此地宁静、圆润。就剧作完整地艺术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剧作是圆满自足的。不管对于陈仲于如何见仁见智,都无碍它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使人把玩、沉吟不已,久久不能释怀的作品,一个真正“古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