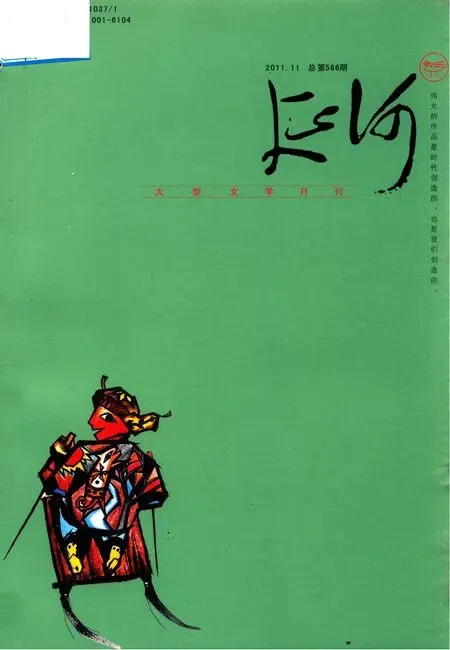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古炉》:民族秘史的别样书写
任 瑜
《古炉》是那种很难用某一理论话语进行阐释和解读的作品。它在陕西高塬的田野风景、民风民情和真实典型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回顾、展示“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轨迹,内容并不复杂深奥,但内涵却丰赡沉厚。贾平凹用以实写虚返璞归真的方式,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在古炉村这个具体的封闭空间内,建造出一个“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但这一意境所指向的时空刻度,远远超出一个狭小的陕西村庄,也超出“文革”那一段历史,而是将各种中国乡村,甚至整个中国都涵盖其中。要理解这样一部作品,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或许就是回到对小说文本的阅读和分析,从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最基本也是必不可少的层面进行感受和思考。
一
不得不承认,阅读《古炉》是需要勇气的,需要那种耐下性子去过琐碎纷乱、枯燥重复的磨人日子的勇气。只有具备这样破釜沉舟的勇气,才能静下心去读,才能渐渐潜入其中,及至摸清了头脑,理顺了脉络,熟悉了其间的人情世事,就会像过日子过出滋味来一般,读入了佳境,品味出许多细微的乐趣,不知不觉间就翻到了最后一页。
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古炉》的叙事模式所导致的,正是它的叙述结构和方式决定了这样的阅读效果。“叙述结构就像支撑起现代高层建筑物的主梁:你看不到它,但是它的确决定了这栋建筑的外形与特色。”(戴维•洛奇著,《小说的艺术》)《古炉》采用的并不是经典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和方式。首先,所有的故事不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而展开的,狗尿苔作为叙述视角之一,只是一个引线式的“主角”。作者让一群几乎同样亮度、同等重量级的人物蜂拥而出,霸槽、支书、天布、水皮,诸等角色形成一个个叙述的点,却不介绍人物和人物关系,也不评议人物,甚至几乎不着墨不琢磨人物的心理,更不去探索人物的意识,只停留在人物行为的表层。这样的叙述无法提供明确的背景细节和情绪感受来指引读者衡量角色,因而,面对扑面而来的各色人物,缺乏概念的读者需要一个逐渐熟悉的了解过程。
另一方面,《古炉》并没有描写一个紧凑的有清晰发展脉络的故事,而是将一个个的大小事件直接展开,小到吃喝拉撒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大到人命关天的历史事件,作者都一视同仁不分轻重,以一种“无动于衷”似的旁观姿态进行追踪展现,形成一个个叙述的面。其中没有引导和暗示之类的“著者介入”,也不提供简便现成的结构线索,作者好像仅仅是在事无巨细地客观记录,而不是想讲故事给读者听,其姿态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是展示。这种不“召唤”读者的叙事,让读者也成为和作者一样的旁观者,只能从外部观察到事件的进展,而不是从内部感同身受。读者被小说对事件心无旁骛的叙述牵着走,会忘却阅读中常有的对文本“虚构”的认知,简化阅读过程,不过,一头雾水的读者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掌握来龙去脉。
最考验读者的还是那种“过日子”式的写实手法。整部作品的叙述布满了对日常生活无比细致的展现。茶米油盐、吃喝拉撒、冬冷夏热,一个个细微琐碎的生活细节在作品中汇成一条几乎感觉不到流动的生活之流,而人的生老病死和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只是河流中泛起的几朵浪花,不曾激起动人心魄的波澜,也无法改变河流的沉寂黝黯。乍一看,人物是普普通通的,环境是往返重复单调粗陋的,似乎透着一种贫乏而麻木的无趣,而时间在这个简陋空间中的流动,又是如此之缓慢,仿佛是静止的,这样的文本氛围,确实需要强大的驱动力来推动阅读。
然而,在了解、适应它的叙述形式之后,《古炉》的精彩和魅力就显现出来了。那些平常的、朴素的日子,不再琐碎枯燥,而是渐渐变得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逼真得就像发生在眼前,或自己正活在其中。在看似呆板的空间和静止的时间中,那些小悲小喜、小仇小恨,那些善与丑,总之,那些普通又不寻常的人物、真实又不免荒诞的事件,就像静水下涌动的潜流,裹挟而来,创造出一种令人沉浸其中的氛围和魔力。联系到作者所说的写作深受中国传统美术的影响这一点,就会发现,这种写日常的写实非常像是细致的中国传统工笔画,虽然画面没有一个绝对的焦点和统一的聚焦,却有实实在在的颜色、细密清晰的线条,有素朴逼真的韵味和清明透彻的层次脉络,更重要的是,处处透出触目可感的“淋淋真气”。
《古炉》的叙述特色并不止于此。在细密精致的平实线条之中,还有着“大面积的团块渲染”。小说中闪现的人物事件的奇异和荒诞,以及采用的一些西方小说的经典手法,就是叙述中的大块写意,或者是作者所说的“西洋现代派美术的色彩”。比如人物当中的狗尿苔,他的异常之处不仅在于个头非常矮小却一直不长,还在于能听懂动物的语言,能和动植物交谈,可以闻到灾祸的气味。这不由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里的主人公奥斯卡,狗尿苔和他有着相似的特异之处,他们都是特殊岁月中的精怪人物,从黯淡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之中跳脱而出,带着异于常人的魔幻色彩。而《古炉》中最具荒诞色彩的事件,还是普通人的疯狂行为。他们突然跃出平凡日子里的柴米油盐,身不由己地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荒唐举动,于是,日常生活所勾画的井然有序的坚实线条,突然之间就被涂上了没次序不工整的胡摊乱堆的华丽颜色。《古炉》在平实的叙述中也采用了许多典型的象征手法,最突出的就是“疥疮”和“炉灰”这一对象征物的使用。“疥疮”象征“文革”带来的疯狂,霸槽在洛镇染上疥疮,传染给了全村人,用硫磺皂等都无法治愈,最后却意外地发现,只有炉灰能根治,“炉灰”就是古炉村的根基,象征着民族传统中积淀下来的那些品质,只有它们才能治愈“文革”的疯狂。这些人物、事件的表现方式和叙述手法上的中西交融,就像在中国工笔画中插入了西方现代派色彩,达到的叙述效果,正如作者所说,是“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
总的来说,《古炉》最突出的形式特色,就是将写实同写意相糅合,将微不足道的琐碎生活与异常的神奇事件相交织。整篇小说就如写意与工笔结合的图画,其中,真实的和荒诞的,平实的与华丽的,变动不居的和变幻莫测的,既纷繁复杂又脉络清晰、各得其所,阅读的驱动力和乐趣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古炉》的叙述语言。作者远远避开诗意的比喻、优雅的用字遣词,不管是对话还是描述,都采用带有方言色彩的大白话,简朴直白又生动到位。这正是《古炉》的风格所在,也是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的体现,“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简单朴素的文笔往往建立在扎实的写作功力之上,而这种文字风格同整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形态是相得益彰的,达到了叙述语言与叙事形式的高度统一。
二
在某个层面,一部小说的精神价值,更多地体现于它所关注所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写了什么。
就内容而言,《古炉》主要写的是“文革”,是一个乡村的日常生活形态在“文革”发生后的变与不变,作者意在从日常生活的行进中观察“文革”是“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怎样使“文革”之火“一点就燃”的。在小说中,“文革”这一特殊形态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舞台,台上同时上演着荒诞变幻的超验剧情和恒定不变的俗世生活,而它最终所展示出的,也并不仅仅是“文革”这一历史事件本身,还有着更多更宽泛更深刻的思索和内涵。
“文革”前的古炉村人处于典型的宗法制下的乡村生活状态中。千年来的中国乡村,宗族之间的利益纠纷、大姓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姓与小姓之间的对抗和联合似乎从无休止。在古炉村里,两大姓夜姓、朱姓和外姓小姓之间,也有着长期积累的恩怨纠葛和利益冲突。“文革”的发生似乎打破了宗法制下那些不言自明的规则,村人不再以姓氏来划分立场,而是以“革命”为名义组织起对立的派别队伍,但荒诞的是,派别的成立和划分,依然以姓氏为标准,姓氏决定立场的传统并无改变,“榔头队”是夜姓的,“红大刀”是朱姓的。表面上宗族间的矛盾已经转换成派别间的矛盾,但实质上派别的斗争仍然是宗族斗争的延续,“文革”只是为宗族斗争提供了新的名目和形式,披上了一件崭新的外衣,除了让斗争行为更荒诞更血腥更残酷外,丝毫没有改变斗争的目的和本质,掩盖在堂皇的外衣之下的,依然是对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和话语霸权的争夺。唯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文革”人人自危的高压下,原来的宗族纽带逐渐压缩为更紧密更可靠的血缘纽带,坚实的同盟关系缩小到了一个家庭内部。
为什么会这样争斗不休?因为病。如善人所说,古炉村的病人太多了。这些病,既有由贫乏穷困导致的落后、卑微、粗陋,也有人性中本就存在的残忍、自私、暴戾。人们身上潜伏着各种各样的病,每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了算计就有了不甘,于是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文革”发生之前,尽管也有妻不贤子不孝,但不管自觉还是被迫,大家基本都遵从支书所代表的权威话语和善人所代表的人伦道德。经由支书的权威压制和善人的伦理说解,争斗被控制在某些既定的规则之中,病症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缓解。而“文革”却将权威打到,将人伦颠覆,突然之间就打开了古炉村的潘多拉魔盒,释放了人们身上的魔鬼,于是潜伏的的病都爆发了出来,已发的病也更加恶化,人人都变得疯狂起来,在病魔的驱使之下,互相之间无情地揭发、恶毒地攻击,最终发展到残暴地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争斗终于没有了规则、失去了控制。
“文革”就是古炉村人共同患上的病,它就像人们身上的“疥疮”,让大家焦躁、难耐、狂暴,同时也经受苦痛,并且迅速地互相传染,几乎无人幸免。人人都是传染者,但又是被传染者,人人都有罪,又好像谁也没有责任,人人又皆是受害者。这种吊诡的情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丢钥匙事件,一家丢了钥匙之后,家家都开始丢钥匙,原来是每家丢钥匙后都去偷别家的钥匙,结果是每家都丢了钥匙,每家也都偷了钥匙。霸槽没能分到救济粮,追问起来,一个人牵出另一个,每个人都起了作用,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主要责任者。最惨痛的是,在席卷全村的“革命”斗争中,每个人都伤害了别人,每个人也都受到了伤害付出了代价。那么,这个难以找到罪魁祸首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呢?也许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似乎没有哪一个是该千刀万剐的责任人,但悲剧就这么神使鬼差地发生了,这就是古炉村人的“文革”的命运,也是中国人的“文革”的命运。不管拨开迷惘理清“文革”的理想具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古炉》至少实现了走进和走近“文革”、把握“文革”的企图,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并反思,“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之外,同时也有着魔鬼。”
当然,不管规则如何被颠覆,伦理如何被践踏,人性如何被扭曲,“文革”并没有也不可能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们身上总有一些特性是“文革”所不能改变的。浅层的如人的生存本能和生存智慧,世俗的生活终究是亘古不变的,不管革不革命、怎么样革命,人们最关心的,始终是过日子,是吃喝拉撒,是生存本质的问题,所以,不管是“榔头队”掌权还是“红大刀”占上风,都必须先解决“吃”的问题。同时,人的权欲心理也是一以贯之的,不管是谁掌握了话语权,都企图树立权威的象征,要像支书那样“威风”地穿衣走路,要刻新的象征权力的石狮子。最为重要也最让人欣慰的是,相伴于本能和欲望的传承,传统文化和人伦道德也同样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并未被生存状态的变化和人事的扭曲变形所摧毁,所以善人在焚身之后还能给大家留下一颗良善之心。善人婆、狗尿苔、杏开等人身上所有的善良、坚强、淳朴、包容、宽厚、仁义,这些可以被归结为人性中善和美的东西,就像激流下的深水,在“文革”的变幻和喧嚣之中积淀下来,对这个爆发了恶的年代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始终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观察,对各色人物、大小事件包括“文革”,进行不动声色不涉入其中的客观记述,所以,《古炉》中没有形于色的人性拷问和道德评判,展示的是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悬置不意味着道德的缺席,这种将道德审判悬置的“道德”是一种境界更高更宏大的道德,源自作者将人当作“自治的个体”而不是善恶样板、规律代表或真理化身的清醒认识,反而更能表明作者对人物爱恨交加的深切情感以及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包容,“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作者对古炉村人、对自己族类的书写清醒而客观,悬置了道德评判却保持了大悲悯的情怀。更重要的是,悬置也不意味着作者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虽然整部作品没有明确的批判和控诉,但是通过“文革”对古炉村民人性的“改造”,呈现出了“文革”的真实面貌,让读者自己进行思考和评判。
归根到底,写“文革”,写生活,写伦理,都是在写人。在《古炉》中,“文革”就像作者手中的一盏聚光灯,照在古炉村的病人身上,让他们从里到外纤毫毕现,一举一动无所遁形。实际上,这束灯光所照的,不仅仅是古炉村的病人,也是中国的病人,由他们到我们,由一个村庄到一个民族。巴尔扎克将小说看作一个民族的秘史,《古炉》不仅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一段民族的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