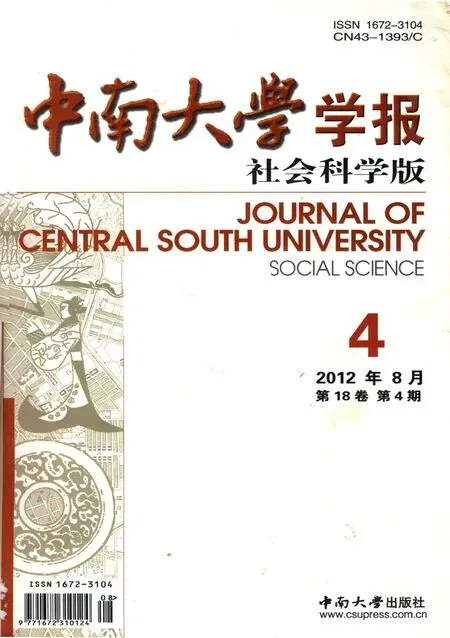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梁漱溟的伦理内涵探析
廖济忠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410083)
如同“正义”总在“争议”之中一样,“伦理”也总在“论理”之中。笔者无意把关于伦理的许多不同的意义列举出来加以品评,但在研究梁漱溟的伦理思想时,有必要弄清楚他在使用这一名词时所赋予的意义。梁漱溟从传统中国的生活实际与社会结构尤其是从它的特殊性出发,几乎言必称伦理或伦理情谊。相对于其著述中诸多模糊、笼统和粗糙的概念来说,他对伦理概念的界说要清晰、流畅许多。
如果说,西洋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的是其个人主义和权利观念,那么,中国最大的存在则为伦理,中国传统文化就植根于伦理情谊之中,且抽象的伦理情谊实寄于具体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对伦理概念的述介与其说是学问家的严格定义,毋宁说是思想家对这种存在情有独钟地挖掘、渲染与展示。
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虽然并未直接对伦理概念给出解释,但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他整个伦理思想的文化基调和理论基础。
在 193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梁漱溟对伦理概念给出如下解释:“伦理者,盖示人之人生必为关系的。……人生实存于此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乃天然基本关系。故所谓伦理者,要以家庭伦理——天伦——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1](86)
在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对伦理概念给出如下解释:“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互关系中。……既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2](168)
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对伦理概念给出如下解释:“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3](81−82)
在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对伦理概念给出如下解释:“伦者,伦偶。即谓在生活中彼此相关系之两方,不论其为长时相处者抑为一时相遭遇者,在此相关系生活中,人对人的情理是谓伦理。其理如何?即彼此互相照顾是已。更申言以明之,即理应彼此互以对方为重,莫为自己方便而忽视了对方。……举凡这轻重不等种种顾及对方的心情,统称之曰伦理情谊。情谊亦云情义,义是义务。人在社会中能尽其各种伦理上的义务,斯于社会贡献莫大焉,斯即为道德。”[3](738)
上述按出版时间顺序所列的五部著作是梁漱溟一生主流思想的集中体现,伦理无疑是其中的“航标性”话题。若要比较准确地理解梁漱溟所谓伦理的内涵,应特别注意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一、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这一判断中包含密切相联的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伦理首重家庭。“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申出伦理之‘理’,没有这样的‘伦’,‘理’只能是缺乏现实性的抽象”。[4](34)众所周知,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梁漱溟认为,孑然一身的男人或女人只能算半个人,必两性关系成立方为全整人生的造端。父母总是最先有的,继之以有兄弟姊妹。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开展,则又有夫妇子女,宗族戚党由此而生,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说不尽的关系也接锺而至。在中国传统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项同属于家庭伦次。家人父子是天然的基本关系,家庭伦理被尊之为天伦。如果说“家”只是一种现实的组织形式,那么“亲”则是使这种形式获得神圣地位的内容。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人生的美满,就在于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所谓人生的不幸,就在于疾苦穷难不得就所亲而诉之,例如鳏寡孤独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被称之为“无告。”因而可以说,“家为中国人生活之源泉,又为其归宿地。人生极难安稳得住,有家维系之乃安。人生恒乐不抵苦,有家其情斯畅乃乐。‘家’之于中国人,慰安而勖勉之,其相当于宗教矣”。[1](86)
“五伦说”由孟子提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132)五伦的设定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制度中的坐实,标示着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人伦设定原则已然确立。与西化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漱溟不是“撕下”而是“紧捂”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往情深地为世人雕琢了一幅暖风熏人醉的家庭生活图景。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这种把人伦设定于家庭血缘基础之上的传统伦理,“一方面,使得人伦关系与伦理生活具有了最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伦理具有了与西方宗教伦理相类似的神圣的性质。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结合,使中国伦理具有无以匹敌的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4](36)
另一层意思是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它各方面。或者说是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也就是依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梁漱溟曾引严几道先生所译孟德斯鸠《法意》中的有关论述以说明中国所以立国者何在。“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也。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于所生表其年德者,皆将为孝敬之所存,——则长年也、主人也、官长也、君上也,且从此而有报施之义焉。……伦理、礼经,而支那所以立国者胥在此。”[2](256)“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此见正与梁漱溟所见略同。他还进一步指出,缺乏集团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以伦理组织社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融了个体与团体的关系,而把社会上一切关系都伦理化——亦即把骨肉之情推而及于社会上一切有关系的人——是中国人一向的风气。例如“称县长为父母官,称民为子民,称老师为师父,称学生为徒弟……乃至朋友的关系,东伙的关系,一切关系都把它伦理化。这就是想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都拉得更近一些,这就是重情义,讲亲爱的意思”。[1](855)
缺乏集团生活与欹重家庭生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而非两件事情。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家庭几成虚位,而中国人所有的只是家庭和准家庭关系,只是父子兄弟和准父子(君臣、官民、师徒等)、准兄弟(朋友等)。伦理关系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近则身家,远则天下,从己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俨然已成一条无障碍通道。于是,“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2](175)总之,“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1](587)费孝通曾以“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来说明中西社会人和人关系格局的不同,且形象地喻之为“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和“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由此,他对伦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6](25−27)这种说明和解释与梁漱溟的阐述是相同或相近的。
二、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
这一判断中也包含密切相联的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关系本位。所谓本位就是重点,所谓关系本位,就是以关系为重点。如何在人际中去定位一个人的方法无非两种:一种是由自我去定义人际关系;另一种是由人际关系来定义自我。中国传统社会通行的定义方法无疑属于后者。仁者人也,而且是二人之谓,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之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才能成全这个二人之间的所谓仁。梁漱溟曾戏称西洋人生为“单式的”,中国人生为“复式的。”前者先则以每个人直接宗教,后则以每个人直接国家,其中无非是团体与个人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而中国人“伦理复式的人生”处处发生的皆是对人的问题,“如何处夫妇、如何处父母子女,如何处兄弟乃至堂兄弟,如何处婆媳妯娌姑嫂,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乃至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徒东家伙伴一切朋友,……如是种种”。[1](87)也许李泽厚先生对这一层意思点得更透,“我是谁?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妇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是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性、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他(她)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于是,父有‘为父之道’,子有‘为子之道’,此即‘道在伦常日用之中’”。[7](316)从伦理社会的整个精神来看,伦理关系一经有了,便不许再离。根据梁漱溟的论述,其中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主观上不忍离。就是自己在情感上伤痛不忍。二是社会上有督责。伦理蔚成礼俗,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即便有说不尽的委屈,也只能忍受。三是生活上过不去。彼此相依之势已经造成,一个人的生活与周围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伦理关系一旦离绝,此人在现实中就无法生活下去。
美国学者尼斯贝特在《思维的版图:西方人见木,东方人见森》一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实验,心理测验者让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分别是鸡、牛、青草,并要求将其分为两类。结果,大部分中国儿童把牛和青草分为一类,把鸡分到另一类;而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鸡归为一类,而把青草分为另外一类。这个实验结果体现了东西方儿童思维方式的差异:前者首先看到的是关系,其次才有被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实体。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视为同一个类别。后者则首先看到了实体,然后构建起实体间的关系。按照“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青草是植物。类似的实验结果还表明,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足以延续到成年时期。[8](21)正是基于关系的重要及其背后渠道化的“关系式”,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情理是随人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说话要看谁说,不能离开说话的人而有一句话。此即所谓相对论”。[3](741)“标准是随人的,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此即所谓相对论”。[3](95)在与不同个人的对应关系中,由于自身所处地位或所扮角色不同,于是其伦中之理也相应而异。人际关系虽然复杂万端,但万变之中不变者是种种关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统统是“此一人对彼一人”的关系或简称“一对一”的关系。
另一层意思是向里用力。也就是互以对方为重。梁漱溟认为向里用力是中国式人生的最大特点,所有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之类的传统教训,都是以社会构造的事实作背景而演成的。从历史传统来看,梁漱溟区分了封建社会关系与伦理关系的不同,前者是“呆定的”,例如日本武士为忠义的忠义;而后者“准乎情理而定”,例如中国人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突出体现后者精义的儒家经典论述当属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5](195)封建的君臣关系,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道德平等的色彩。儒家理论原本如此,在儒家理论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现实也大致如是。就孟子的论述分析,伦理关系包含互动对应的两个方面,积极的一面是你仁我义,消极的一面是你不仁我不义。梁漱溟在传统儒家理论基础上格外置重的是其积极的一面,更准确地说,是立足自己这一面。从我做起,做我应该做的。我仁我义,不是“行仁义”,而是“由仁义行”(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合乎责任”[9](14))。对自己而言就是向里用力,对他人而言就是尊重对方。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人人向里用力就是互以对方为重,“极而言之,伦理的意思,是要牺牲自己去为对方”。[1](854)例如,何谓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什么是最好的父母?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为子女着想的就是最好的父母。什么是最好的子女?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孝顺父母的就是最好的子女。“推而言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姊妹,乃至夫妇、朋友,社会上一切相关系的人,彼此都要有牺牲自己、为对方着想的精神,都要互以对方为重”。[1](854)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唯有向里用力。无论是农工商人还是读书人乃至高高在上的皇帝,各色人等都要向里用力。正如古书所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等等。而当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不好的状况时,解决的办法仍然只有向里用力。
“例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倍加小心,倍加殷勤,莫问它结果如何,唯知在我尽孝。此即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者,外此更无他道。反之,若两眼唯知向外看父母的不是,或一味向父母顶撞,必致愈弄愈僵,只有恶化,不能好转。其它各伦理关系,要亦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其所求者,却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合,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3](195)后起新儒家唐君毅所提出的“自我寻找论”深得梁漱溟“向里用力”论的个中真味。所谓“自我寻找”的主要内涵有三:一是在一切伦理关系中,吾人的主动是第一位的;二是吾人的道德修养无须他人的赞美;三是吾人的道德原则、理想与价值,均可由自省获得。[10](165)
从中西社会的对比来看,梁漱溟认为中西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就在于讲权利义务的出发点恰好相反,西方人是从自己出发,而中国人是从对方出发。“权利”一词的本义是正当合理,中西两方对权利本义的理解并无不合,但对现实权利的要求却根本相异。在西方社会,权利“不是出于对方之认许,或第三方面一般公认,而是由自己说出”。[3](93)以子女享受父母的教养供给为例,如果子女对父母说“这是我的权利”,“你应该养活我,你要给我相当教育费”——这便是西方式的权利。如果父母对子女说“我应当养活你们到长大”,“我应给你们相当教育费”——这才是中国式的权利。梁漱溟强调伦理关系是顶清楚顶明显的义务关系,但中国人所说的义务和西方人所说的义务万不可混为一谈,中国人的所谓义务是道德上的义务,它是从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硬向我要的,因而是“软性”的。西方人的义务是法律上的义务,如果说我有这种权利,就等于说对方于我有这种义务,因而是“硬性的”。总之,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思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伦理精神的“中国味道”应当说“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2](294)简言之就是:权利不从自己说,义务不从对方说。更直截地说:只许有义务观念,不许有权利观念。中国式的权利义务观是向里用力精神的必然产物,似乎“中国人做什么都必须说成是为了别人才有合法性”。[11](59)
三、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
只要涉及中国现代伦理的建设问题,各家各派都无法避免对传统五伦地位与价值的反思。贺自昭曾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2]一文中指出:从本质上考察,五伦观念实际包含四层要义:一是特别注重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十分注重人与神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永久关系;三是以等差之爱为本而善推之;四是以常德为准而竭尽片面之爱或片面的义务。不论其中所含褒贬成分的多少,毕竟历史的潮流已向现代涌进,传统的五伦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现代伦理的实际需要。例如,谭嗣同曾在《仁学》中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蔀,如地狱矣,……夫惟朋友之伦独尊,然后彼四伦不废自废。”[13](113−114)因为君臣、父子、夫妇三伦违背了自由平等、不失自主之权的原则,因而他主张五伦之中只可保留朋友一伦。除与朋友之道相近的兄弟之伦外,其余三伦都必须废除。如果说谭嗣同是在基本反对的态度下对传统五伦实行了“减法”,那么梁漱溟则在基本赞成的态度下对传统五伦实行了“加法”或“替换法”,“因为以前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之伦,而缺乏团体与个人之一伦,所以现在可以加多一伦,成为六个,或者把君臣之伦,改成团体和分子”。[1](795)
在与西方社会的对比中,梁漱溟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缺欠: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技术。相较而言,团体组织的缺欠更为关键,“旧日伦理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的关系,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必如此,乃为善于取长补短”。[14](300)根据“是关系,皆是伦理”的基本观点,现在人对人的关系就应当包含个人对集体、集体对个人那种相互关系在内,也包含集体对集体的关系在内。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如何处理“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也就是团体与个人之间如何求得均衡之道,同样要贯彻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的精神。“我是团体中的一分子,我应以团体为重,而团体对我,也应以我为重。或者说:在团体立场,不要以团体为重,应以个人为重;而在个人立场,应当尊重团体,并且互相尊重个人。这样一来,结果自然能平衡”。[1](794)梁漱溟自认为他提出的这个伦理——第六伦——比以前的伦理要进步。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第六伦说”作过更充分的发挥和更深入的探讨,例如台湾的李国鼎先生曾把第六伦定义为“个人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也就是从前所说的群己关系”。[15](183)尽管梁漱溟对第六伦的直接论述不多,但率先提出第六伦,无疑是他对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
四、小结
综上可以看出,梁漱溟对伦理概念内涵的界说是老树发新芽式的。一方面,继承传统伦理意蕴并注入自己的理想成份;另一方面,适应时代发展为传统伦理增添新的要素。简括言之,梁漱溟的所谓伦理,就是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或者说,就是在与人相关系之中,互以对方为重。这种关系与情谊同样适用于第六伦即团体与个人之间。
梁漱溟伦理概念的根本内涵及其价值趋向就在于: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以伦理组织社会就是要把社会家庭化,而堪称其灵魂的伦理情谊则发端于家庭、培养于家庭。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家庭美德仍然是人生幸福的不竭源泉和社会秩序的有力屏障。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梁漱溟那里,从家庭通向社会,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却要求把家庭与社会“断开。”社会是公共生活的场所,而家庭则为私人生活的场所,私人生活场所的道德要求并不适用于公共生活,因为公共生活的私人化倾向或社会关系的“二人化”所导致的结果更为常见的是私德对公德的严重败坏、私利对公利的肆意侵蚀。
家庭和社会同为人生的来栖之地,没有理由以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的名义牺牲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也没有理由以现代社会伦理价值的名义牺牲传统家庭的伦理价值。家庭相对容易成为人生的宜居之地,而社会确乎甚难成为人生的宜居之地,因而后者的培育与生长显得更为急切。家庭伦理生活的价值显然被梁漱溟无限放大了,无论他所描绘的家庭伦理生活图景多么迷人,我们也只能在严格分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的情况下认取其家庭伦理中美妙而有限的价值。
[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4]樊浩.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J]. 学术研究, 1998(1): 34−40.
[5]王缁尘. 四书读本·下册[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6.
[6]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8]曲学丽. 西方人见木. 东方人见森[J]. 读者, 2009(5): 21−22.
[9]依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0]唐君毅. 中国人的心灵[M]. 上海: 联经出版公司, 1984.
[11]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贺麟. 文化与人生[M]. 台北: 地平线出版社, 1973.
[13]张岱年.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4]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七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韦政通. 伦理思想的新突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