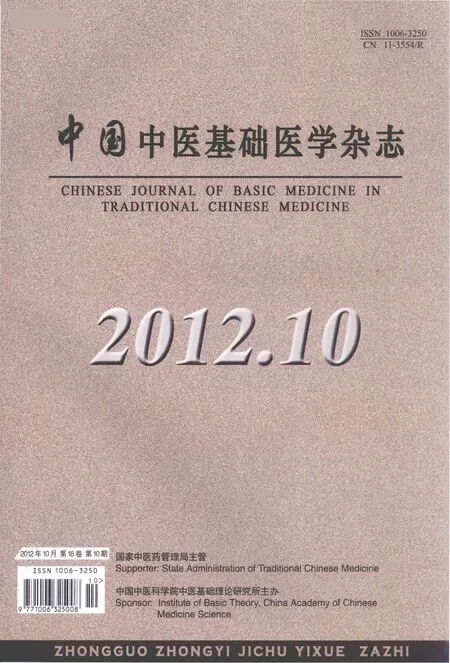针药同效相须关系临证验案
韩 彬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北京 100700)
针灸与中药的作用性质和作用环节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最终的临床效果却可能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例如,艾灸百会穴可以起到益气升提的作用,而补中益气汤也被认为具有相似的临床功效。虽然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二者在实现这一疗效过程中的机制,但其机制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临床实践中,有时需要利用针灸和中药功效相同而其内在机制有所差异的现象,同时运用针灸和中药疗法以达到相同的治疗目的,此时针灸和中药的关系可称为同效相须关系[1]。针药同效相须的治疗,一般多用于以下情况:一是单独针灸或中药治疗其功效有所不及,须同时使用针药并用的方式,利用二者功效相似或者相同来加强功效达到治疗目的;二是通过简单的增加药物剂量或增加针灸的刺激量已经不能获得相应疗效的场合。笔者在临床实践中,以上述治疗思想为指导治疗多种病例,获得较好效果,以下列举4个病例加以阐述。
1 针药并用温补脾肾治疗泄泻
案1:埃瑞克,男,46岁,2011年5月19日初诊。主诉慢性腹泻、反复发作脓血便25年。患者自25年前开始出现腹泻、腹痛,渐致下痢脓血、畏寒、手足不温,在法国医院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西药治疗效果不显,病情渐进性加重。严重时每日排便20次以上,便中可见大量黏液脓血。5年前患者到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工作学习,用中医中药治疗顽疾。诸医皆诊断为脾肾阳虚,应用的方剂为多为四神丸、参苓白术散、金匮肾气丸类。服药略有疗效,便次有所减少,继续服用则疗效减弱。刻下症:腹泻每日10次以上,便中夹有黏液脓血,脐周脐下冷痛,腹部喜温喜按,畏寒,多着衣被,手足不温,腰膝冷痛,阳痿,阴部湿冷。舌淡胖、脉沉细弱,诊断为泄泻(溃疡性结肠炎),辨证属脾肾阳虚证。治疗以四神丸合参苓白术散加减以温补脾肾:制附子9g,补骨脂10g,吴茱萸 5g,肉豆蔻 5g,五味子 5g,生晒参 5g,茯苓12g,白术 10g,芡实 10g,山药 20g,莲子 10g,木香5g,砂仁5g,珍珠粉0.9g(冲服),5剂水煎服,每日1剂。二诊:服上剂后便次减少至每日7~8次,腹痛腹冷症状减轻,微觉口干咽痛,口渴欲饮。考虑为温补之药助阳,效不更方,原方附子加至12g,再入5剂。三诊:服后便次减至每日3~5次,但口干咽痛症状加重,烦躁,舌红。附子减至5g,吴茱萸减至3g,再入5剂。同时加入针灸治疗,艾条温和灸法灸神阙穴,温针灸肾俞(双)、关元、天枢(双)、命门、足三里(双),每周3次,10次为1个疗程。四诊:按上述治疗方案治疗1个月后,便次减至每日1~2次,脓血便消失,且口干咽燥、舌红心烦等症未见。停止汤药、针灸治疗,嘱其继续每日分3次服用珍珠粉0.9g(冲服)及参苓白术丸1个月巩固疗效。1年后随访诸症平稳,体力恢复,体重增加5kg。
按:张介宾谓:“泄泻之本,无不由脾胃。”又云:“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阴气盛极之时,则令人洞泄不止也”[2],提示腹泻的发生与脾肾密切相关。本例患者本于脾肾阳虚、统摄失职、通调失畅而致,治宜温补脾肾,助阳益气。考本例患者的病史,前医辨证无误,论治亦合于法度,其不效或不能持久有效者,皆在于方中温补之药的运用不得法。用量小药味少则力有不逮,用量大药味繁复则助阳生火而耗伤阴津。而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外治法治疗脾虚泄泻疗效确切,如针灸天枢穴提高肠道局部免疫,可以有效保护肠道黏膜的完整性,对治疗脾虚导致的泄泻具有重要意义[3]。但临床观察亦表明,针灸治疗的即时疗效好而其疗效难以持续。本例以灸神阙穴、命门、肾俞等以助肾阳,针灸关元、天枢、足三里等穴既温补脾阳又健运脾胃之气。药物得针灸之功则气味可以彰显,针灸得药物之力则效能可以流转。因针灸的应用减少了药物的用量,而又因药物的存在延长了针灸的作用,针药并用,功效合一,二者相得益彰。
2 针药并用滋阴清热治疗滑胎及月经后期
案2:张某,女,35岁,2011年 3月 1日初诊。主诉滑胎2年、流产后月经后期6个月。月经初潮11岁,月经周期 28d~30d,经期 3d~5d,经量适中有血块,末次月经2011年2月初。结婚4年,2次孕8~9周时自然流产,2010年8月孕9周时第3次流产,流产后月经周期45d~50d,带经期 2d~3d。在北京某医院检查诊断为黄体功能不全。本次因习惯性流产、月经后期而来就诊。刻下症:月经后期、量少,色鲜红,潮热盗汗,手足心热,口渴喜冷饮,心烦,失眠多梦,颧红消瘦,时有胃痛,嘈杂反酸,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脉细涩、舌红少津苔少,诊断为滑胎(习惯性流产)、月经后期,辨证属肾阴不足。因病人久服中药不效,加之脾胃素弱,所以拒绝服用中药而选择针灸治疗。针刺以滋肾养阴、和血清热为主。穴位处方:太溪(双)、志室(双)、复溜(双)、归来(双)、三阴交(双)、血海(双)、次髎(双),针用泻法,留针20min,每周3次,10次为1个疗程。二诊:针刺6次后患者自觉症状好转,月经应时而至,经量尚少。继续针刺治疗方案如前。三诊:针刺10次后多症状好转,胃痛反酸等症状消失,惟觉五心烦热症状减而未愈,偶发盗汗。针刺治疗方案同前,同时配合中药汤以加强疗效,方以清骨滋肾汤[2]加减剂:地骨皮 20g,牡丹皮 10g,麦冬 10g,玄参 15g,沙参15g,炒白术 15g,炙五味子 6g,石斛 10g,青蒿 6g,鳖甲15g,5剂,每日1剂,水煎服。四诊:共计服药10剂,针刺20次后诸症消失,月经按时而来,周期正常,建议停止治疗待孕。在针药并用调理之后,患者于2011年6月末停经,经化验证实受孕。2011年11月电话随访,患者孕期5个月,孕检胎儿发育正常。
按:中医认为本病多与禀赋不足、体质虚弱或劳伤太过,或饮食失养、情志所伤有关。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主生殖,直接为胎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肾主系胞,与任脉交会于“关元”,与冲脉下行者相并而行,超过冲任二脉与胞宫间接相连。由于屡次堕胎伤肾更甚,肾阴不足使经血亏少、冲任血虚、胞脉失养而致滑胎。正如《傅青主女科》所言:“妇人有骨蒸夜热,遍体火焦,口干舌燥,咳嗽吐沬,难于生子者,人以为阴虚火动也,谁知是骨髓内热乎,夫寒阴之地,固不生物,而干旱之田,岂能长养?[4]”本例患者因久服中药不效,故只能先给予针刺,选太溪、志室、复溜、三阴交、血海等滋补阴血、清泻虚热的穴位治疗。症状减轻说明针刺穴位处方方证契合,疾病未愈说明针刺效力有所不及。清骨滋肾汤原方[4]地骨皮用至30g以上方可,同时按照原方说明,需“连服三十剂而骨热解,再服六十剂自受孕”。本例针刺合用清骨滋肾汤加减方,针刺及药物滋阴泻火之力相合,功效相得益彰,减少了药物用量的同时,缩短了总的服药时间,说明针灸和中药在功效相同或相近时,其临床疗效可以呈现叠加的趋势。
3 针药并用调和阴阳,镇静安神治疗惊悸
案3:周某,女,71岁,2011年11月14日初诊。主诉心悸、易惊3个月。现病史:患者平素体虚,思虑重重,善惊易恐,心胆虚怯。自亲人去世后,思虑过重,每每难以入眠。渐至心悸不安,易惊恐,每遇突发声音或意外事件则心率加快,甚至突然晕厥、瘫倒在地。恐惧黑暗,睡眠时亦不能关灯。在其他医院诊断为心脏神经官能症、焦虑症等。服用中西药无效,转来本院以期以针灸治疗。刻下症:惊恐不安,受惊则全身颤动,甚则瘫倒汗出、反应略显迟钝,紧张面容,时时头痛,神疲体倦、头晕,心悸失眠健忘,腰膝酸软。脉沉细弱无结代、舌淡苔白腻,诊断为惊悸(阴阳失和、心肾不交),治宜调和阴阳、镇静安神。针刺穴位处方:劳宫、神门、太溪、涌泉、关元、命门、百会、水沟,针用平补平泻法,每周2或3次,10次为1个疗程。二诊:针刺治疗10次后,惊悸、失眠等有所好转,但仍感虚弱胆怯,每每惊恐。考虑只用针刺治疗其效力不足,故配合中药治疗,处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减:生龙骨30g(先煎),生牡蛎30g(先煎),桂枝 12g,白芍15g,炙甘草 10g,大枣6g,远志 10g,石菖蒲 12g,郁金 10g,合欢皮 10g,5剂,每日1剂,嘱另加生姜5g水煎服。三诊:上述针灸治疗20次服药15剂后,恰逢春节烟花爆竹之声彻夜不停,虽时时惊悸,不胜其扰,但症状已经可控,受惊吓后已不至于瘫软晕倒。效不更方,按照上述治疗方案继续。四诊:元宵节后来诊,自诉症状消失,睡眠好转。虽节日烟花爆竹之声未停,但身心未受任何影响,惟仍感心悸乏力。嘱服人参归脾丸善后。
按:惊悸病名源自《内经》,系统论述惊悸病辨证施治,出自《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医学正传》曰:“怔忡者,心中惕惕然动摇而不得安静,无时而作者是也;惊悸者,蓦然而跳跃惊动,而有欲厥之状,有时而作者是也。[5]”后世总结惊悸病因病机,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其本为阴阳亏损、气血不足,标为气滞、血瘀、痰浊、水饮等。本例患者平素思虑惊恐,日久导致心肾阴阳失调,神不守舍,则惊恐不安之状更甚;阳不入阴则失眠,肾不足则腰膝酸软。脑为髓之海,髓脑不充而健忘,舌淡苔薄白、脉细弱乃气血不足之象。《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故用劳宫、神门、太溪、涌泉交通心肾,命门、关元调理任督以安阴阳,百会、水沟以镇静安神。针虽有效,但终因患病日久、积重难返,故配合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加减以调和阴阳、潜镇摄纳、交通心肾。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系桂枝汤原方加龙骨牡蛎组成,方中桂枝配白芍,桂枝辛甘化阳,白芍酸甘化阴,二药相合有阴阳合化之用,故该类方剂或治表或治里,治疗机理均为调和营卫、燮理阴阳。本方用龙、牡也是取其重镇摄纳之功,以冀取得潜阳入阴之效,可收摄浮阳,主精神不宁,正气浮越。本例以针药并用治疗,针药并用,功效合一,二者相得益彰,收到较好疗效。
4 针药并用益气养阴安神治疗内伤发热
案4:艾杰尼,男,35岁,2011年3月2日初诊。主诉低热、精神不振3年。现病史:病人平素性格内向,精神抑郁、精神疲惫,但工作劳累,压力较大。近1年来下午体温升高至37.1℃ ~37.5℃。工作能力下降,时时失眠,常述乏力,动则尤甚。患者于1年前在莫斯科某医院诊断为功能性发热、神经衰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症。服用西药(药名及品类不详)治疗,疗效不显,故专程来中国求医。刻下症:精神抑郁,常述乏力,精神疲惫,无故忧伤,情绪不宁,纳食尚可,心悸健忘,失眠多梦,每夜醒三四次,五心烦热,盗汗,口咽干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舌色绛红,晨起有极少量薄白苔,下午则完全光红无苔,脉弦细有力,诊断为内伤发热(气阴两虚证)。治疗拟针药并用。以中药汤滋阴清热、益气安神,方用青蒿鳖甲汤加减:青蒿6g,炙鳖甲15g,生地黄30g,知母 10g,牡丹皮 10g,枸杞子 15g,麦冬 10g,天冬10g,女贞子12g,旱莲草12g,丹参30g,西洋参 3g另煎兑服,10剂水煎服。针刺以滋补肾阴、清心安神。针灸处方:百会、太溪(双)、神门(双)、涌泉(双)、劳宫(双)、关元、气海、足三里(双)、阴陵泉(双)、脾俞(双),针用补法,留针30min。每周3次,10次为1个疗程。二诊至四诊:上述治疗后体力渐复,精神好转,无倦怠乏力,虽在京旅游活动较多但仍感体力尚可。睡眠好转偶尔醒来,尤其是舌红绛减轻、舌苔渐复。以此为基本方加减服用30剂,针灸治疗1个月。五诊:诸症消失,睡眠正常。判定为临床治愈。嘱带药回国,待其舌色红绛时煎服三五剂以巩固疗效。2011年7月病人来京度假旅游时来院探访,得知其诸症未发,精力充沛,睡眠时间及质量均好,体力与常人无异。综合考量可判断为临床治愈。
按:本例患者乃系劳心过度、耗伤肾阴、日久虚火上炎、伤津耗气、营血亦为火热之邪灼伤所致。故病人表现为阴虚火旺之证,同时又有气虚。故取青蒿鳖甲汤滋肾养阴,清解内热,阴液足则热可伏;更加用补气养阴生津,丹参以除烦安神,全方以青蒿鳖甲汤滋阴清热为本,滋阴透表并进,亦即标本兼顾之法。而针灸之法,以太溪涌泉补肾阴清热,神门补心阴心气,劳宫清心安神,百会镇静。合以关元气海脾俞三里等穴补气。针药法度一致,作用方向相同,其功效合二为一。
小结:针灸和中药的临床运用是建立在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辨证论治也是针药并用的理论核心。在临床实践中,针灸和中药的运用有各种不同的配合形式,如针药异效互补[6],但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利用针灸和中药功效上的一致性,即针药的同效相须关系,对同一个证候、同一种疾病或同一个症状进行治疗。而在这些实践中,观察研究针灸或中药在针药并用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则成为临床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有助于回答针药并用的治疗能否产生较单独的中药治疗或针灸治疗更好的疗效这一涉及针药并用地位的关键问题。在针药并用的过程中,利用二者的协同关系,在保证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通过针灸的使用,减少药物用量,缩短用药时间,进而减少药物的在整个疗程中的总用量。临床对于特定患者及疾病状态,可以考虑选择适当的方式针药并用,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
[1]韩彬.论中医针药并用过程中针灸和中药的关系[J].中医杂志,2012,53(15):1273-1276.
[2]明·张介宾.景岳全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539.
[3]逄紫千,王富春,严兴科.针灸天枢穴对脾虚泄泻大鼠免疫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J].江苏中医药,2005,26(4):27-28.
[4]清·傅山.傅青主女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38-39.
[5]明·虞抟.医学正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274.
[6]韩彬.针药异效互补关系临证应用体会[J].中医杂志,2012,53(17):1507-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