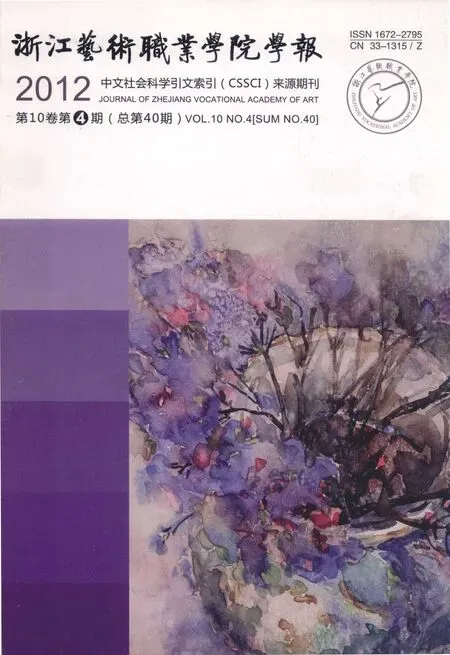两对有情人的不同命运——谈杨小青导演的越剧《西厢记》和《陆游与唐琬》
薛若琳
《西厢记》是一部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古典名著,自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编撰的杂剧《西厢记》问世后,历代演出一直很活跃。传奇兴盛后,又有明代李日华据“王西厢”改编的“南西厢”传播更为广泛。我认为这出戏的艺术生命力之所以如此久长,与它提炼了一个审美强烈、符合人心的主题:“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密切相关的。茅威涛在《张珙是谁》的文章中谈到,在张生的身上,充满多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爱情,来自婚姻,来自事业,来自人性”,这样的“压力”,则“接通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两个终端”。茅威涛认为,古人和今人,都会遇到“压力”,但张生能够克服困难,变压力为动力,她说:“张珙的胜利,是现代人的骄傲。”这话讲得很精彩。可见,张生碰到的“压力”,今人也有,但在“压力”面前,是退缩动摇,还是坚强面对,是该剧对今天观众的心灵撞击和有益的思考。杨导说,她要“排演一部适应当代观众审美需求的《西厢记》,赋予这部古典名剧现代美”。杨导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她要让张生这个距今一千多年的古代青年的所作所为,具有比较深刻的普世价值。
《西厢记》这部名著,以莺莺为主人公者居多,后来有的戏又以红娘为主人公,台湾的话剧也有以孙飞虎为主人公者。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改编演出的《西厢记》,则以张生为主人公。摆在杨导面前的选择是:她是按前辈艺术家的传统演出复排呢,还是闯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杨导选择了难度较大的后者。首先,杨导要确定立意。过去强调反封建的主题,当然不错,但现实感已经不强了,杨导把主题定位为:“对美好憧憬的执着追求和追求过程中的艰辛、曲折、磨难。这样,故事还是爱情故事,但内涵更丰富了。”其次是人物,明确该剧以张生为一号人物。杨导说,要“强化他们形象,更能体现积极追求自由的精神和青春的活力”。三是确定舞台体现。主要是使舞台有限的构建时空转为人物无限的心理时空,因此,杨导与舞美设计专家一起,决定使用“转台”,两人刚见面便擦出感情的火花。杨导根据此时人物的心理特征,便把舞台切成四块:第一块是张生游普救寺的大殿外;第二块是张生与莺莺不期而遇的过道;第三块是张生与莺莺在做佛事的大殿;第四块是佛事散去,张生跟追莺莺,莺莺顾盼的大殿一角。杨导通过这四个板块的处理,意在充分渲染《惊艳》是全剧男女两个人物将来命运的起点和指向。又如《赖婚》一场,是矛盾激化的焦点,杨导把时空切成三块:第一块是张生的书斋,他自以为好事将临,于是手舞足蹈,喜不自持;第二块是莺莺的闺房,她娇羞的对镜理云鬓,等待母亲宣布佳期;第三块是老夫人的厅堂,在这里她严肃的告知张生和莺莺,今后只能以兄妹相称。这样的舞台效果,形成张生在书斋是“动”,莺莺在闺房是“静”,老夫人在厅堂发生的“雷霆万钧”之势是“大动”,形成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烈,使观众同情张生和莺莺的纯真爱情,谴责老夫人不讲诚信。再如“赖柬”后张生极度痛苦,老夫人失信固然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但关键人物莺莺也变卦了,也向张生传达了“自食其言”的明确信号,张生受不了,感情极度痛苦,但他永不放弃。这时“转台”的一侧是张生抱琴,步履艰难地上上下下,苦苦寻觅和强烈追求;“转台”的另一侧是莺莺无限的愁思。“转台”缓缓地转了三百六十度,任凭莺莺近在咫尺,但无论张生怎样的追寻,甚至是踉踉跄跄,就是到不了莺莺的身边,形成强烈的悬念,这样的效果不但使舞台上的剧中人焦虑,台下的观众也随之着急,因为“转台”的转动,把戏剧人物的坎坷和观众欣赏的投入“转动”到了一起。
这里,我还要谈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大奖获得者茅威涛的精彩表演。一处是在大殿做完佛事后,莺莺离去,张生望着莺莺追赶,茅威涛用前踢褶子、后踢褶子的动作(借鉴川剧表演),一方面表示张生对远去的莺莺能看一眼是一眼的急切心情,一方面表示对莺莺离去的抓耳挠腮的期盼心理。另一处是《赖柬》之后,张生心灰意冷,忽然红娘又来送请柬,张生以为一定是莺莺责备他或拒绝他,心里七上八下,犹犹豫豫不敢接柬,红娘见张生迟迟疑疑,便不耐烦地把请柬扔在地上就离去,张生围绕地上的请柬一面反复搓手,一面绕了两圈,他猜不透请柬的内容,最后还是鼓起勇气从地上拾起请柬,先是将请柬用双手举在远处,逐渐往眼前移动,结果一看便大喜过望,原来是莺莺邀请他晚上到后花园相会。茅威涛在杨导“综合各个元素产生演出总体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突出表演艺术,因为演员表演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茅威涛在杨导总的导演构思的框架内,通过对张生这个人物的深切体会,运用形体动作,成功地塑造了张生经历各种坎坷却百折不挠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决心。
总之,在越剧《西厢记》中,杨导通过强势的导演构想,使全剧剧情紧凑、流畅,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并且通过“转台”的巧妙运用,形成戏剧的抒情性十分明显,成功地完成了“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
越剧《陆游与唐琬》是一部历史剧。陆游的一生坎坷困顿,他屡试不第,以秦桧为首的权奸当道,陆游很难有出头之日。面对北中国被金人占领、南宋只有半壁河山,他报国无门,一筹莫展,深深地陷入了“兵魂销尽国魂空”的痛苦之中。家庭内部陆游的处境也很凄苦,夫人唐琬是他母亲的内侄女,夫妻鱼水和谐,但陆母抱怨儿子“偏听枕边话”,担心“大事不与母商量”。陆游已长大成人,并且是才华横溢的文坛词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但是,陆母仍把住儿子不放,一切行事都要听从她的安排,于是形成母子、婆媳的矛盾。焦点是陆游究竟是在自己家门口的杭州做官,还是在唐琬家门口的福州做官,陆游不愿在杭州为官,他回避在投降派秦桧的指挥下过着屈辱的宦海生涯,陆游愿到福州做官,他说:“福州多有忠义之士,共商恢复河山,可以摆脱秦桧的约束。”可见陆游是从政治着眼的,唐琬支持丈夫的主张。但是,陆母政治上糊涂,她要陆游“莫把丞相视作仇”,要求陆游留在杭州谋官,陆母与陆游、唐琬的分歧,看起来是家庭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对时局的判断和对奸相秦桧的评价问题。陆母怨恨唐琬,终于拿出了杀手锏,要陆游“出妻”,陆游是孝子,无奈将唐琬转移出陆府,别处安置在小红楼。茅威涛饰演的陆游,陈辉玲饰演的唐琬,为了表现夫妻和谐,唐琬在弹琴,陆游缓缓走来,先是在唐琬身边踱来踱去,欣赏妻子的高超琴艺,然后与唐琬一起弹琴,琴声悠扬,形成琴瑟和鸣的景象。洪瑛饰演的陆母,决心驱逐唐琬,她狠狠地摔琴,把陆游和唐琬的心摔碎了,陆游从地上把琴拾起抱在怀里,意在温暖妻子破碎的心。茅威涛和陈辉玲表演的陆游、唐琬很深情、内在。当陆母要陆游“出妻”之后,陆游悲愤、激越的舞剑,唐琬则悲愤、忧怨的舞袖。后来在别居的小红楼,唐琬舞袖长长地抛向空中,向上天表达哀怨,然后昏厥倒地,她十分孤独、痛苦,老一辈小一辈的思想和观念无法沟通。唐琬在小红楼又弹琴,诉说自己的愁思,陆游也与妻子一起弹琴,表现深深的理解,琴弹到极致,二人抱琴依偎,难解难分。唐琬住在小红楼三个月,陆母已有所察觉,唐琬抱怨离去,夫妻从此分离。三年后陆游浪迹天涯,感慨伤怀,陆、唐二人又重新相聚在沈园,唐琬已再嫁宗室士人赵士程,陆、唐邂逅相逢,先是“大推磨”,后是“小推磨”,表示二人意想不到的惊讶,难以置信,但毕竟是现实。陆游面对物是人非,百感交集,一下子呆傻了,发出了“茫茫情天难补恨”和“一生痛苦是婚姻”的悲鸣,于是写下了千古传唱的《钗头凤》,唐琬亦和之。此时唐琬剧咳吐血,她的心被撕碎了,一切期待和寻觅都付之东流。陆游在政治上有气节,在家庭中讲孝心,两个年轻的生命,在世道、家道中挣扎,唐琬倒下,陆游仰天长啸。
杨导在越剧《陆游与唐琬》中,紧紧抓住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把全剧的结构以“婚变”为界分成两个区块,前一个区块表现陆游与唐琬夫妻的和睦和陆游力争夫妻关系的存续的努力,但终于失败后一个区块表现陆、唐再次相遇沈园,二人十分尴尬、无奈,两颗纠结的心在碰撞,似埋怨,又似哀怨。茅威涛和陈辉玲演得很深刻。杨导和演员们的切磋、沟通,前一个区块,主要用剑、琴,表现人物的心灵深处。后一个区块利用《钗头凤》词,运用音乐的效果,表现两颗破碎的心无法修补,已再难破镜重圆了。杨导在《陆游与唐琬》中,不追求矛盾的尖锐和大起大落,同样如《西厢记》那样,运用抒情性的舞台处理和调度,完成了悲剧意义的提升。
一个有成就的导演,其才华主要体现在对戏剧主题树立的高度,对剧中人物开掘的深度,对舞台装置设计的适度,而不在于使观众处处看到导演的斧凿痕迹,只充当一个工匠,那是导演的悲。小青导演的功绩和贡献,在于自己艺术胸襟的宽度,才有戏剧的大度。小青导演艺术的惊艳,应当很好的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