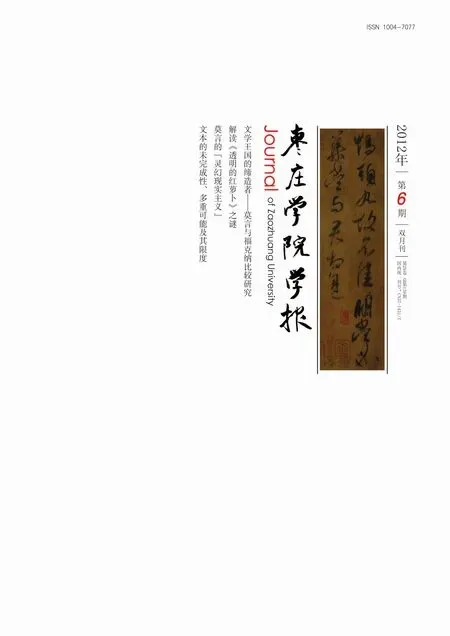解读《透明的红萝卜》之谜
刘旭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2012 年10 月,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对此众说纷纭,认为莫言不该获奖的居然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不提那些没读过莫言作品的,读过的人中间至少有相当多的人不懂莫言的作品。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和探讨如何理解莫言的作品,掌握了这一篇小说的解读方法,对于莫言的其他作品也就有了个有效的认知入口。因为《透明的红萝卜》在莫言的整体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莫言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在同一篇中莫言还说:“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1]
1985 年春,《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第2 期上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20多年过去了,评论界引进的理论越来越多,对莫言的解读也越来越丰富,本文从叙事学入手尝试分析这篇小说的特点。对于莫言的小说,叙事视点的选择非常关键,《透明的红萝卜》中由黑孩确立的儿童视点在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黑孩的叙事视点决定了整个文本的故事语法。叙事语法确立之后,才形成整个文本的叙事结构。故事语法是一个叙事文本的原始架构,或者说像是一幢大楼的框架的手绘草图。因此可以说,叙事作品都是由简单的故事语法衍生出丰富复杂的话语。从故事到话语,是一部叙事作品非常重要的建构过程。故事,可以来自神话、民间传说、一些传闻或是作家的经历,类似原型或母题,故事语法的规则指一个作家如何重写原始素材,在重写过程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形成意义层面的叙事目的。
对于这篇小说,作家对故事的重写过程中各种经历与思想的植入、叙事视点的选择等都产生的重重不解之谜,或者说不解之谜与作家的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意义层面的复杂意旨嵌入直接相关。其实故事/素材很简单,黑孩的家庭经历是农村常见的故事,即后妈的虐待,相当于一个继母母题,类似西方的灰姑娘的故事。在黑孩的家庭环境中,父亲的缺席造成后妈精神的扭曲,还有一个对抗性的、后妈生的新弟弟,黑孩因此饱受虐待,没饭吃还要干重活,深秋了只穿一条短裤,裸露的背上全是伤疤,后妈的一切怨恨和压力都转嫁到黑孩身上。故事开始于中国的灰姑娘走出家庭,无意中参与了一次社会性的事件。由此,一个备受摧残的孩子单独进入了成人世界。
从故事到话语的编码规则是一个关节点。首先从故事/素材到情节是编码的直接目的,也是叙事建构的关键步骤之一,即作者要把故事/素材转变成情节,中间要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换,就是如何把故事语法转换成叙事语法。故事的特点是事件的线性排列,按时间进行。情节则是把事件之间的关系由线性时间发展处理成因果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就是当前许多名著被重拍或重写过程中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一部小说或一个神话传说被重写之前先要被还原成原始故事,然后作者进行故事语法的重写,产生新的故事规则,武则天的故事即为典型。历史上的唯一的武则天,从五四以来至少有了十几本以武则天命名的小说,林语堂、苏童、赵玫、北村等作家都写过同名作品,但武则天的面貌在每个作家那里都是不同的,这是为什么?武则天是故事,以武则天命名的小说则是叙事,情节是叙事基本组成部分,武则天的历史事件在被处理成情节的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加入导致了情节的不同,由此所产生的意义层面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也截然不同。如武则天杀死自己的女儿这件事,是否存在已经是个问题,有的作家的作品中写了,有的没写,这就有了很大不同。另外,如果真的杀了自己的女儿,对她的行为如何评判也会形成重大的情节的差别,问题就在于因果关系常常是作家主观情感的产物。作家可以认为武则天心狠手辣丧尽天良,那么,杀女情节的因果关系就被处理一个残忍的阴谋家的夺权行为。如果是同情,那么就会在因果关系上加入武则天不得不如此的因素,则变成残酷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因此对武则天的编码和解码都变得极其复杂。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把自己的故事经过虚构之后处理成不同的因果关系,形成不同的情节。莫言在情节转换的过程中他把灰姑娘的故事隐入背景,继母母题成为行动主体的心理活动的内容和其他行为主体的对话内容。小说重点叙述的是黑孩走出家庭之后的故事。修水闸是成年人的事,黑孩不合时宜地加入进来,叙事编码一开始就出现奇异的因素。而在此编码过程中,叙述行为不断制造出复杂的情节,黑孩与菊子、黑孩与小石匠、黑孩与小铁匠、黑孩与老铁匠构成了情节的序列。叙事文本提供了复杂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迷惑重重。前面说过,《透明的红萝卜》的故事语法非常简单,黑孩的存在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一女两男的爱情,时间的自然推进产生出悲剧化结局,菊子在两个情敌的争夺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莫言在重写故事的过程中把无关紧要的黑孩安排为叙事的中心,其他的都成为催化情节。通过分析其故事的重写规则过程中情节的因果关系,可知作者在文本形式层面如何操作,从而达到了意义层面的复杂之境。通俗地说,就是整部作品从语言到内容的大师级的感觉是如何营造的。这不仅仅是叙事话语的操作能达到的,还与作家本人的才华和对社会的理解及整合形式与意义的能力直接联系。
故事开始之后,继母母题就退后成为故事的背景。进入1960 年代初大跃进时代的中国农村,描写了饥饿下的人群。饥饿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背景,但叙述人没有刻意渲染饥饿和人们对当时的体制的憎恨,而是在容忍了一切的不平和灾难的前提下,故事分解转换为一个爱情母题、一个孩子的意识流动下的继母母题和一个古老东方的教育母题,用最纯净的语言和最丰富的内涵,描绘出一个复杂又充满生机的农村世界。
谜之一:透明的红萝卜是如何产生的?
既然题目由此命名,我们就先分析萝卜为什么透明。透明的红萝卜产生于文本的中段,一个晚上黑孩被小铁匠派去偷萝卜和地瓜,然后与菊子和小石匠、小铁匠一起烤着吃,这个奇特的现象发生在烤萝卜的过程中,黑孩看到了一个发光的萝卜: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这个谜比较容易解释,现在基本有了定论。一般认为是因为饥饿。极度饥饿之下,食物被神化,产生幻觉。即从情节的建构来看,这素材来自作者自己,莫言说过:“我以前作品都没有我。这小说全是我。”[2]自身的经历直接成为故事和素材,被作家以幻觉进行重写,改造成很有魔幻色彩的叙事片断。莫言2000 年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其中说:“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们象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叶,吃草根,啃树干,而且把煤炭当成美食,他还说到,“当我成为一个作家后,我开始回忆我童年的孤独,就向面对着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莫言很小即缀学,当别人家的孩子在读书时,他只能与牛为伴,跟牛交谈,听鸟唱歌,与他们对话,“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醒半梦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了什么叫善良。我学会了自言自语。”[3](P167~169)
莫言的许多作品都提到了童年时代的饥饿经历。最好的《丰乳肥臀》及《牛》、《三十年前的一次赛跑》等都是比较好的作品。散文集《猫事荟萃》写得也像小说,更多地涉及莫言的经历,直接写他自己少年时代的饥饿,可以与《透明的红萝卜》当成互文的文本来看。“透明”产生的原因,其实在于莫言叙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叙述过程不做过多的干涉,如果从故事语法来分析,“透明”之所以变成难解之谜的原因,是因为在转化过程中,因果关系被隐藏了起来。这个谜基本与以下的谜生成原因一致,都是作家在建构情节过程中隐藏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谜之二:黑孩为什么不愿接受别人的关怀?
备受压抑而变得极其沉默的黑孩进入成人世界之后,他的最大特点是疏离感。即使与很关心他的菊子也保持着距离。那么,这个黑孩到底在想什么?先看他对陌生人的反应:“全工地的男人女人们都叫他‘黑孩’儿,他谁也不理,连认真看你一眼也不。只有菊子姑娘和小石匠来跟他说话时,他才用眼睛回答他们。”
对难得关怀他的老铁匠,黑孩还是不领情:“‘冷不冷?’老铁匠低声问。黑孩惶惑地望着老铁匠,好象根本不理解他问话的意思。‘问你哩!冷吗?’老铁匠提高了声音。惶惑的神色从他眼里消失了,他垂下头,开始生火。他左手轻拉风箱,右手持煤铲,眼睛望着燃烧的麦秸草。老铁匠从草铺上拿起一件油腻腻的褂子给黑孩披上。黑孩扭动着身体,显出非常难受的样子。老铁匠一离开,他就把褂子脱下来,放回到铺上去。老铁匠摇摇头,蹲下去抽烟。”
黑孩对众人是不理不睬,仿佛他们都不存在。但对老铁匠的关心,他不是不理睬,而是很不安。这个也好解释,基本上是意味着他在久经后妈的虐待和压抑之后形成对成人世界的警惕。但在无人之际,这个沉默的孩子却做另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很快地他又走到了妇女们砸石子的地方,他曾经坐过的那块石头没有了。他很准地找到了菊子姑娘的座位,他认识她那把六棱石匠锤。他坐在姑娘的座位上,不断地扭动着身体,变换着姿势,一直等调整到眼睛跟第七个桥墩上那条石缝成一条直线时,才稳稳地坐住,双眼紧盯着石缝里那个东西……
文本用角色的行动而不是叙述来表现出复杂的内涵,而其意义都需要读者去解读,这更有挑战性,也更增加文本意义层面的张力。这儿形成一个谜中谜,即:桥洞里的秘密是什么,代表了什么?从故事语法来看,这个谜在现实中肯定有因果关系,而作家在重写故事规则的过程中却将因果关系省略掉,形成叙事的空白,而被隐藏的因果关系正是秘密的所在。桥洞里的秘密是菊子给他包扎伤口用的手帕,它有着更深层的心理暗示:对一个年轻女性的关怀的感激和试图将之化为永恒。这些又是黑孩偷偷的地去做,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隐秘的温暖,应该说明黑孩知道珍惜这一情感,但却明白这是不可能长久的,更不可能改变他现在的家庭关系,而残酷才是常态。所以他只能冷漠。另一重原因可能是他已经太不习惯别人的温暖,意味着黑孩在压抑下表达和交流能力的丧失。可以说是异化环境下的异化人格。黑孩不能算是正常人,只能说是性格被部分扭曲了的未成年人,个体的软弱造成恐惧被无限放大,对成人世界的恐惧也会成为沉重而长久的阴影。所以他对菊子的感激会变成一个怪异的行为。是莫言的叙事策略造成了这个难解之谜,因果链的断裂造成意义的缺失,同时也是意义的张力所在。叙述中省略的部分反而比叙述的部分更有感染力。同时这种张力也让黑孩的怪异行为更有发掘的价值,接受者也更容易获得阅读的快感。
谜之三:对菊子有着奇特感情黑孩为什么咬了菊子?
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中,作为行动主体的黑孩的行动场景发生了一次变化,从砸石头工地转到了打铁的场地。这一转换的原因,叙述人说清了因果关系,是因为黑孩掌握不了砸石头的技能,砸伤了自己的手,当然也因此赢得了菊子更多的关怀。黑孩初进打铁的桥洞,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打铁拉风箱的技能,也没人教他,一开始就受到小铁匠的恶毒的咒骂,黑孩受到严厉的责骂后的反应也很严重:
孩子急促地拉着风箱,瘦身子前倾后仰,炉火照着他汗湿的胸脯,每一根肋巴条都清清楚楚。……菊子姑娘看到黑孩的下唇流出深红的血,眼睛里顿时充满泪水。她喊道:“黑孩,不给他们干了。走,回去跟我砸石子儿。”她走到风箱前,捏住了黑孩那两条干柴棍一样的细胳膊。黑孩拼命挣扎着,喉咙里呜呜地响着,象一条要咬人的小狗。……黑孩恨恨地盯了她一眼,猛地低下头,在姑娘胖胖的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她“哎哟”了一声,松开手,黑孩转身跑回了桥洞。
黑孩在刚开始从事一种劳动最不适应也最难过的时候,菊子来带他走,类似民间故事中的解救行为,黑孩应该感谢菊子才对,何况从一开始就只有菊子在关心他,他最感激的也应该是菊子,但他却在这时狠咬了菊子一口。叙述人没有任何解释。这同样是作家在建构叙事世界时省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黑孩的怪异行为愈发让人疑惑,这个小东西是什么做的?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叙述人偏偏不做任何解释——咬了就咬了。
再往下看,我们可能看出些原因所在。黑孩去拉风箱,这是需要技术的,黑孩开始时拉不好,火灭了,小铁匠很粗鲁地骂了他。从事实来看,对一个孩子提这种要求太过分了。但黑孩的倔强性格发挥了作用,他非要拉好风箱。因为,对于一个农民,劳动是最基本的生存本领,黑孩只是个孩子,但在家庭压迫和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下也领略了这一点乡村伦理的真谛。看下一个叙事片断对打铁场面的细致描述:
老铁匠把钻子放在铁砧上,用小叫锤敲了一下铁砧的边缘,铁砧清脆地回答着他。他的左手操着长把铁钳,铁钳夹着钻子,钻子按着他的意思翻滚着;右手的小叫锤很快地敲着钢钻。他的小锤敲到哪儿,独眼小铁匠的十八磅大铁锤就打到哪儿。老铁匠的小锤象鸡啄米一样迅疾,小铁匠的大锤一步不让,桥洞里习习生出热风。在惊心动魄的锻打声中,钢钻子火星四溅,火星溅到老铁匠和小铁匠围腰护脚的油布上,“滋滋”地冒着白色的烟。火星也飞到了黑孩裸露的皮肤上,他咧着嘴,龇出两排雪白的小狼牙齿。钢火在他肚皮上烫起几个大燎泡,他一点都没有痛的表情,眼睛里跳动着心荡神迷的火苗,两个瘦削的肩头耸起来,脖子使劲缩着,双臂交叠在胸前,手捂着下巴和嘴巴,挤得鼻子上满是皱纹。
叙述人对劳动场面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叙事节奏平稳从容,叙事密度突然增大,故事时间在叙事停顿中被拉伸,时间好像凝滞了,打铁的动作缓慢而诗意,而叙事话语带来了隐含的快乐修辞效果。所以,无论对于作者还叙述人还是行为主体黑孩,打铁都成了劳动美的表现场域之一,因为它意味着生存技能,而技能熟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变得象舞蹈一样美,象诗一样具感染力:
黑孩双手拉着风箱,动作轻柔舒展,好象不是他拉着风箱而是风箱拉着他。他的身体前倾后仰,脑袋象在舒缓的河水中漂动着的西瓜,两只黑眼睛里有两个亮点上下起伏着,如萤火虫幽雅地飞动。
姑娘目瞪口呆地欣赏着小铁匠的好手段,同时也忘不了看着黑孩和老铁匠。打得最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
这是由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以来极少有的对劳动之美的描写。有此举者只有莫言。其他的自称工农兵作家者虽然也想描写劳动,但总因人在劳动之外而无法真正体会劳动之美。黑孩咬了菊子的真正原因,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掌握这一劳动技能,菊子拉他走是剥夺了他努力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还和他那种倔强的性格有关,他被骂无用,他就要证明他能做到。乡村生存伦理也已经深深地积淀在生活于其中的黑孩的潜意识之中,为了以后的生存,他就必须要劳动。
谜之四:小铁匠和小石匠打架,为什么黑孩帮的是对他极坏的小铁匠?
在整个叙事文本中,小铁匠作为次要行动主体一直是个恶人形象,从黑孩帮忙打铁开始就没说过一句正常的话,不是骂就是训斥。像小铁匠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的原型很多,他代表着那样一种极端粗暴又极端自私的人,从不为别人考虑,一切都是要求别人必须满足自己的要求,至少自己是否满足了别人,他是从来不用想也不会想的。小铁匠从来都是骂黑孩,又数次命令黑孩去偷东西给他吃。最重要的是,他破坏了黑孩最神圣的透明的红萝卜。看一开始他如何骂黑孩:
“让这么个毛孩子拉风匣?你看他瘦得那个猴样,在火炉边还不给烤成干柴棍儿!”小铁匠不满意的嘟哝着。
“要拉火的不要他!刘副主任,你看看他瘦得那个样子,恐怕连他妈的煤铲都拿不动,你派他来干什么?臭杞摆碟凑样数!”
这是对黑孩的存在价值的完全否定,也给黑孩带了巨大的耻辱,这个耻辱直接造成了黑孩咬菊子的后果。另一方面,是贪婪的小铁匠抢走了本属于黑孩的萝卜,他已经吃了几个,黑孩一个都没吃,他还过来抢,而且那个萝卜是黑孩的梦想,一个神奇的透明的红萝卜。但小铁匠全无一点做人的基本良知,像狗一样和黑孩撕抢,并打了黑孩,最后把红萝卜扔进河里,让黑孩的梦想就此破灭。而且这红萝卜还是他命令黑孩偷来的。这样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人,黑孩应该非常恨他才对。另一方面,小石匠虽然开始时对黑孩并不好,使劲敲黑孩的脑袋,表现出人性恶的一面,但和菊子的恋爱开始后,小石匠总是和菊子一起关心黑孩,黑孩也知道菊子爱小石匠,但后来两人因为菊子发生了冲突,黑孩子为什么不看菊子的面子帮助小石匠?
对此,不少人解释说黑孩对菊子有了那种朦胧感情,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但在潜意识中对菊子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感激,文中特意描写到黑孩非常注意一种鸟叫声,那是小石匠发出的信号,让菊子溜出去两人幽会。黑孩这时,嘴角会露出一丝冷笑。就是说,黑孩的潜意识已经有了男女之爱朦胧意识,和小铁匠对小石匠的恨一样,是一种爱的嫉妒。这样解释当然很有道理,小说文本中也有明显的暗示。但大家都没注意到的是另一重更重要的原因。小铁匠曾经对孩子说过这样一段话:“别回家,我收你当个干儿吧,又是干儿又是徒弟,跟着我闯荡江湖,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这句话对黑孩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句话发生场景是菊子和小石匠一起来接黑孩,要带黑孩回家,小铁匠出于嫉妒而与小石匠争夺黑孩,并不是真的对黑孩好,但是,这句对黑孩的影响却很可能是一生的。因为,这是饥饿的乡村中一个巨大的生存希望。这个谜与下一个谜有隐蔽且关键的联系。
谜之五:老铁匠为什么不告诉小铁匠打铁的秘密?
整体文本中,小铁匠和老铁匠的关系更是迷惑重重,且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整个不解之谜在于小铁匠一直想发现老铁匠打铁的秘密,即如何把钻头打得坚韧耐用。小铁匠曾经自以为学到了老铁匠的全部本领,像那只跟猫学艺的老虎一样,不尊重老铁匠,在某天老铁匠不在的时候,想大展身手,结果却遭遇惨败,被众石匠们大骂无能,因为他打的钻头用不几次就或弯或断。小铁匠才知道老铁匠的老奸巨猾,之后便一直致力于去寻找老铁匠的秘密。老铁匠也一边得意,一边故弄玄虚,让小铁匠难以偷走他的杀手锏。为什么会这样?按常理说,他们是师徒关系,师父应该毫无保留地教会徒弟一项技能。但老铁匠不,就是不告诉小铁匠。这背后隐藏了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伦理问题,先看老铁匠的一段表现:
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老铁匠只唱了这一句,声音戛然而止,听得出他把一大截悲怆凄楚的尾音咽进了肚子。老铁匠又看了小石匠一眼,低下头去给刚打出尖的钻子淬火。淬火前,他捋起右手衣袖,把手伸进水桶里试着水温,他的小臂上有一个深紫色的伤疤,圆圆的,中间凸出,尽管这个伤疤不象一只眼睛,小石匠却觉得这个紫疤象一只古怪的眼睛盯着自己。
这个叙事片断的第一句是高密乡流行的戏曲茂腔《西京》里李彦荣妻子裴秀英唱段,一个类似陈世美的故事。这句戏文代表着乡村的残酷生存状态:即使是夫妻也常常是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同富贵。整个乡村的生存伦理也是如此,文本刻意强调的老铁匠胳膊上的大大的眼睛一样的伤疤即是残酷性的表现之一。伤疤成为一个寓言,它的寓意在一下段小铁匠最终发现其秘密时得到揭示:
老铁匠伸手试水温。加凉水。满意神色。正当老铁匠要为手中的钻子淬火时,小铁匠耸身一跳到了桶边,非常迅速地把右手伸进了水桶。老铁匠连想都没想,就把钢钻戳到小伙子的右小臂上。一股烧焦皮肉的腥臭味儿从桥洞里飞出来,钻进姑娘的鼻孔。小铁匠“嗷”地号叫一声,他直起腰,对着老铁匠恶狠狠地笑着,大声喊:“师傅,三年啦!”老铁匠把钢钻扔在桶里,桶里翻滚着热浪头,蒸气又一次弥漫桥洞。姑娘看不清他们的脸子,只听到老铁匠在雾中说:“记住吧!”
小铁匠以同样的代价换取了打铁的最终秘密。他的胳膊上也被烧红的钻头烫伤出一个巨大的血洞,但小铁匠感觉到的首先不是伤痛,而是巨大的快乐。在这儿表现的正是东方的轮回观念和严酷教育传统的深远影响。轮回观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切都要亲身去经历,像对“道”和“惮”一样强调本人去“悟”,别人经过的苦难与你无关,你同样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这也是底层的生存观之一,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只能面对苦难,以轮回来安慰来麻醉自己,但同时形成了东方民族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常年食不裹腹的状态之下,底层生存之际形成了紧张的竞争关系,这与中国小农社会的生存伦理相辅相成,所以,老铁匠在教育徒弟的过程中,除了中国传统的以打骂为手段的严苛教育方式,还和底层残酷的利己原则相关,活着才是根本,老铁匠必须保住自己饭碗,莫言也说过:“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3](P169)所以,对老铁匠来说,徒弟不是儿子,而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小铁匠与老铁匠的故事意味着中国乡村伦理与下层人民的生死轮回之道。所以,小铁匠发现老铁匠的秘密没两天,老铁匠就一声不响地永远消失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来和小铁匠竞争,如果和小铁匠一起,已经不再是合作关系,因为师徒关系也已经终结,老铁匠的生存会面临重大的威胁。这种结局更深刻地寓示着残酷的乡村生存伦理下底层生存的艰难。内部竞争一直是中国民众生存的巨大障碍。这儿也可以解释黑孩帮助小铁匠打架的另一重原因:小铁匠收他为徒,就是给了他一生的依靠。这种帮助,远比菊子给他点食物、给他条手帕重要的多,因为,几千年前的《盐铁论》中已经昭示了一个农耕社会的事实,手工业和商业能带来远超农业的巨大收益。所以,小铁匠给黑孩的不止一个师徒关系,而是还有黑孩一生的生存资本,它对于任何一个农民都无可替代。
余论:无所不在的未解之谜
总之,一切都是复杂的,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复杂的一个,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尽可能复杂地去理解莫言,许多谜仍然没有定论,有待更多的后来者去阐释。
如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还有许多的未解之谜,如谜之六,黑孩为什么期待那样一个透明的红萝卜?透明的红萝卜为什么找不到了?谜之七,最后,黑孩的鞋子和上衣从哪儿来?一个个谜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和儿童心理密切相关,形成巨大的张力和真文学的魅力。注意,对于莫言的作品,我们要当成一个复杂的叙事文本,不必按照意识形态批评和社会学批评方式非要得出一个固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莫言是最具包容性的作家,在十年前我的第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中我就说莫言是比西方的上帝更具包容性的作家,西方的上帝在博爱的背后恰恰是极度的狭隘,必须成为他的子民才能得到他的垂青,不是他的子民,即不信仰他,就成为上帝的弃儿。莫言绝不如此,在他的笔下没有弃儿,从道德判断上角度看再坏的人在莫言的作品中也有他的善良的一面,不会被完全否定存在的价值。莫言作品中所反应的更多的中国道家文化的那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包容性,又与儒家的仁义息息相关,整个作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从这篇小说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很少有知识分子能平静地去描写他,特别是对极左时期难以宽容的80 年代,只有莫言不但做到了淡然,而且写出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另一面,即不是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西方式现代的召唤下致力于描写东方乡村的阴暗、制造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式的自我他者化叙事,而是在包容了人性的阴暗和时代的错误之后,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中国农村的神秘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相结合,给中国乡村文明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莫言曾说过“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就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 的,就 是 优 良 的 品 种。”[3](P167~168)即 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蕴含的那种生机和韧性也深深地融入莫言的潜意识之中,那是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他不需要专门去研究老庄,不需要研究乡村伦理,他生活的土地就已经蕴含了一切,这个成长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伟大作家,他不必刻意是什么,他只要在那儿就足够了。
[1]莫言.自述[J].小说评论,2002,(6).
[2]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创作前后[J].上海文学,2006,(8).
[3]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A].小说的气味[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