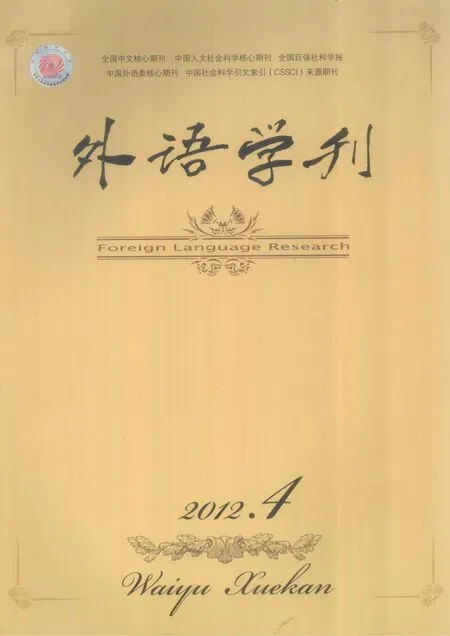论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中的“逻辑证实”
郭 佳
(长治学院,长治046011)
1 引言
众所周知,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在阐释意义生成与理解的尝试方面,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以下简称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独特地位。具体讲,学界普遍将维特根斯坦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认为他在这两个时期内分别提出两种不同的意义观——“图像论”(picture theory)和“游戏论”(language-game theory)。学者们将目光投向这两种意义理论的单一性研究及其对比研究。所谓对比研究,就是强调前、后期意义理论的对立性、异质性。调查发现,仅有少数学者把维特根斯坦从1927年到1935年间的思想看成其整个思想发展的一个独立时期,即所谓“转型期”、“过渡期”或“现象学时期”。本文将这些说法统一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中期”。因此,作为维特根斯坦这一时期的意义观“意义证实论”(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中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中,学者仅仅提及这一理论。张学广初步归纳维特根斯坦的中期思想,讨论他的“证实原则”(张学广2003:51)。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证实论。维也纳学派借鉴维特根斯坦证实思想的目的在于逻辑实证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因而相关著作并没有全面阐释与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证实思想,尤其是他的意义证实论(艾耶尔1989:226)。然而,考察中期维特根斯坦思想,尤其是研究他的意义理论,无疑是揭示其思想转型“真相”的关键所在。须知,考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有助于揭示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我国语言哲学发展。徐英瑾尝试从考察现象学出发,弥合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断裂(徐英瑾2005),但是他的着眼点是现象学而不是语言哲学。综观学界,目前还没有学者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艾耶尔 2006:38)——意义理论出发,研究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连贯性和两个时期思想形成的整体性。于是,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应该成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
中期维特根斯坦的证实思想产生于他对数学证明的研究。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意义理论,其初衷是检验“图像论”意义观。“图像论”意义观认为,对命题形式和命题内容的要求,即逻辑句法要求与经验事实要求共同构成判定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正是依据这两条标准,命题意义的证实具有两种方法: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①;也正是这两种证实使得意义证实论作为维特根斯坦意义观发展的中间环节,兼备其前后期思想的双重内核。鉴于维特根斯坦证实思想体现在文本中的细腻繁杂,笔者对意义证实论的归纳与梳理主要从证实方法、证实困难和证实反思3方面展开;限于篇幅,本文研究逻辑证实。
2 证实方法
调查发现,中期维特根斯坦通过证实检验“图像论”意义观的主观原因来自学界对他前期思想的广泛批评;而客观原因就在于,“图像论”澄清命题意义的诉求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证实的要求”(张学广2003:365)。“图像论”意义观要求有意义的命题首先在形式上符合逻辑句法,这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强调的命题的“逻辑可能性”(Wittgenstein 2003:85)。逻辑证实就是从逻辑上验证命题是否具有表达意义的可能。其构造符合句法规则的句子首先具有逻辑意义,同时具备经验证实的前提。“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Wittgenstein 1979:227)“命题所能说的不外就是由证实的方法所确定的东西。”(维特根斯坦2003a:198)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在证实原则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对证实方法的强调。判断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是“证实的可能性”,“这种证实的可能性需要句法来解释”(Wittgenstein 2003:119),即需要由命题的逻辑分析呈现。逻辑证实的方法就是对命题的逻辑分析,它回答“怎样通过逻辑分析得出命题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如下:
“命题具有意义,语词具有意指”(维特根斯坦2003a:191),人们通过规定语词意指使有意义的命题得以产生。有意义的命题必然按照规则建立,命题中的符号(语词)就是“由规则所引导的应用记号”(维特根斯坦2003a:200)。记号是感官在符号上觉察的东西。一个记号的使用规则就是它的含义,“赋予一个记号以含义,意味着提出一个使用它的规则”(Wittgenstein 2003:119)。赋予记号含义的主要方式是下定义,这也是前期维特根斯坦为逻辑语言制定的逻辑规则。逻辑证实围绕对记号的“定义”展开。
“定义借助其他的记号来解释一个记号的含义,一个记号就是这样指向另一个记号,另一个记号又指向其他记号,等等,记号就是这样排列起来的。一个记号指明了它通往所有用以定义它的记号的道路。如果我们按照定义用其他的记号来代替这些记号,用另外一些记号来代替这些记号的记号,如此进行下去,从而分解一个陈述中的这些记号,那么,证实的道路就逐步清晰了。定义就是做路标。它知道通往证实的道路。”(维特根斯坦2003a:202)事实上,命题本身就包含用以构成命题的那些记号的定义,“这些定义在证实中引导我们”(维特根斯坦2003a:202)。因此,命题本身包含证实它的方法;对命题的逻辑分析就是沿着定义的路标摸清证实的道路。一旦这条道路上的某个记号没有所指对象,并且它也不能通过定义还原为其他记号,那么“通往证实的道路就堵塞了”(维特根斯坦2003a:208)。
然而,“证实的道路不能走向无限。有意义的命题已经通过整个定义的链条说到了现实”(维特根斯坦2003a:202)。为得出命题的意义,我们必须借助一串连续的定义来转换命题,直到最后转换出的记号是不能再被定义的记号,它们的意义只能被直接给出。换言之,“证实已被推至最后的点,人们不能越过此点而继续推进”(维特根斯坦2003a:203)。这个“最后的点”就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elementary proposition)。这样,一个命题最终被转化为若干基本命题;基本命题直接与现实相关,它们先验地给予所有命题意义。“语言用基本命题指涉现实”(维特根斯坦2003a:204)。
至此,逻辑分析引领我们抵达证实道路的终点,即“知识与实在之间的不可动摇的接触点”(陈嘉映2003:150),它是证实的最终保障。与“图像论”不同,这一终点不再是无法经验的逻辑终点,而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和经验。
3 证实困难
逻辑分析得出命题的意义。然而,“逻辑分析不是一开始就赋予命题以意义的”(维特根斯坦2003a:203)。逻辑证实的前提是句子可分析、可证实,句子构造符合句法规则是这一前提的判断标准。问题是:在证实之前,我们怎样根据句法规则判断句子有意义?为解决这一问题,维特根斯坦转换视角,重新阐释“句法(句法规则)”②。
维特根斯坦注意到,有意义的句子必然能够被理解;可理解的命题就是可证实的命题;这样,证实就成为理解命题意义的重要途径。“为了理解一个命题,将追问它的意义转化为追问它的证实方法,总是非常有用的方式。”(Wittgenstein 2003:119)可见,维特根斯坦此时转变视角:从“人”出发,开始对人的世界(内在世界)中“理解”等问题的思考——这标志着他在意义理论上乃至整个哲学思想上的转折性飞跃。为深入研究“理解”与“句法”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提出“体系”(system)(或“系统”或“形式”)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他的意义观开始从逻辑原子主义向整体主义③过渡;并且,后者预示着维特根斯坦本体论语言观的形成。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语言及语言的全部规则都在“体系”中。对某一命题而言,定义这一命题中所有记号的规则群同样形成“体系”。命题的意义由构成句法的“规则体系”决定。
第一,维特根斯坦认为,每个命题P都处于体系中。然而,体系到底是怎样的体系?它包含多少规则、怎样的规则?规则能否被呈现?——“人们不能说P属于体系S;人们不能问,P属于哪个体系;人们不能去寻求P的体系。理解P,这意味着理解它的体系”(维特根斯坦2003b:170)。维特根斯坦认为,P的体系不能被言说,它只能被P显示,并由此被人理解。“体系”如同“逻辑形式”,它作为语言本身的性质被维特根斯坦引入“不可说”④之域。维特根斯坦强调,“人们不可能去追问使每个问题终究得以成立的那个初始的东西。不能去追问使系统得以建立的东西。这类东西肯定存在,这是明白无误的”(维特根斯坦2003b:194)。
第二,无论是语言整体还是个别命题,它们所处的体系都是完全的规则群。语言体系中完全的规则保障所有命题都在相应的确定体系中被理解并产生唯一的意义。“为了构建规则由之产生系统。”(维特根斯坦 2003b:216)体系为构建规则产生,只有体系——规则群才能确定意义,P要根据其确定的体系才可证实。并且,“在不知道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它是否是一个命题之前,我不会去使用这个命题”(维特根斯坦2003b:204)。P的可证实是我们使用它的前提。因此,体系或者形式中的规则一定要完全。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可能发现适用于我们所熟悉的形式的新规则。如果它是新规则,那它就不是旧形式。如果我们真想用一个概念进行工作,规则的构造就必须是完全的。——在句法中不可能进行发现——因为只有规则群才确定我们符号的意义,而且规则的每一次改变(例如补充)都意味着意义的一种改变”(维特根斯坦2003b:172)。由此,“仅仅说P是可证实的,这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说:可以根据一个确定的体系加以证明……如果P看起来是从一个体系转入了另一个体系,那么事实上P已经改变了这个体系的意义”(维特根斯坦2003b:170)。
第三,句法由语言体系中约束命题的规则总体组成。“句法作为规则的总体说明一个符号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有意义。它并不描述什么,而是限制可描述的东西”(维特根斯坦2003a:174);“无意义的语词的组合的图像通过句法被排除。所以,在记号的本质与事物的本质还不适合的地方,在记号的组合多于可能的实际情况的地方,句法将是必须的。语言的这种巨大的杂多性必须通过人工规则加以限制,而这些规则就是语言的句法”(维特根斯坦2003a:194)。句法约束语言,同时造就有意义的语句,人对语言的理解以句法知识为前提。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就是对语言句法的解释,它提供对命题的理解”(维特根斯坦2003a:175)。
综上所述,维特根斯坦以语言的系统性为预设前提,分别阐释句法规则的先验性、完整性和约束性;与此同时,尤为重要的是,他将“意义”的判定与人的理解相联系,强调句法对人们理解语言,进而使用语言的重要性。主观因素的引入直接导致证实思想的“主观化”;进而以逻辑证实为基础,经验证实对语言与实在的“观念化处理”(李洪儒2011:19)直接导致证实方法的多样化。
此外,我们为何能够证实某个命题?维特根斯坦进行猜想:语言能够被证实的前提是它本身具有一种“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然而,这种可证实性是否存在,如何证实它的存在?“可证实性的证明是什么?”(维特根斯坦2003b:169)如同“逻辑性”、“系统性”,“可证实性”作为语言本身的性质同样被维特根斯坦视为“不可说”,对它的证明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证明命题的证明”(维特根斯坦2003b:169)。“所谓的对可证明性的证明是一种归纳法,对归纳法的认识就是一种对新体系的认识。”(维特根斯坦2003b:179)“可证实性”作为事物的一种性质,它要通过对被证实事物的归纳得出。要证实“可证实性”须对“归纳”有所言说,而归纳法(经维特根斯坦论证)同样“不可说”。由此,命题的证实预设语言具有“系统性”、“可证实性”等性质,然而这些性质本身却是“不可说”——不可证实的。这似乎就暴露出逻辑证实的语言观基础“语言工具论”“局限于具体语言分析和瞎子摸象的语言研究弊端”(李洪儒2011:3)。
4 证实反思
在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与真理探寻同步展开的始终是价值性反思。这大概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兼备两种“气质”:“一种是追求逻辑清晰的科学主义气质,另一种是追求神秘性的人文主义关怀”(龚雅琴 2008:17)。这种“关怀”同样体现在逻辑证实中:“命题是用来作什么的?命题只是被缩短的解释(abbreviated explanation)。命题只有在语言中才是命题”(Wittgenstein 2003:119)。中期维特根斯坦更加关注语言本身。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仍有一只脚留在指称论的阵营”(赖尔1992:608),那么此时他的这只脚已迈出指称论。逻辑证实中,虽然意义的源头依然在基本命题所指涉的事实世界,但是整体主义视域中的命题意义已不再由语言和世界的映射关系生成,而是“完全变成语言内由逻辑完成的事情”(张学广2003:138)。这样,虽然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逻辑证实沿袭“图像论”,但是在对命题意义的理解与阐释中,证实论已与“图像论”意义观的内核——指称论全然不同;由此,“我们应当承认,证实论的意义理论比起彻底的实在论的意义理论是一个更有可能打赢的赌注”(Dummett 1976:137)。可见,证实思想已超越“图像论”所隐含的工具论语言观,而将语言视为特殊“在者/是者”进行独立研究——语言本体观此时已经蕴含在维特根斯坦的学术思想中。在此基础上,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是“在者/是者”作为建构自己语言哲学理论的预设。这在某种程度上明晰了语言哲学的发展路径,即分析性的形式化研究必将纳入形而上的本体讨论。因此,“要研究人及人的世界,就须要把分析性语言哲学对语言现象的分析纳入本体论语言哲学之中,在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语言哲学”(李洪儒2011:3)。
反思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认识到,“逻辑分析是对我们已有的东西的分析,而不是对我们没有的东西的分析。因此它是对现有的命题的分析。如果人类一直在说话而没有哪怕是说过一个真正的命题,这就奇怪了”(Wittgenstein 1975:52);“如果我们已经对一个命题作出了完全的分析,那么在分析的最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一直通过表达这一命题,确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维特根斯坦2003a:202)。并且,“逻辑分析没有必要为了达到完全清楚而对我的命题的现有含义增添任何内容”(维特根斯坦2003b:172)。逻辑分析不会赋予命题意义,它基于命题本身具有的意义进行,就是这种意义规定并引导逻辑分析。并且,人们无须通过逻辑分析使语言“达到完全清楚”就能够理解它的意义。然而,逻辑分析绝非徒劳,形式分析必然是目的探寻的手段及途径。由此,逻辑分析纵然得不出“新东西”,却还是让维特根斯坦注意到“新变化”:“看起来不清晰的东西,经逻辑分析后其原有内容仍然丝毫没变,只是它的语法变得清晰了”(维特根斯坦2003b:178)。从语言观来看,当语言作为表征实在的工具,它的“工具”性质——逻辑性必然成为逻辑分析的依据;然而,当语言作为能够独立运作的有机整体,即特殊“在者/是者”,分析过程已无须规定其依据,因为这一过程就是语言本身的运作机制,即语言本身的使用,由此产生语言的用法。从分析过程来看,逻辑证实的过程即分解命题记号的过程,记号由它的使用规则定义——证实过程要求始终关注记号的用法;对命题的分析贯穿着对语言用法的思考。据此,逻辑分析的前提和依据是命题的句法,而分析过程一直向我们呈现的则是语言的用法——语法。“语法”与“句法”显然不同:逻辑证实中,作为分析性语言哲学形式化研究的产物,“句法”依旧是“一种逻辑形式,一种可能性的框架”(张学广2003:150),它构成“形式语法”(文炳 陈嘉映2010:18)的哲学基础;而“语法(哲学语法)”涵义更为广阔,它预示着对它的研究要在更为广阔的日常语言中进行。并且,“语法”正是日常语言的核心价值及灵魂所在——“它把语言与意义,语言与应用,语言与人的活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文炳 陈嘉映2010:16)。这着实让维特根斯坦释然,“实际上,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也就是说,在眼下,我们不需要期待什么。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语法范围内活动,这一语法已经是现成的。因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不必期待未来”。反思之前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一语中的:“只要我们执着于命题的外在的语言形态,我们就只会是混沌不清的”(维特根斯坦2003a:202)。这样,清晰的“语法”代替“句法”,成为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中的另一核心概念——逻辑证实由此成为经验证实的前奏。
5 结束语
本文初探逻辑证实得出,中期维特根斯坦意义证实论的早期研究依然建立在逻辑语言基础上,以逻辑语言为背景的外显意义理论追求命题构造与事实构造相一致的可确定性。从而,逻辑证实中,意义通过对命题逻辑,即语言形式的证实得到确定。可以说,这就是根据“图像论”意义观的意义判定标准对命题意义的检验,即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后续研究。由此,在研究方法上,逻辑证实沿袭“图像论”对语言结构的静态、显性考察;在研究目的上,逻辑证实对意义的追问依旧出于探求科学真理。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期甚至认为,“真理标准与意义标准是同一的,它们都在于证实原则”(舒炜光 1982:180)。可见,逻辑证实对意义的解读依然停留在“图像论”所描摹的事实世界。
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是对逻辑语言及其意义的建构,那么中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证实则通过相应解构过程将意义的源头还原至事实世界,这是中期维特根斯坦对前期思想的继承。然而,须要注意的是,证实思想以语言为考察主体的必然要求促成了维特根斯坦语言本体思想的潜出。由此,逻辑证实对语言的实证性考察在继承前期思想的同时将意义交付语言本身。进而,语言作为本体,它的功能及运作机制——“语法”在证实中消解了由所谓证实前提和依据——“句法”衍生出的一系列证实困难,并最终代替句法。语法的完善性并非也无法由逻辑语言建构得来,而是由日常语言逐渐生成。从而,完善的语法成为考察意义的依据所在,日常语言成为意义的可靠家园。这充分表明:哲学在转向“语言”的同时彰显了其“人学”的内在属性;“鲜活”的日常语言是语言本体的应有之义,它“证实”了人的存在,并且构成了“人的世界”。中期维特根斯坦将“人”引入证实困难的探索及证实的价值性反思中,这在超越与发展其前期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向我们昭示,“语言只与人的世界有关……它不仅仅是人的交际工具,更是人的符号性存在”(李洪儒2011:4)。
注释
①石里克等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命题证实的可能性区分为“逻辑可能性”(logical possibility)与“经验可能性”(experiential possibility)。前者指把语言的逻辑语法规则应用到句子上去。在给语词下定义时创造的规则并不是我们能够“发现”的自然事实,而是下定义的行动制定的法规,它是语言逻辑的产物。后者指同自然规律不矛盾。只要是我们在同自然规律相容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判断,就是一种“经验可能性”。它是对命题语义内容的要求。经初步考察,虽然维特根斯坦并未在著作中明确认同这一区分,但是其证实思想确实包含对命题“逻辑”与“经验”的双重检验。本文将这两种性质的证实分别称为“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
②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逻辑句法”、“句法规则”与“句法”含义大致相同;它们具体指“那些能告诉我们一个词只有在哪些连缀组合上才具有意义从而能排除无意义结构的规则。”——引自《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第267页。
③“语言的意义理论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和整体主义的意义理论。前者指的是谈论词或短语的意义的各种理论,后者指的是至少在一个语句的语境中谈论词的意义,或者至少以句子作为谈论语言意义的单位的各种理论。”——引自《维特根斯坦与理解问题》,第132页。
④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前期维特根斯坦为完成“哲学的根本任务”——为思想的表达“划界”而提出的“不可说”思想。学界普遍认为,维特根斯坦视为“不可说”的东西主要有两类事物:语言的本质以及对世界整体的论断。前者以语言的逻辑形式为代表;后者以伦理学、美学命题为代表。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李洪儒.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J].外语学刊,2008(6).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外语学刊,2010(6).
李洪儒.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J].外语学刊,2011(6).
文 炳 陈嘉映.普通语法、形式语法和哲学语法比较[J].外语学刊,2010(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二卷: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a.
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三卷:哲学评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b.
张学广.维特根斯坦与理解问题[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Wittgenstein,L.et al The Voices of Wittgenstein:The Vienna Circle[M].London:Routledge Press,2003.
Waismann,F.Wittgenstein and the Vienna Circle[M].Oxford:Basil Blackwell Press,1979.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Remarks[M].New York:Barnes& Noble Books Press,1975.
Dummett,M.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Ⅱ[A].In G.Evans & J.McDowell(eds.).Truth and Meaning[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