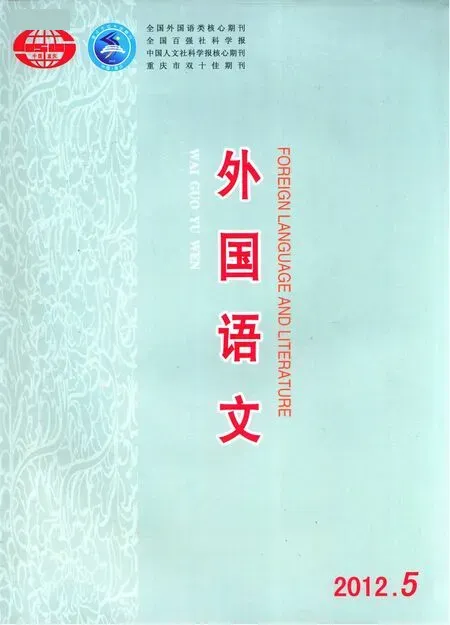历史与文本镜像中的美国华裔女性符号研究
付明端
(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开始引起国内文化界的关注。“文化寻根”、“双重身份间的游移”、“文化族性的归属”等成为诸多学者探讨的重要学术命题。近几年的学者也大多从文化、性别、族裔身份、认知心理、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华裔女作家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各种策略。本文以立体研究的视角,把华裔女性置于跨文化、跨领域的历史真实空间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旨在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话语模式,为建构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模式提供一种参考。
二、历史镜像中的美国华裔女性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华裔女性移民的历史纪录。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唤醒了华裔妇女的女性意识,华裔女性开始自觉参加争取平等权利、改革美国社会的斗争。在这样的运动背景下,华裔女性的相关记录开始出现在美国历史研究中。
在1880年之前,仅仅有很少中国女性愿意远离故土到美国。1834年,第一位到美国的中国妇女叫梅阿芳(Afong Moy),她曾在纽约某博物馆举办的文化展中出现,目的是让美国人一睹来自异国女性的真实样子。在梅阿芳之后,其他中国妇女也陆续到达美国,到1837年,估计有1784位中国妇女来到美国,她们大多住在美国西部。1870年以后的50多年中,中国妇女在美数量约4000人上下,同时期的中国男性在美人口已达十几万。华人男女数量极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美国各州制定的限制法案使中国女性无法顺利进入美国。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重点限制华人女子进入美国。美国政府还制定法案明确规定与华人女性结婚的美国男性将失去美国公民身份,很多州还颁布了反对种族通婚法案。所有这些限制加深了华裔女性的痛苦,同时也阻挡了20世纪在美华裔家庭的发展。
鉴于以上各种法案的限制,大多数中国妇女无法到美国与亲人团聚,那些设法到达美国的少数中国女性是作为性奴隶被买到美国的牺牲品。当大批收入极低的华人劳工在美国西部淘金、修建铁路时,在他们背后有着众多中国妓女在美国从事服务工作。有研究者认为:19世纪后半期,每两名在旧金山的华裔女性中,就有一人是妓女。①据估计,在旧金山,1860年,华裔妇女中85%是妓女,1870年妓女比例为71%,1880年为61%(Hirata,1979:43)。当时年龄在16~25岁的中国娼妓大多来自中国南部的贫困家庭,在悲惨的生活状况下,很多妓女都受到不同程度病痛的折磨,而痨病和性病经常是她们难以避免的疾病。她们总是受到客人和妓院主的折磨,有的妓女甚至被殴打致死,而且有的客人威逼她们进行变态的性行为,因此不少妓女在很小的时候就因非人的折磨而死。
华人社会中的娼妓业不仅被美国政府和媒体用来歪曲华人的形象,更成为其全面限制华人进入美国的借口。1910~1940年,美国移民局在旧金山湾的天使岛设立移民检查站,专门检查到旧金山的移民是否有资格入境。①天使岛(Angel Island)是旧金山湾内最美丽的小岛之一,现为郊游及野餐胜地。天使岛在历史上是与华裔美国人历史密切相关的,因为1910~1940年大部分华裔试图进入美国时被拘留于此地,其设立是为了处理排华法案中所未排除在外的对象,如商人、官员、学生、教师、游客即宣称有美国公民身份者。在天使岛上,绝望的移民写的一些诗句至今依然刻在墙上。在过境站开放的30年间,约有17.5万华人抵美。在漫长的接受检查和审问过程中,华裔妇女与丈夫、孩子被隔离审问,对未来茫然不知所措。她们承受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压力,有许多华人妇女因为无法承受如此的拘押而痛苦无比,甚至自杀。
而对那些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到达美国的华裔妇女来讲,在新环境的生活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如意。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这些早期的中国移民妇女既要积极应对生活的贫穷艰辛,又惧怕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排华活动。移民妇女不但要抚养教育孩子,而且还要和丈夫一道,为整个家庭的经济和政治生存而努力,这使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也改变了以前她们对丈夫的绝对依赖关系,在家庭事务中开始有了发言权。但是,华裔移民妇女生活的唐人街仍然是通过传统专制组织来管理的,在这种封建专制的环境中,女性的主要生活范围依然被禁锢在家庭狭小的空间,尽管她们曾满怀憧憬希望到美国得到平等自由的生活,然而在唐人街这块特殊的社区,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移民妇女虽身在国外,仍难以逃脱被男权社会边缘化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华裔女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美国民众和许多社会组织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废除了众多损害华人基本权益和法律地位的排华法案。歧视性法案的废除以及新法案的颁布极大地改变了华裔移民美国的历史状况,特别对女性移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每年平均只有60名中国妇女进入美国;在从1944~1953年期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妇女占82%。随着美国历史上华人妇女和华人家庭数量大幅度增加,华人中男女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平衡。从1940年的2.9∶1变为1950年的 1.8∶l,1960 年的 1.3∶1。
随着美国华裔女性的数量增多,女性移民整体结构趋于多样化,她们不少走出唐人街,进入崭新的行业工作。新到达的华裔女性不少拥有文化和知识,对美国文化不再陌生,她们到达美国的目的不再是逃避战乱,而是在美国继续学业或在理想的职业中发展自我。1970年,30岁左右的华裔妇女中有三分之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到1986年,大概有40%的华裔妇女在自己的技术岗位找到理想职业。尽管有很多华裔女性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美国主流社会,种族歧视和排斥现象依然以各种隐形的方式存在,华裔女性几乎没有在大型公司和集团进入高级管理阶层,这种现象被称为“玻璃屋顶”(glass ceiling)②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和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了很大改进,但是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中,94%的副总裁以上的职务,仍由白人男性占据。他们控制着美国社会真正的权势。见《玻璃天花板吗?更像是铁笼子》,《洛杉矶时报》,1995年3月20日,第4页。。而且仍有华裔妇女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局限在相对封闭的唐人街,尤其二战后到美国与丈夫团聚的妇女,生活显得格外艰辛,因为这些妇女大多已过中年,而且不懂英文,这使她们在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中永远处于弱势。
华人女性移民来到美国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不仅表现在华人职业女性人数的增加上,而且也反映在她们对家庭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中。研究华人生活的学者认为,移民他国自然改变了华人家庭原有的权力与性别关系,这导致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有了较多的机会。如果说美国社会给亚裔妇女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原因可能是因为“亚裔文化中的男性特征被美国父权制挤垮所造成,因为种族主义的白人父权制不会给亚裔男性留下任何权利”(金伊莲,1990:64)。因此,移民美国后生活的变化对于在华人社会本来就人微言轻的女性移民并无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她们因此显得比男人坚强,更能适应新环境,在家中也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
三、文本再现的美国华裔女性规约性描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白人主流支配的法律条文、学校教育、艺术创作以及各种媒体都把华裔女性定义为刻板的模式化形象。如果华裔妇女形象出现在主流文化,那一定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这正如汤亭亭所言:“把我们描述为不可理解和具有异国情调否定了我们共有的人性,因为我们被刻画成与正常人类不同,天生是不可理解的样子,而这种模式化的定义必然是无知的表现。”(Kingston,1982:55)
第一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华裔女性是英国作家萨克斯·罗墨(Sax Rohmer)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角色。萨克斯·罗墨描述了反抗白人的亚洲恐怖女首领“Fah Lo Suee”,这个女性形象有三个主要特点:富有情调、性感神秘、阴险狡诈。她洞悉亚洲人暗杀、绑架以及利用神秘毒水的种种计谋。Lo Suee还钟情于白人男人,善于利用东方女性的魔力使白人男子对她痴迷。和其他许多亚裔妇女模式化形象一样,Lo Suee把白人男性当作自己的拯救者,而白人男性也自愿把自己处于英雄的位置,帮助所谓落后种族的女性来显示他们的种族优越感。Lo Suee的形象后来被“龙女”(dragon lady)代替,成为众所周知的亚洲女性代名词。“龙女”最初是漫画家米尔顿·卡尼福创作的形象。书中讲的是典型美国人特瑞的冒险经历,为了与健康阳光的特瑞形成鲜明对比,卡尼福塑造了一个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坏女人,这位带领一帮海盗的美丽混血女子,大家都叫她龙女。龙女妖艳性感、聪明狡诈,但她和Lo Suee拥有同样的弱点就是她们都是白人男子的性牺牲品。在作品结尾,作者毫不例外以她的死亡作为白人男性欲望的终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种族和性别的差异是如何在主流社会被产生、深化,继而在传媒中不断被固定化的。
在华裔男作家笔下,华裔女性形象不约而同地与上述西方主流文化中的歪曲描述达成默契。长期以来,华裔男作家对移民妇女有很大的偏见和敌意,众多作家把华裔女性作为“他者”,有意把她们放逐在文化的边缘和失语的状态。在陈耀光的短篇小说集中,华裔妻子一般都有悲惨的结局。在他的小说中,华裔女性不是抛弃亲人的妓女,就是贪婪、自私,有极大控制欲的妻子。另一位华裔男作家赵建秀笔下的华裔女性完全不具有主流文化女性的美德和文化素养。在其小说中,女性都充当次要的配角,她们或是愚蠢、贫穷的流浪者或是邪恶残忍的虐待狂。华裔社区许多女性选择白人男性作为结婚对象的现实引起赵建秀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纯粹是漠视华裔男性的行为,这种不平和愤怒完全体现在赵建秀的小说《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1974)中。在这部小说中,华裔女子认为华裔男性缺乏性能力,没有阳刚之气从而毫无例外地想嫁给白人男子。作为反抗,这些作家把华裔女性刻画成只会以性取悦于白人男性,而在婚姻中自我贬低的形象。总之,华裔男作家和白人男作家如出一辙,站在同一战壕,对华裔女性的塑造不约而同地遵从了从卑微顺从的奴隶形象到男人性牺牲品的模式化塑造的过程。
四、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华裔男作家对华裔女性模式化塑造是因为他们更为关注“自身作为男性的身份,以及他们作为男性在亚裔族裔中的地位”(Kim,1981:145)。而华裔女作家自从19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塑造女性的崭新形象——力图用全面人格发展的女性个体代替以往男性作家笔下柔弱、有诱惑力的华裔种族妇女的整体模式化形象。水仙花就是这样的女作家先驱。
水仙花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她实际是只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水仙花曾经说过:“我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东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东西方之间这微不足道的‘桥梁’。”①引自水仙花自传《一个欧亚裔的回忆拾零》、《独立》,1902年1月21日,第132页。详见林英敏,安娜特·怀特帕克特《水仙花、春香夫人及其作品》,伊利偌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表达了水仙花作为一名欧亚裔混血儿的感想,同时也表达了她希望向世人阐释美国华裔群体的美好愿望。水仙花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1912)获得当时美国主流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欢迎。在文中,她努力表现传统华人女性的善良与高尚的品质。以美国化的春香夫人为例,她天性积极上进,让人感到亲切可爱,敢于承担责任,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在新环境中如鱼得水,开始独立思考,不受丈夫的左右,变得勇敢甚至叛逆。这个反传统的女主人公天性乐观,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女主人公独立的个性与反抗中国传统的行为进一步反映她对美国个人主义的坚定信念:即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应拘泥于他人的想法。春香夫人的行为与传统中国妇女必须遵从“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完全不一样,她成功表现了华裔女性的崭新形象。从这一意义来说,水仙花笔下的春香夫人这一女性华裔形象,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文学中华人妇女多为娼妓和女仆的传统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个世纪之前,水仙花就在为华裔妇女的应有权利开始呐喊了。
早期的第二代华裔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美国大众对华裔的普遍认识,同时试图将自身民族文化转换为可以帮助自己进入主流社会的积极因素。通过正面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化,他们希望为华裔塑造一个模范族裔的新形象,从而被美国社会所理解并接纳。黄玉雪被汤亭亭称为“华裔美国文学之母”,她的代表作《华人阿五》既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华裔女子的故事,也塑造了一个华裔女儿作为模范族裔的形象。小说表现黄玉雪极力进入美国主流的勇敢和执着,经受的种族歧视反而坚定了她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信念。面对种族歧视的干扰,她们冷静地用保持沉默来表现自己的文明修养,不是将愤怒与委屈发泄到美国社会主流的群体上。此种沉默行为有可能使美国白人更加认为华裔是没有自信、逆来顺受的民族。但是,在当时,黄玉雪的做法应该是典型美国华人的为人之道。一位研究少数族裔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美国华裔之所以能够数次度过灾难,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信念中寻找到安慰和力量。就此意义来看,黄玉雪不过是仿效先辈的例子。黄玉雪想要塑造一个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愿望虽然使得她有时过多美化了美国社会,但这绝对不全是对美国文化的主动迎合,更不代表与之共谋,而是不得已为之的一种间接对抗。因为作为少数族裔作家,他们所期待的读者是不懂中国文化的美国大众,通过这种策略性写作,美国读者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些对中国正面的描述与以前白人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歪曲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20世纪60年代永远改变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景观,民权运动引发的民族平等斗争唤醒美国华人的少数族裔意识。60年代最有实力的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探讨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关注女权主义运动,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小说着力刻画女性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无论是中国封建传统制度下的牺牲品还是作为传奇的英雄和增进相异文化交流的使者,汤亭亭笔下丰富多彩的妇女形象都有深刻的涵义。汤亭亭不仅为被消音的华裔女性获得言说权,而且把她们当作道德的楷模、冲锋陷阵并无往不胜的勇士和英雄。通过文中这些女性角色的刻画,汤亭亭试图在白人主流社会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妇女翻案,消除主流社会对华人妇女的歪曲性刻板形象,以其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批判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著名台湾学者冯品佳在论述汤亭亭的贡献时,把她与美国黑人女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相提并论,说她俩“塑造亚裔和非裔身份的作品对成长小说(bildungstroman)研究、美国文学史和美国集体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Feng,1998:2)。
与汤亭亭一样,谭恩美同样是一位开拓者,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她以优美的语言描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恩恩怨怨,以及在文化认同方面的各种矛盾冲突、感情冲突等,探寻了母女两代人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与融合。作者在创作中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同时在中西文化大传统的语境中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作品更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文本中的母亲们逐渐从困惑和迷茫中清醒,她们大胆打破沉默,通过回忆历史达到母女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同时也使深陷东西文化夹缝中的母亲和女儿获取力量,找回自我。在她的小说中,中国母亲的形象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谭恩美所有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视角体会到的中国文化传统,因此激起了美国华裔及其他族裔美国人的关注。
善于使用幽默彰显华裔美国人生活的作家任壁莲要求以一个族裔“边缘”文化解构美国社会以男性白人为中心的霸权文化,继而追求不同文化之间无障碍的交流以及文化身份之间无种族背景困扰的自由流动。任璧莲在《典型的美国人》小说中刻画的特蕾萨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正面的女性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她是道德完美的代表,在为人处事方面,特雷萨考虑周全,时时忠于家庭,总是扮演着家庭的保护者的角色。特雷萨自小接受西式教育,来到美国后她许多方面都相当西方化了,为了生存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我奋斗的道路,并通过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虽然特雷萨已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在内心深处里,她依然是个负责任、明事理,具有自我牺牲等传统美德的中国人(程爱民,2010:193)。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身上的故国优秀文化传统,任璧莲所宣扬的“杂交”文化身份在特雷萨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1993年,被称为美国华裔新生代作家的伍慧明直接用“骨”(Bone)一词作为她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受到最高赞誉的一部小说的名字,这种对祖先遗骨归宿的追忆,等于是用明确的方式对华裔祖辈历史的探寻。书中的女主人公莱拉是作者尝试塑造的新一代自立自强的华裔女性代表。尽管华裔女性追求自我的道路充满艰辛,但女主人公一直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对自我有着明确清晰的认识与自我价值认同。她反抗中国传统礼教“重男轻女”的观念,对男权社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抗议,从而对自身文化身份有清晰的定位。小说的结尾,莱拉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搬离唐人街,与男友结婚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的行为肯定了华裔女性在处于两种不同文化时必须坚定信念、肯定自我价值、大胆追求自我。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莱拉超越了东西文化冲突的模式,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求自我文化身份的整合,从而形成互补性的建构。
五、结语
华裔女作家群通过更为真实的华裔女性形象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也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化及华裔男作家对华裔女性“莲花”和“龙女”型形象的文化扭曲。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在无意间也形成了新的模式化女性形象。如奴隶女儿或妓女几乎没有出现在华裔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正如历史学家佩吉·帕斯科所说:“在对抗种族模式化形象中,华裔作家60和70年代的作品不谈罪恶和丑陋,努力淡化美国华裔的过去。”(Pascoe,1989:631)也许华裔女作家是出于一种对母体文化的尊重,在有意淡化华裔美国人在美国负面意义的经历和体验。但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为华裔文化的代言人,华裔女作家有责任在作品中反映现实,因为她们的作品之所以被众多西方读者接受是因为她们本身是华裔群体的一分子,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华裔女作家只有勇敢面对伤痛,揭开昔日的伤疤才能真正明白作为美国华裔女性的真正意义,并为美国华裔女性新的政治、文化、性别身份增添新的内涵。
[1]Cai,Qing & Zhang Hongwei.Eternal Seeking—A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dition in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9.
[2]Feng,Pin-chia.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M].New York:Peter Lang,1998.
[3]Fox,Timothy R .Challenging Racism with Pan-Asianism:Learning Resistance through Failure in Frank Chin’s“The Sons of Chan”[C]//Huang Guiyou & Wu Bing.Global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Beijing:FLTRP,2008.
[4]Kingston,Maxine Hong.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views[C]//Guy Amithanayagam.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London:Macmillan,1982:55-65.
[5]Kim,Elaine H.Visions and Fierce Dreams:A Commentary on the Works of Maxine Hong Kingston[J].Melus,1981(8):2 ,145.
[6]Louse,Vivian S.Compelled to Excel-Immigrati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among Chinese Americans[M].Guy Amithanayaga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7]Pascoe,Peggy.Gender Systems in Conflict:The Marriages of Mission-Educated Chinese American Women 1874~1939[J].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89:631-652.
[8]Tang,Weiming.Emergent Literature:Transcultural Matamorphosis in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Writings[M].Tianjin:Nankai UP,2010.
[9]程爱民.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关合凤.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身份寻求: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1]金伊莲.差别如此悬殊:美国亚裔文学中的男性和女性[J].密执安评论季刊,1990(2):75.
[12]李小兵.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13]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石平萍.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研究[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15]吴冰.华裔美国文学的历史性[J].外国文学研究,2010(2):120-125.
[16]张龙海.美国东方主义语境下的华人形象[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12):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