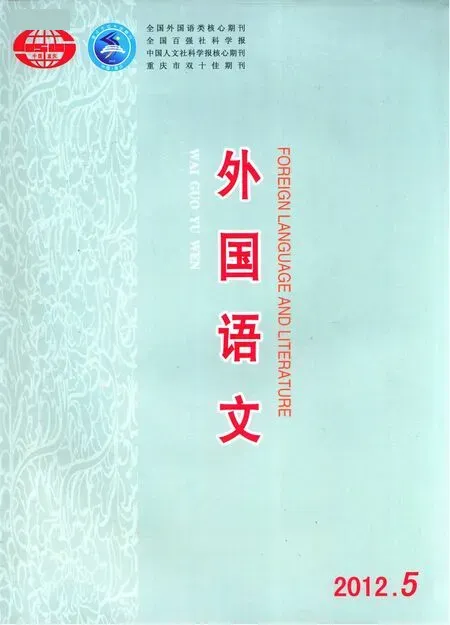加拿大南亚移民文学作品述评——多元文化车轮之独特齿轮
刘忠文
(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辽宁 大连 116036)
数十年来,多元文化问题已经涉及艺术、文学、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这些多方位的研究反映出多元文化主义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极为广泛。它们重点对以下领域进行审视:关于特有文化基本原则的制定;关于主流文化中的“我们”区别于边缘文化的“他们”的确定;关于民族特征和文学反应的凸显。当前加拿大有两种意识潮流(国家集体意识和单一民族意识)并存,这种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有可能锻造成国家意识。
一、加拿大多元化人口构成的新趋势
加拿大拥有极其丰富的多元文化人口。根据2006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加拿大目前拥有200多个不同民族,总人口超过3100万,有色族裔约500万,其中有120万为南亚人,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斯里兰卡人。[1]同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加拿大58%的新移民来自亚洲或中东,11%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1%来自非洲,来自欧洲的移民下降到了16%,这与1971年的61%相比,有了大幅下降。[2]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促成了加拿大人口多元化特征愈加明显。20世纪初期,主要由欧洲和俄罗斯东部大量涌入的移民态势已转向了20世纪后30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移民涌入。这种种族多样性预示着21世纪加拿大的多元文化问题将更为广泛而复杂。全球不断发展的人口和经济趋势表明加拿大未来的移民将主要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传统性国家。[3]为了应对这一新的移民形势,加拿大政府启动多个项目以培养本国公民的多元文化意识。1971年颁布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到目前为止制定的各项相关政策,尚未完全满足少数民族的需求。帕萨里斯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一个国家的财富》中这样评价:“从更大程度上说,多元文化主义被视作民俗盛事,社会缺陷或政治足球。”[4]3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移民社区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创伤。帕萨里斯断言:“似乎联邦政府的原有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再是一个有远见、有创造性的计划与行动的坚实基础。这项计划是在世纪之交为建设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和谐共处的加拿大社会铺平道路。”[4]3为了确保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实现所有加拿大人完全公平的合作目标,需要制定一项新政策。198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保护和加强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法案》,这为多元文化政策的新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法案成为多元文化政策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助推器,加拿大多种族宝贵的人类资源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他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多元化的国家而各尽其能。
二、加拿大移民文学作品之功能
文学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移民文学作品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在与“他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中,实现了两项功能:探索与评价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文化、宗教及价值取向。事实上,文学作品是具有权威性的文化研究,它能够穿透不同的社会政治利益,突出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的多重斗争。由于它们对权力机构中的不平等分配提出了质疑,它们为寻求重建主流和亚文化之间的正常关系提供了途径,因此,移民文学作品介入了政治领域。它们对整个社会的信仰和制度、文学作品的产出形式以及其他文学附属问题:出版、发行与营销,进行着全面的审视和深刻的剖析。
加拿大最近出版的大量移民和土著文学作品探讨了多元文化问题,对多元性中的统一性提出了假设,对加拿大众多民族与众多文化群体的融合方式进行了探索。然而,移民文学文本似乎在暗示上述两个目标都是神话,它们的核心象征是距离与差异。构建着这种神话的文学作品可以解释、证明,甚至是逐渐削弱加拿大的现实。正如英国殖民者是在基于殖民地民族是劣等种族的神话下,他们才会“合情合理”地统治着殖民地。然而,这里也出现了恰好与之相悖的神话:这片土地留下了英雄的足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加拿大的文学作品选择了讴歌差异性,而并未讴歌统一性。
加拿大土著和移民文学作品对承认与欣赏文化多样性怀有真正的渴望。从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化中可以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证明上述观点。21世纪的文化导向是重视培养人们有效解决冲突和文化差异的能力。正如格拉芙和费兰[5]所观察:“未来通过争论来学习是对公民正确有效的培养。”瓦桑吉和穆克赫吉是来自南亚的移民作家,阿姆斯特朗和约翰斯顿是土著作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加拿大多元文化车轮中具有文化差异性的齿轮的基础。正如他们的文学作品所展现的,这些“齿轮”正在有意义地参与到所有对社会、文化和政府至关重要问题的进程中来。这些所谓的边缘族群应当利用其母语作为争取其权利的斗争武器,他们独特的身份特征应当是保留,而不是浸没在毫无差别的统一身份中。移民作家把多元文化的差异问题嵌入其文学作品,他们尝试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源于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被混合的生活方式和交错的语言形式所包围。巴伯哈提出这样的问题:“语言之间、文化之间、约束之间、民族之间,你怎样能够为它们划出清晰的界线?”移民和土著作家已经选择借用自己的独特语言——母语——来发出心灵、文化和地域的痛苦的呐喊。
三、加拿大南亚移民文学作品之评介:从原籍国到加拿大的心灵跋涉
欧裔加拿大人对于“南亚”一词会产生大量想像的身份特征,包括对南亚次大陆不同的地理特征,以及锡兰岛(斯里兰卡的旧称)和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1858~1947)“光辉”历史的联想:“南亚”既可以是甘地主义(不使用暴力的抵抗主义)产生的摇篮,又可以是旅行者获得巨额财富的梦想,抑或是一贫如洗的梦魇。
1.南 亚移民作家的写作特点:以瓦桑吉为例
尽管很多加拿大作家已经对“南亚”形成了上述观念(从萨拉·丹肯到莎朗·鲍洛克),但是南亚裔作家的作品无法得到广泛的欣赏。首先,必须承认加拿大南亚移民作家存在某些内在的弱点,即他们用过多的笔墨描绘着自己的原籍国,而忽视了其接受国——加拿大。作家瓦桑吉除了一部小小说《没有新土地》是描述加拿大本土的作品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均以他的出生地坦桑尼亚为背景。密斯特里的小说则发生在印度,这将导致一定程度的背景混乱,或者在双背景下徘徊。南亚裔加拿大人在两种文化世界之间挣扎,若想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就必须理解他们双层背景的复杂类型。移民背负着本民族文化的沉重行囊,那些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熟悉的宗教仪式、林林总总的文化表现形式:服饰、生活方式、歌曲、故事、民俗等等,把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蕴诉诸笔端。他们的移入限制了他们按照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的能力,但是却无法限制他们强烈的保护其传统理念的内心需要。在新家园他们面临新传统的挑战,他们通过顽强生存作为迎接挑战的回应。南亚移民属于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族群,拥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发现难以适应加拿大这个新鲜、多民族、多文化、混合复杂的生存环境。因此,南亚裔加拿大作家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无法被主流群体视作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南亚作品”这一术语包罗万象,它既包含直接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的移民作品,又包含那些能够追溯到印度祖籍的加勒比和非裔加拿大人的作品。许多第一代移民作家表达出双重背景交替转换的心理紧张情绪,描绘了因物质和经济的丧失自己不得不离乡背井的忧愤情怀,同时也述说了他们在新的国度所遭受的敌意、种族偏见和倍受忽视的内心苦痛。大多数南亚裔加拿大作家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表现出论述原籍国风貌的一贯风格,后期才转而论及加拿大的主题。瓦桑吉的《没有新土地》(1991)就是一个南亚裔加拿大作家在爱上他的第二故乡时才开始触及加拿大主题的最好例证。然而,他的另一部作品《秘密书籍》(1994)却继承了其早期作品:《麻袋》(1989)和《乌湖卢大街》(1992)的衣钵,重新追溯种族往事的记忆。这表明了移民作家的一种内心需要,即重新发现共同分享和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这将成为那些被除却其历史的社会成员追溯其历史与身份的参照系,去了解本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内在关系,并由此获得自我认识和自豪感。瓦桑吉在他的作品中竭力向他的民族展现这样一幅记忆的画卷,他渴望自己成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他期待着写作成为他的专职工作和终身事业。他写道:“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地域感的民族,因此我的民族成为我写作的主题。我们知道我们居住地的名字,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我们往往放眼未来,也许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我们的过去在哪儿?我们的根又在哪儿?”《麻袋》中的主人公萨利姆·卡拉对他的祖籍、他的自我身份和他的历史足迹的探寻就是作家瓦桑吉本人的探寻。《麻袋》就是一个来自非洲印度裔加拿大作家追溯其历史渊源的铿锵陈词。《秘密书籍》既是几代人的发展史、社会编年史,又是一部侦探小说,一个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的逼真的生活画卷。《没有新土地》是夹杂在这两部小说之间的“纯粹娱乐”型小说,表现了瓦吉桑对本族群移入多伦多后的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注,它聚焦于那些来自达雷斯萨拉姆的移民生活,他们如何在这片异国土地重新确定自我。他替沉默的本族同胞(加拿大主流群体中缺失或隐没的群体)代言。瓦桑吉用豪华商场、高楼大厦和CN塔(世界第一高塔)来重新描绘多伦多,传递着亚洲移民所难以理解的信息:这是一个“另类”亚洲人眼里的多伦多,一个神奇世界和隐秘的陷阱:“每一步都是一个充满着窘迫的神秘之旅,人们等待着你出丑。”[6]32这些亚裔人离开非洲(他们几代人家园),来到加拿大,深切地体悟到他们必须确定自己的未来,要竭尽全力获得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位。但是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这个新家园的主人并未向他们热情地敞开大门,工作机会极为稀少。努尔迪恩·拉拉尼(《没有新土地》的主人公)意识到在求职场,微妙的种族偏见意识让他屡屡受挫,这就是被他们称作王牌的“加拿大经历”。
他的前几次工作申请都被拒绝了:一点失望却增加了最终成功的喜悦。但是这种生活模式却持续着,在他的内心深处显现出最赤裸裸的阴影:即将到来的绝望和就业无望的前景,逐渐变得清晰可辨。然而,这却没有让他感到恐惧。[6]43 -44
这就是加拿大。拉拉尼一家人发现了这个一贯重复的短语的新的内涵,一个与加拿大白人语篇所获得的完全不同的内涵。瓦桑吉的关切是要表现亚洲移民如何适应新的现实世界,根深蒂固的历史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演变成充满仇恨的流沙。他们要与过去相妥协:不能逃避,而是要承认它,目的是为了勇敢地面对现在和奔向未来。“从前,过去在远方为你安排着一切,你却不予理睬;现在,过去就在面前,在你的四周,你所担当的未来与你会更加相配。”[6]207无疑,《没有新土地》显然被认为具有加拿大的特质,诉说着移民所经受的严酷的生活现实,以及交织在两个世界的人类精神痛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描述离乡背井的小说一改瓦桑吉前期作品一贯重视范围和意义的写作特征,如《麻袋》、《乌湖卢大街》或《秘密书籍》。正如另一位移民作家伊特瓦鲁所言:“离乡背井不仅仅是生活在另一个国度,这是一种认识到逐渐与我的过去相疏远的自我的生活。”[7]《没有新土地》完整地描述了一个移居民族在与大量主流人口的社会交织网中所深切体会的疏离感。《没有新土地》小说文本更适合对多元文化主义命题的探讨。
2.南亚移民女作家独特的心理特征:以穆克赫吉为例
最感人的南亚裔小说家的作品往往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加拿大以外的国度,它与“加拿大经历”或加拿大风貌无关。这使得弗兰克·大卫把本民族进一步边缘化,理由是他们包含着极少的加拿大政治文化元素。然而这种排他性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他的《后民族论》中的固有主张与1985年联邦政府颁布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所宣扬的理想相同,都是在竭力消除任何一个族群试图影响和统治其他族群的危险。“南亚”这一术语本身由于范围广泛而具有分歧意义,由此产生了无法共同讨论的弊端。在广为赞誉的包容理论中,肤色、民族和种族等概念无从寻找。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多元主义坚持认为人类应被视作独一无二的个体,种族应被视作最次要的特征;多元文化主义则认为民族作为族群的代表,应被视作最重要因素,种族是讨论的关键问题。但是对于加拿大移民作家的写作事业而言,这两种理论的简化原则均未得到充分体现,虽然很多移民作品由著名出版社出版,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与白人作家相同的待遇。
移民女作家可能会受到双重边缘化,作家巴哈蒂·穆克赫吉就是范例。她的作品往往被视作南亚裔加拿大作品的一部分,主要探讨加拿大经验:一些是讽刺联邦政府的公民权利和移民部门,一些是概述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思想偏狭,一些是揭示种族之间的深度误解。穆克赫吉是一位有争议性的作家,因为她竭力疏远印第安读者,而去讨好非印第安读者和批评家。这大概应归因于这类小说《老虎的女儿、妻子或茉莉花》对“抨击印第安人”产生了明显作用。然而,她收集在《黑暗》(1985)和《中间人和其他故事》(1988)两部故事集中的作品则大多以她的加拿大移民经历为线索。也许,我们在她的作品中能够察觉到猜疑的阴影或遭受迫害的综合情结。她这样写道:“我在加拿大度过的这些年,从1966~1980年,我发现国人对那些出生在炎热、潮湿的大陆(例如亚洲)的公民怀有敌意,我发现国家骄傲地宣称他们彻底反对文化同化的概念。在加拿大,我经常被当作妓女或扒手,经常被认为是家仆,受到周围听众的吃惊的赞誉,我竟然没有那种移民常有的单调口音。”社会本身,或者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和我们“这一类”移民通常怀有无限的成见。[8]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甚至一个已经西化的亚裔人也会因上述经历心灵受到创伤,谁都承认这种令人破碎的极度痛苦和不断增加的非安全感是当代南亚裔加拿大人的特殊情感。穆克赫吉故事中的许多印度裔主人公在未移入加拿大前天真纯洁,但是在这个异域环境中却丧失了灵魂,被他们难以控制的力量所围困,身陷“囹囚”。他们对爱情、友谊、交流、安全感和自我身份的追求却被公开和隐蔽的种族主义所阻断;他们向异国土地的迁移遭遇了种族主义的冷遇。穆克赫吉这种被放逐原籍的令人心神不宁的故事,抑或那些兴高采烈和充满信心的故事(表现在对缓慢但是最终要融入到主流社会的同化持认同态度)有效地突出了在两种文化之间,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表现了移民的无助与无奈。穆克赫吉表达了那些摆脱幻想的人物在自我意识的拙劣模仿下的辛酸,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四、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和南亚移民文学作品的反思
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坚持“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作家对生活的参与,任何作品都反映生活对作家的影响和作家对生活作出的回应”[9]。加拿大南亚移民作家也正是在基于两种文化背景交替转换的过程中,在参与到两种生活方式,体验到双重生存状态中,创作出凸显南亚移民的各民族特质、表现南亚移民特殊情感的文学作品。这是加拿大多元文化车轮中一个别具民族特色的独特齿轮,是加拿大文学作品中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他们写作初期的作品大都追溯其原籍国,本民族的文化风貌,展现原籍国的风土人情,这是移民作家对自我身份的一种积极的心灵探寻。从追溯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增加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他们后期的作品则开始触及加拿大本土的主题,这一方面源于定居时间的加长逐渐产生了对加拿大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源于对自我移民生活心理真实感受的记录。南亚移民作家眼中的“加拿大”与主流社会白人眼中的“加拿大”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虽然加拿大特鲁多政府从1971年宣布实行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随后,政府在四个方面推进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帮助所有不同文化成员克服文化障碍,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在保证国家团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加拿大各文化集团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帮助移民学习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使其全面顺利地融入加拿大社会。1988年议会正式通过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重申了1971年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声明:加拿大政府承认族裔与文化多样化之合法性,视多元文化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与宝贵资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鼓励他们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至此,加拿大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多元文化主义为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成为加拿大的象征,成为加拿大人家喻户晓的政治代名词,但是在该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却让众多少数族裔感受到政策与实践的相互脱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南亚移民作家的后期作品对此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描述,让读者感受到南亚移民在加拿大的生活困境和为创造美好人生而遭受的种种磨难。虽然生活窘迫,但是移民却表现出不畏苦难,通过自我奋斗,改善生存现状的乐观精神。这也是南亚移民作家送给本民族移民的精神食粮和情感慰藉,帮助他们在加拿大寻找既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精髓,又能够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构建既富多元化特色又能协调统一的加拿大文化意识。
通过对南亚裔文学作品的分析,我们应思考这样一个课题:旧世界(原籍国)的信仰能否为移民在“新世界合理化”的思潮中提供一定程度的宽慰。未来世界是多元化和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只有让公民通过公开辩论和深刻反思才能让他们学会自我学习,不断提升自我认识。这是对未来公民进行培训的明智选择。学会有目的地参与到各项与加拿大社会文化以及与政府事务相关联的活动,这对普通加拿大移民而言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然而,移民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身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一种文化被看作是对另一种文化的支撑,那么这两种文化将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相反,却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任何亚裔加拿大人都眷恋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根,因为他们的外表与他们的内心都难以抹去自己的民族特质。原籍国的传统与文化,例如宗教,在道德本质和精神支持方面都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移民作家在文化兼精神层面的贡献已初显雏形,他们通过语言,利用自己的文字作为武器和策略,为本民族移民争取了应有的权力。正如赛里尔·黛比狄恩所言:“加拿大人的集体精神在新旧传统的融合和撞击中被多样化的文化潮流所提升与丰富,它将逐渐发展成统一的加拿大意识。”[10]
五、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展方向的思考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从战国时的“胡服骑射”到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织锦术,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是中华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源泉。文学的精神财富是属于人类集体的,无论文学的创造者属于什么民族。虽然汉族书面文学一直非常发达,但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却超过了汉族,如蒙古族《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它们是中国文学的佼佼者,并为世界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文坛,少数民族作家是一支强劲的不容忽视的创作队伍。但与主流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时候是缺少主体独立性的存在,这与少数民族自身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的双重边缘有直接的关系,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在社会飞速发展时期无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难以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的主流生活,使得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其他民族观赏、误读,被同一民族漠视、遗忘的尴尬处境。从上世纪末,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进入一个文化身份意识深入挖掘、不断寻求民族发展动力的新阶段。这是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正如加拿大南亚移民作家,注意到本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变化过程,努力探索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将其诉诸笔端,这是注重文化身份意识的表现,更是创作的不竭源泉。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参与生活,感受文化,失去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难以建构一个独特丰富的文学世界。但是全球化的车轮把世界所有民族都要搭载上飞速发展的战车,此时此刻,如果拒绝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想以一种纯粹的保护主义来对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是肤浅的,偏执的,从根本上说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真正热爱自己民族文化并谋求其继续发展的人,就应当摆脱完全保护、拒绝发展的民族情绪。只有以辩证的态度审视自我并且敢于自我否定者,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捍卫者。这种审视和否定不是对民族文化的怀疑和抛弃,更不是从“他者”的强势文化体系出发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同化,而是站在全球化高度,摒除一切阻碍现代发展的消极因素,最终使自己的民族文化走向真正的完善和强大,真正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性走向更深刻、更广阔的人类性,这是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具有长期性的一个话题。[11]
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富含强大自足的传统、灿烂多彩的文化,但是在当下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的确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处境,其文学价值和文化功能往往不被认同或不被重视。但是只要少数民族作家永保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敢于面对和参与现代生活,提高知识分子心灵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从他民族文学中汲取营养,既讴歌本民族灿烂的文化和历史,又能直面其内在的问题和缺点,走出“单边叙事”的传统表达方式,就能够为少数民族文学开辟全新的发展道路。一种民族文学自觉的追求如果仅仅过多地看重主观设置的“单边叙事”,这就很难达到多方面的文学目标。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该“走出”自我限制和自我隔离的樊篱,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叙事,采取多种个体性的写作叙述风格,广泛地参与文学交流与互动,只有这样,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才会越走越宽广。少数民族文学必将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它一定会有从遮蔽到绚烂的过程。
[1]人口普查:加拿大人口组成进一步多元化[EB/OL]2008-04-03路透社http://usNews/idCNChina-908520080403
[2]加国种族结构悄然改变2009-08-18[EB/OL]http://ent/2009-08-18/detail_72138.html
[3]Canada.Roy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Un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Canada[R].1985:668.
[4]Passaris,C.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The Wealth of a Nation[C]//Calgary.Multi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Building Canada.AB:Detselig.1989:3.
[5]Graff,G.and J.Phelan.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nn:A Case Study In Critical Controversy[M].Boston:St.Martins Press,1995.
[6]Vassanji,M.G.No New Land[M].Toronto:McClelland Stewart.1991.
[7]twaru,A.H.Excile and Commemoration[C]//F.Birbalsingh.Indenture and Exile:The Indo-Caribbean Experience.Toronto:TSAR Publications,1989:202.
[8]Mukherjee,B.Darkness[M].Markham,ON:Penguin Canada.1985:2.
[9]邵珊.走向文明的批评:现实与诗性之间——论埃·威尔逊的批评观[J].南京师大学报,2006(6).
[10] Dabydeen,C.A Shapely Fire:Changing the LiteraryLandscape[M].Oakville,ON:Mosaic Press,1987:10.
[11]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民族文学研究》[EB/OL].2010 - 03 - 08,http://wx.tibetcul.com/zhuanti/pl/201003/20540_3.html